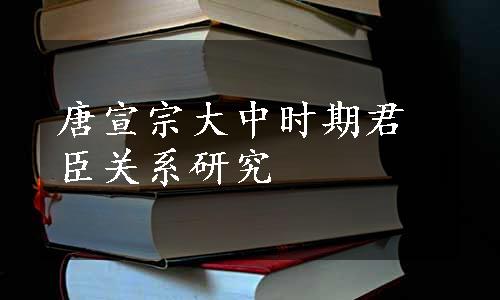
第二节 大中时期的君相关系
我们知道宣宗为宦官矫诏拥立,同朝臣并无多少渊源关系,故而大中初期宣宗不得不向宰臣们作出诸多让步。白敏中碌碌无为,在其失去利用价值之后,宣宗不动声色地借党项之乱将其出为都统。崔铉欲引其党人郑鲁为相,宣宗亦装作不知,出郑鲁为河南尹。宣宗不想将自己同宰相的矛盾公开化,在最大限度上维持君臣之间表面上的和谐。大中中期以后,宣宗对李德裕一派的政治清洗基本完成,君相之间失去了共同的敌人,矛盾也随之凸显出来。牛党宰相喜欢结党怙权,重用党人,而宣宗欲强化皇权,必然要拔擢近臣,双方的摩擦开始增多。这种变化在大中八年(854)及十年(856)的京兆尹人选之争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京畿地区为唐朝统治的心脏地区,所居多为豪门显贵,尤为难治,因此唐代“京兆尹有生杀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轻薄之,目为所由之司”[15]。党争兴起后,牛、李双方对京兆尹之选都十分重视[16]。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所用韦正贯、李拭、韦博、孙景商等人多为李德裕所抑之人[17],而薛延赏等武宗朝敢于任事者皆遭贬斥,长安很快又恢复到权豪恣意横行的状态,京兆久不为理,宣宗对此大为不满。大中八年,京兆尹孙景商迁为刑部侍郎[18],京兆尹一职出现空缺,围绕着京兆尹人选问题,宣宗与宰相之间展开一番暗中较量。《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附杜中立传》云:
京兆尹缺,宣宗将用之,宰相以其年少,欲历试其能,更出为义武节度使。[19]
杜中立开成初尚主,历左右金吾将军、又两任弘农卿,已有一定的治理京城的经验,所谓“欲历试其能”其实是排挤杜中立的借口。宰相抑塞杜中立,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杜中立为驸马,是皇亲国戚,背后有皇权撑腰,较为跋扈,日后难为宰相所制。其二,杜中立居官精明,用法深刻,曾扬言:“朝廷法令备具,吾若不任事,何赖贵戚挠天下法耶?”杜中立若得大用,牛党官僚势必要多有忌惮。在这次人选之争中,宣宗做了让步,杜中立出为义昌节度使,而且无缘再返朝廷。继孙景商上任的是崔罕,崔罕颟顸不法,一次内园巡官冲撞了他,竟被活活杖死。宣宗怒不可遏,敕宰相远贬一郡,但是在宰相的再三论救之下,最后仅贬为湖南观察[20]。崔罕事件后宣宗逐渐赢得了主动,大中十年(856)五月,宣宗面授翰林学士韦澳京兆尹一职,便令赴任[21]。韦澳上任之初,宣宗即赐度支钱二万,与作府宅;宣宗舅郑光庄吏恣横,租税积欠不纳,韦澳将其收捕,宣宗代为交足欠租;又京兆府有厌蛊狱,涉案者郭群属飞龙厩,三牒不可取,韦澳入奏后次日即押解送府[22]。在宣宗的积极配合下,京城很快就出现“豪右敛手”的可喜变化。但是正如前面所言,韦澳任京兆尹出于宣宗面授,没有得到宰相的支持,其与宰相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迅速激化。我们知道,武宗时李德裕大力奖擢孤寒,抑制子弟应举,宣宗即位后会昌之政被悉数废除,科举几乎完全为官僚权贵们所垄断,“至解送之日,威势挠败,如市道焉”[23]。韦澳对此深为不安,下榜规定送省进士、明经不再划分等第。这一举措很快就遭到令狐绹等朝中当权派的排挤报复,《旧唐书》卷一五八《韦澳传》载:
会判户部宰相萧邺改判度支,澳于延英对。上曰“户部缺判使”,澳对以府事。上言“户部缺判使”者三,又曰:“卿意何如?”澳对曰:“臣近年心力减耗,不奈繁剧,累曾陈乞一小镇,圣慈未垂矜允。”上默然不乐其奏。澳甥柳玭知其对,谓澳曰:“舅之奖遇,特承圣知,延英奏对,恐未得中。”澳曰:“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务,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错。尔须知时事渐不堪,是吾徒贪爵位所致,尔宜志之!”[24]
萧邺判度支在大中十年(856)秋,此时距韦澳任京兆尹仅数月而已,短短几个月内韦澳就已经“累曾陈乞一小镇”,其在朝中的孤立也可以想见。判财政三司是通向宰相的重要阶梯,是年郑颢正在积极地营求宰相,令狐绹与郑颢为姻家,必然全力支持郑颢,暗中排挤韦澳。至于令狐绹以何种手段向韦澳施加压力,史无明言。韦澳对其甥柳玼说:“吾不为时相所信,忽自宸旨,委以使务,必以吾他歧得之,何以自明?”在唐代,自“他歧”得官很大程度上就是交通宦官得官的同义语。韦澳京兆尹之任为宣宗私用,没有同宰辅商议,这里韦澳旧话重提,显然是有所指的。我们推测,诽谤韦澳自“他歧”得京兆尹可能就是令狐绹等人煽动舆论,压迫韦澳引退的卑鄙伎俩。总而言之,在宰相的安排下,郑颢顺利地谋得户侍判户部之职,而韦澳则没能逃脱外任的命运。大中十一年(857)正月韦澳出为河阳节度使。继任京兆尹的是柳熹、崔郢等大族。崔郢同崔罕一样喜欢作威作福,因杖决府吏而罢。继其后者为张毅夫,这时韦澳所定京兆解送不分等第的做法已被公然废除[25]。
韦澳外任时,宣宗对他说“卿自求便,我不去卿”[26],但也无可奈何。韦澳去后不久,宣宗又思之不已,复派人去河阳探望。《东观奏记》卷下载:
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尹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遂中寝。
本条不仅肯定韦澳自京兆出镇河阳为“当轴者”的排挤,而且还进一步表明,宣宗本不乐外授此官,所以命中使以密诏安抚韦澳,并许以秋季入朝。但是,宣宗为什么要特别告诫王居方“无令人知”呢?大中十一年(857)宣宗手诏刘瑑入朝也有类似举动,刘瑑也是深受宣宗器重的翰林内臣,此前出为河东节度使,直到刘瑑从太原动身赴京,外人才知入朝之事。刘瑑入朝时宰相为令狐绹、崔慎由、萧邺三人,其中,萧邺与崔慎由素不相合,刘瑑入朝即为其所引。宣宗秘其行踪,目的就是要防止崔慎由、令狐绹等人从中作梗。同样,宣宗欲命得罪权贵的韦澳返京,密诫中使“无令人知”,目的就是在韦澳返京前摆脱宰相们的无端阻挠。大中后期,尤其是大中十年(856)韦澳面授京兆尹以后,宣宗愈来愈多地采取密授近臣官职的办法,这反映出宣宗君相之间的矛盾日益公开化。
从京兆尹的任免情况来看,宣宗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自由”,即他可以把有错误的官员撤换掉,却总不能随心所欲地提拔自己亲信的官员,尤其是那些不为宰相所喜的官员。在无力撼动宰相权势的情况下,宣宗只得运用各种权术来驾驭宰相。
宣宗为宦官所立,对宦官集团的政治能量心有余悸,非常留意防范宰相与宦官结交。《东观奏记》卷上云:
马植为相,与左军中尉马元贽有亢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贽恩泽倾内臣,曾赐宝带,内库第一者,元贽辄以遗植。一日,便殿对,上睹植带,认是赐元贽者,诘之,植色变,不敢隐。翌日,罢为天平军节度使。行次华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狱,尽闻植交通之状,再贬常州刺史。[27](www.zuozong.com)
大中早期宣宗地位不十分巩固,不敢直接触动马元贽,只有拿根基尚浅的马植开刀,将其远贬为常州刺史。大中中后期随着皇权的巩固,宣宗对宰相交通宦官的防范更为严厉。《东观奏记》卷中云:
上每命相,尽出睿旨,人无知者。一日,制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仰指挥学士院降麻处分。”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邺先判度支,再审圣旨,未识下落,抑或仍旧?上意贵近佑萧也,乃宸翰付学士院:“户部侍郎、判户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书、平章事,落下判户部事。”宸断如此。
自从韦澳被排挤之后,宣宗对宰臣有所不满,命相很少同宰相商量,以至外间“人无知者”。就本条萧邺罢相之事而言,萧邺在崔慎由后一年拜相,王归长、马公儒二人都是宣宗临终前的托孤之臣,此三人并没有因此而获显罪,宣宗临时换相,目的就是杀鸡儆猴,警诫王归长等不得自作主张,同时也告诫萧邺等不得结交宦官。
延英召对是中唐以后宰相议政问题上的重大变革。唐制:“阁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28]朝臣退后,宰相形式上也只能提出意见供皇帝参考,即所谓“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29]。延英议政最大限度上保证了皇帝集思广益,避免权臣的欺隐,宣宗对此尤为重视。《东观奏记》卷上载:
上临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唤上阶后,左右前后无一人立,才处分,宸威不可仰视。奏事下三四刻,龙颜忽怡然,谓宰臣曰:“可以闲话矣。”自是,询闾里闲事,话宫中燕乐,无所不至矣。一刻已来,宸威复整肃,是将入宫也,必有戒励之言。每谓宰臣:“长忧卿负朕,挠法,后不得相见!”度量如此。赵国公令狐绹每谓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对,虽严冬甚寒,亦汗流洽背。”
宣宗非常重视延英召对时的威仪,特意通过调整召对时的张弛变化来营造整穆氛围,给宰臣造成压力,使其不敢欺隐自己。并且经常用“长忧卿负朕,挠法,后不得相见”等语句警告宰相不得朋比营私。旧例,延英召对时枢密使等也可参与其事,为避免宰相不能畅所欲言,宣宗规定召对时两中尉先降,枢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结束后,枢密使再在案前受事[30]。大中末宣宗曾用“异日不复得独对卿矣”作为蒋伸入相的暗示语,可见宰相不得独对的原则也得到较为严格的贯彻。
文宗大和初,刑部、大理寺等刑法官获得在皇帝面前奏对的权力,开成五年(840)武宗即位后专任李德裕,百官谒见之制削弱,刑、法官奏对之制罢废。大中三年(849)十月,宣宗规定待制官与谏官、法官循环奏对[31]。除宰相外,待制官、谏官、法官及诸道节度使、诸州刺史等也都有机会谒见宣宗。宣宗接见群臣,表面上看是宣宗勤政纳谏,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相权的猜忌。
《金华子杂编》卷上载:
令狐公绹,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亲握庶政之后,即诏诸郡刺史,秩满不得赴别郡,须归阙朝对后,方许之任。绹以随、房邻州,许其便即之任。上览谢表,因问绹曰:“此人缘何得便之任?”对曰:“缘地近授守,庶其便于迎送。”上曰:“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亲问所施设理道优劣,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德音即行,岂又逾越?宰相可谓有权。”绹尝以过承恩顾,故擅移授。及闻上言,时方严凝,而流汗浃洽,重裘皆透。[32]
唐代选官皆在孟冬,本条云“时方严凝”,与时令相合,疑前引《东观奏记》中令狐绹自语“虽严冬甚寒,亦汗流洽背”所指为同一事。胡三省就此事批评宣宗道:“如令狐绹之欺蔽,罢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为相而畏其有权,则宰相取充位而已。”[33]事实上,若宣宗因如此小事就将令狐绹“罢其相而罪之”,不但其党羽会三番五次地论救,甚至还会落下气度狭小、猜忌宰辅的恶名。宣宗当面指责令狐绹“宰相可谓有权”,即顾全自己的威严,又给宰相施加压力,警示其不可擅作主张。此事《通鉴》系于大中十二年(858)十月下,同年十一月,牛僧孺子牛藂自司勋员外为睦州刺史,中谢时宣宗问道:“卿顷任谏官,颇能举职,今忽为远郡,得非宰臣以前事为惩否?”[34]看来令狐绹的回答并没有打消宣宗的疑忌,在牛藂外任时宣宗尚故意旁敲侧击,希望能抓住令狐绹的把柄。宣宗责令狐绹事从侧面揭露了当时宣宗君相之间貌似相得,实则疑忌很深的情形。
宣宗驾驭宰相的策略以“防”为主,通过自己的“明察秋毫”,防止宰相欺君枉上。既然宣宗喜以细节末枝来“明察”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也会制造种种善行来迎合宣宗的“明察”,这一点在令狐绹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令狐绹对付宣宗“明察”的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自己不亲自收受贿赂,而由其子令狐滈代行其事。为表示清白,令狐绹故意不让令狐滈参加科举,也不为其谋求任何官职。这样既可消除宣宗疑虑,又可利用其布衣的身份自由地交通权贵。“每岁春闱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虽出于绹,取舍悉由于滈。喧然如市,傍(旁)若无人,威动寰中,势倾天下。”[35]其二,假装廉洁,不为亲属谋利。令狐绹因其族单,大肆提拔同姓宗人,民间有“天下诸胡皆带令”的讥讽,但是宣宗却始终深信不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令狐绹虽然广引同姓之人,却对自己近属故意不加照顾。据两《唐书》令狐楚本传和《令狐 墓志铭》[36],令狐绹父令狐楚与令狐从、令狐定为兄弟三人。其中令狐定子令狐缄及其二子沨、湘都官宦无闻,令狐从子令狐
墓志铭》[36],令狐绹父令狐楚与令狐从、令狐定为兄弟三人。其中令狐定子令狐缄及其二子沨、湘都官宦无闻,令狐从子令狐 早孤,辗转供职于河中、解县、陕州等转运使院,其仕途同令狐绹没有明显的关系。令狐绹兄令狐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37],但是两《唐书》令狐绪本传俱载其汝州任上坚辞功德牌坊之事。不管事实如何,“明察秋毫”的宣宗肯定会透过让碑这样的小事对令狐绹的“谦逊”心满意足的。其三,不失时机地投其所好,主动向宣宗行贿。晋代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为罕见名画,大中时几经辗转,落入令狐绹手中。一次宣宗闲谈中问其有何名画,令狐绹便将此稀世珍宝进献给宣宗[38]。对这样的善解人意之臣,宣宗自然是宠信倍增。其四,一旦情况对己不利,便动用权力,将事态压制下去。大中九年(855),科场发生泄题丑闻,举人柳翰从裴谂处先得考题,令温庭筠预作答卷,此事弄得满城风雨。因其中涉及令狐绹故人子赵秬,令狐绹怕受牵连,遂将弘词科所有中举者一并落下,连考官也尽加贬逐。当然,有些事情为宣宗亲自察觉,已经无法隐瞒,如擅自令故人便道赴任一事,这时令狐绹就会摇尾乞怜,作出一副“时方严凝,而流汗浃洽,重裘皆透”的姿态,以求得宣宗谅解。宣宗号为明察,实际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奸相的权术之中。王夫之曾言:“夫宣宗之于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贪自己……涂饰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39]此论可谓极为深刻。
早孤,辗转供职于河中、解县、陕州等转运使院,其仕途同令狐绹没有明显的关系。令狐绹兄令狐绪“小患风痹,不任大用”[37],但是两《唐书》令狐绪本传俱载其汝州任上坚辞功德牌坊之事。不管事实如何,“明察秋毫”的宣宗肯定会透过让碑这样的小事对令狐绹的“谦逊”心满意足的。其三,不失时机地投其所好,主动向宣宗行贿。晋代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为罕见名画,大中时几经辗转,落入令狐绹手中。一次宣宗闲谈中问其有何名画,令狐绹便将此稀世珍宝进献给宣宗[38]。对这样的善解人意之臣,宣宗自然是宠信倍增。其四,一旦情况对己不利,便动用权力,将事态压制下去。大中九年(855),科场发生泄题丑闻,举人柳翰从裴谂处先得考题,令温庭筠预作答卷,此事弄得满城风雨。因其中涉及令狐绹故人子赵秬,令狐绹怕受牵连,遂将弘词科所有中举者一并落下,连考官也尽加贬逐。当然,有些事情为宣宗亲自察觉,已经无法隐瞒,如擅自令故人便道赴任一事,这时令狐绹就会摇尾乞怜,作出一副“时方严凝,而流汗浃洽,重裘皆透”的姿态,以求得宣宗谅解。宣宗号为明察,实际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奸相的权术之中。王夫之曾言:“夫宣宗之于吏治,亦勤用其心矣,徒厚疑其臣,而教贪自己……涂饰耳目者愈密,破法以殃民也愈无所忌。”[39]此论可谓极为深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