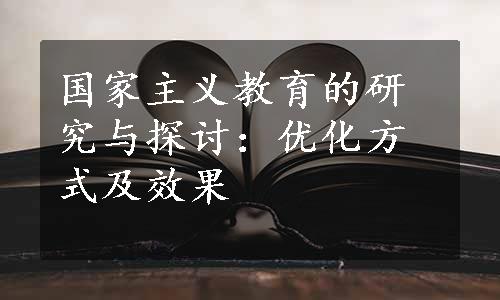
会员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一方面是对欧美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传介,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爱种族观念的吸纳,在理论形式上涵括古今中外的国家主义学说。从现实成因看,五四前后救国救种的现实要求以及受外国侵略刺激而产生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国家主义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可以说,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也是时代的产物。[68]
1.部分会员选择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一种广义的国家主义教育。在少年中国学会关于主义的研究和预备过程中,部分会员倾向或选择了国家主义。“少中”自筹备发起,就存有主义不一致的倾向,但学会对于主义采求大同存小异的策略,期之从各自主义下手共同从事创造“少年中国”的预备工夫。他们认为青年思想与世界潮流是同趋向的,战后世界潮流是变迁最烈的,因之青年思想亦是一种变迁锐进的,故少年中国学会为青年的组织,会员有偏重国家主义的,有偏重世界主义的,亦有偏重无政府主义的,是不一致的,亦不能强同的。[69]所谓偏重国家主义,指涉曾琦、张梦九等人信仰国家主义或国家观念,但尚未形成政治主张。张梦九在1921年对会员的“主义”水准有一个大致估算,他说学会同人真正对一种主义有深厚的研究与明确的判断、信仰终身而一成不变的人,还不多见;“就偶有一二其人,而各人信仰也极不一致,或信仰国家主义,或信仰社会主义,或信仰无政府主义。信仰国家主义的人,既不能强社会主义者以苟同,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亦难强国家主义者以附和,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则又对于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皆极端怀疑”。[70]
析其原因,一是会员尚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主张,“无论对于何种说法、主张,总以‘研究’二字为主,不轻加排斥。因为我们是‘开创’的,‘究理’的,‘大公’的,对于一切事情,都没有成见”。[71]因此,学会尚处于一种没有理论中心的状态。二是在会员心目中,“少年中国”或“中国”是一个地域概念,本非政治意义上的名词,即“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已,“少年中国”只是“少年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少年中国”的意义不是一种国家主义,而是一种世界主义。[72]王光祈明确表示,“我不是抱‘爱国主义’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国弱。并我们人格亦为外人所轻视。则无论如何必与之力争。非至争得平等地位。虽因此牺牲身命亦在所不恤,唯我们与外人力争平等不必取途于‘爱国’”。[73]表明了反对侵略的或和平的国家主义的态度。曾琦也称,所谓少年中国乃指人所生之地域而言,没有狭义的国家主义存乎其间。显然是反对狭义的爱国主义的。可见,从地域观念来理解中国,限制了国家主义在学会的宣传。三是,对新教育的体认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陈启天所说,欧战和苏俄革命改变了人们对国家的态度,原来把国家当作人生归宿,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而摧残人家的国家,而转变为希望超国家的组织。[74]体现在教育上,便是世界主义的教育盛行,国家主义教育成为人们厌恶或谨言慎行的事业。从新文化运动角度反思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以及中国的教育问题,一度在学会内占据主导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主义教育的宣传。
恽代英剖析了自己对国家主义的态度,指出:“只要明白世界大势的人,今天或者亦不至仍拘守着狭隘的国家主义,说什么爱国是人类最终的义务。”退一步讲,中国永远不应发什么做世界主人翁的痴想,亦不应想做无论别国或别民族的主人翁,反过来也不应做别国别民族的奴隶,亦不能让中国亡国与受资本家掠夺。[75]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是国家主义者,而且深恨一般国家主义者以防御为侵略的代名词,使世界人种发生许多嫌怨争哄。其反对的依据,不仅仅是中国现实社会之不需求,还在国家主义学理上之不足。他说:“国家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以为国家既是因人类的需要而自然产生,那便国家的存在,乃是争存的人类不可不十分珍护的。由这样推衍下去,因之他们主张国家有独立人格,是人类最终义务的对象,是可以违背大多数国民的意思以行他[们]所谓有益国家的事的一个怪物。”[76]在恽代英的社会主义认知中,国家的社会主义并非真诚的社会主义,而只是一种国家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主张利用国家的组织,以谋社会利益的,这便是能常所得的国家社会主义。[77]可见,恽代英以其社会主义的有限识见与国家主义的认知,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而主张社会主义。事实上,除一些会员明确表示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的态度外,《少年中国》月刊也刊载了一些宣传世界主义反对国家主义的译作,[78]大致也可代表当时会员的主义倾向。
少年中国学会在1920—1921年正值鼎盛期,会员热心于社会活动的同时,专心于个人求学和道德修养,学会负责人王光祈自鸣得意地说,“本会初发起时,尚有二三主张国家主义之人。经三年来之酝酿,亦皆慨然弃其主张。故今日会中虽不标明主义,而各人信仰,起码亦系社会主义。所未能一致者,不过实现之方法及其组织耳”[79]。应当指出,王光祈所言“社会主义”是一种泛社会主义,对于其中的国家主义持一种相当宽容的态度,与恽代英在《论社会主义》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的分类相比较,可以看出把国家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在学会内部并未引起争论,《少年中国》第一、二、三卷基本上没有从正面来宣传国家主义的文章。这固然与月刊编辑方针不无关系,但也表明“少中”作为一个学行并重的团体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包容力。最为关键的是,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分歧尚未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化而达到非此即彼的对抗地步。用王光祈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反对国家主义的人,我以为国家只是一种政治组织,可以随时取消的。不过国家主义虽不必主张,而民族主义却不可不提倡,我所说的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拿我们民族去侵略他人的民族。只是主张我们这种又勤又俭的民族、素有文化的民族,要在世界上谋一个安全的地位”。[80]其实,王光祈“反对”国家主义而提倡民族主义,实际上又难与国家主义相分离,其依据还在于“国家”是团体与组织,而非政治概念,显然忽视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内容。立足于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把国家主义也视为团体预备工夫的内容之一。他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缺少团体的训练,所以缺乏一种互助的精神。国家是一种团体生活,国家主义便是主张缩小个人自由,从事国家生活,造成一个最强固的团体——国家,因而“少中”的预备工夫自当包容这一点。[81]他把中国人不爱国归之于“未经过团体生活之训练”,因此提倡国家主义还须从团体训练入手。看来,王光祈反对的是国家主义的内容,提倡的是国家主义的团体训练的方法,并希望能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信仰者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推动“少中”的团体训练之预备工夫。所以他在“少中”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填写“不完全反对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认为各有其用,也可资证明。
总的说来,对于主义问题,学会坚持“从事深悠苦索之研究”的预备工夫,对于国家主义同样采取一种切实研究的态度,研究内容涉及国家主义理论的历史及流派,各国实施主义的组织现实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现实生活状况和对主义的需求状况,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及其精神等等。在此期初步研究中,一些会员明确表示反对狭义的国家主义,应当说是一种学会宗旨所标榜的科学精神的体现。
2.主张国家主义教育的趋向更加明显
从学会的教育思想与活动来看,内部大致隐含着普通的启蒙教育与革命教育的分野。就民主主义的教育而言,无论是教育方法还是教育手段,则大致相同:第一步预备工夫便是唤醒民众,集合起来便是革命的力量。要达到这一认识,一方面要从“革命的经验知道自家的利益是靠不着别人的”,一方面还全是靠教育的能力,养成真正的舆论,使大多数人自己觉着他们的力量。[82]从舆论和风俗革新立论,李璜比较了五四爱国运动与欧西的爱国主义,认为五四运动以爱国为帜志,但其中因为爱国而强迫群众爱国以致引发冲突,这是平时没有舆论预备工夫的缘故。欧洲人国家主义的力量则是雷霆万钧,以致欧战一起,无论智识最高的学者,还是主张最激烈的社会主义者,都甘心赴前线去拼命,很少听见个人反对去上阵效死的。这种力量及中西社会对比,使李璜不得不佩服这班国家主义者预备工夫的深厚。这种工夫不仅体现在从初等小学校的课本以至于大学校的讲演天天都在介绍青年爱国的道理,而且出了学校受爱国报纸的影响更大,“可以说欧洲人的国家主义到现代简直注射到各个欧洲人的血里去了,脑经[筋]里装满了他,一举一动无不呈现他的色彩。”[83]他明确表示不十分赞成那种狭义的国家主义,但应当仿效这种建设舆论的方法。而且他认为,法国民主革命的舆论预备工夫既是革命成功的先例,也造成了群众灵魂里预卜国家主义的命运的结局,又认为列宁从俄国革命经验中认识到抬高群众的程度,也是至理之言。正是以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为借鉴,他把高谈新主义而与旧势力接近,称为“怪现象的接近”,张梦九则称为“不彻底”的态度,曾琦甚至认定“彻底主义者,吾党之信条而亦实成功之妙诀也”。[84]由此可见,对于民主主义的信从,尤其是对于国家主义教育方法取“彻底主义”的态度,影响了其后他们对国家主义的信仰和追求。
如果说在学会初期以教育为创造“少年中国”的预备工夫,尚未上升到明确以国家主义为教育宗旨的地步;那么,李璜、左舜生、杨效春针砭中国教育现状,讨论教育方针的通信,无疑提供了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一个渐趋明确的信息,为尔后的国性、民族性的教育提供了思想线索。教育是一种革命的武器,它可以被有计划地用于助长民族整合、爱国主义和新价值的形成。由此来看,“少中”会员尽管对国家主义颇有物议,但民族主义始终是一种共同的趋向,因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教育与国家主义“联姻”充当了媒婆的角色。(www.zuozong.com)
从会员的教育思想发展来看。左舜生立志以教育来改造中国,杨效春颇重中学教育。李璜虽未经手教育,而在法国亦留心考察法国教育改造的历史,并以平民教育为职志,因而在如何发挥教育的社会功能甚至“教育救国”方面,三人自然有着共同的话题。李璜数年来留心中国社会,到欧洲后复与欧洲社会接触,“以种种现象,归纳结果知非从初级教育下手,则其他皆是空言”。不仅如此,“东方民族以后之进步,是否还循西方民族迂曲迟缓之过程,皆取决于此时训练子弟之精神与方法如何”,他希望同人精深极虑之。他详考法国教育改造经过后向左舜生建言:一宜首定理想之宗旨,一宜研究一贯之方法。联系到他后来公开表示不当中小学教师便去革命,当中小学教师还是为实现真正的革命,但又把革命当作万不得已的事情,可知教育在他的社会改革论中的地位,法国教育改造给他的深刻影响。针对李璜以法国教育宗旨来衡量中国的教育宗旨,杨效春提出异议。他全面回顾了晚清以来教育宗旨之变迁,认为中国教育并非没有宗旨,而是有宗旨却没有切实实行或行之不得法,没有实现出效果而已。如何确定理想教育宗旨,李璜认为:教育之理想宗旨须随地方与民族变革,不能一味采用他国之教育宗旨。在他看来,无论法国之自由主义教育、德国之军国主义教育、美国之民主主义教育,还是日本的模仿主义教育,皆有其是处,皆有其宜处,但鉴于中外国情之区别与时代之差异,“吾人欲定教育宗旨,当自审国人之天性与所处之时代,最擅教育者,莫过于启发国人天性之所长,而使其适应生存于所处之时代”。[85]意思很显然,他反对中国一向以来的搬用外国的教育宗旨而制定中国之宗旨,批评在教育模式上完全仿效日本于前,搬抄欧美模式于后。他的结论是改变中国教育无宗旨之弊病,借鉴法国等国的教育宗旨,制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与时代要求的理想教育宗旨。但无论德国、法国、日本还是美国,其国家主义教育是非常实用且明显的,从而为在中国确立国家主义教育宗旨提供了一定思想基础和历史依据。后来国家主义派反复谈及确定国家教育宗旨问题时,持论大致同此,只是更加具体而深化。
杨效春从世界主义教育的角度批评李璜“国家观念太浓”,并非无的放矢。他认为,谈起教育应把国家的观念避开,教育是没有国界的,一旦染了国性,就会磨灭个人的人性,因而主张“善教育者,是能启发个人之所长,而使其适应生存于所处之时代”[86]。有意思的是,李璜强调的是“国人”,杨效春注重的是“个人”,两者相映成趣,大致分别指涉民主(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两种路向,在教育上一是追求教育理论的完善,一是追求教育的中国化,因而在教育的理解及教育理论上呈现分歧。在杨效春看来,各种主义是不同时势的反应物,而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创造出来,教育方面的主义冠以国名是不可取的。证诸史实,欧战以前各国的教育无不带军国主义的色彩,欧战以后的教育又渐渐采用民主主义了。“所以我们的教育要采用什么主义,或注重什么主义,只须看时势,不必问什么国情。”[87]他的态度很明确,教育上不应有一种无上的特殊的固定的主义,教育是人类的事,不应当做国家的工具,学校的理想应该表示人类的理想,不应该表示国家的理想,否则便有重新开启恐怖战争的可能。[88]杨效春从时势或社会要求、个性的发展立论,坚决反对以国家主义作为教育宗旨,或者说教育宗旨带上国家主义色彩,与李璜以教育为国家的工具的旨趣大相径庭。可见,西方教育理论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土壤上滋生出各式各样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教育理念,经教育家或理论工作者兼融为不同的教育思潮,又在不同场合付诸实验,形成不同的教育思想。后来杨效春亦提倡与李璜等人的国家主义内容迥异的国家主义,且加入中国青年党,似乎很难令人理解,大概爱国之念或教育救国的动机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或者说是时势的需要与国家的要求在一定时期的契合交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王光祈由反对国家主义到后来同情于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亦大致类此。
倾向国家主义的舒新城对中国的教育目的产生了疑惑。他依据个人经验并列举国人只注意于枝叶的学制、教法问题而忽视作为舟中之舵的教育宗旨的事实,认为其造成的后果,“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最大多数的中等学生,至除死读英文数学以为升学或炫人的工具以外,不知社会国家为何物,其次则受主持教育者之陶化而为拜金主义,伟人主义,势力主义者之走卒”,所以现在的教育不仅谈不到救国,即便学生个人之生活技能,反不及从前的徒弟,而为一般人所诟病,故提出以国家主义的教育为宗旨。[89]而欧洲国家主义教育的救国先例,自然成为仿效对象乃至依样画瓢的蓝本。正如时人所言,“近顷以来,一部分的爱国的教育家,内感于国势愈趋愈下,外感于世界列强立国政策之未变战前态度,于是毅然提出‘国家主义教育’,以期引起全国教育界人士之努力,共同集中于延续将斩的国命之运动,而唤醒大同主义者之迷梦”[90]。
按照国家主义派会员的解释,民主主义、世界主义是与国家主义相容的。以上各种主义都可服务于或服从于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具体说来,杨效春坚持确定教育宗旨的标准为:(一)有伸缩之余地,应随人随时随学校之性质而变迁;(二)应兼收并蓄,吸收各种主义之长,对各种主义取持平态度;(三)应切于事情,从事情中创造出宗旨。[91]从教育理念上看,杨效春倾向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他希望的是学校为社会的缩影,社会为学校的扩张,学校能社会化,又能化社会,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使学生同时对校做个好学生,对外便是好公民。[92]李璜则认为“教育是预备生活”。这一讨论虽从中国历史沿革与西方教育之得失着眼,尚属草创之作,也可以说是揭开了“少中”内部国家主义教育与世界主义教育论争的序幕。
学会坚持以教育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希望会员为中国的教育制定一个固定的宗旨。李璜通过研究法国教育的改革,以法国教育为参照来批评中国的教育,他自称与杨效春、左舜生谈教育的信,“句句是为中国的现状而言”,即针对于中国“病态的社会,并且那个病遗传和传染的力量都是很危险可怕”。他提倡的教育,就是要想法医治这个病,不然一切说法都是枉自费力。[93]杨效春“忽视”了李璜的这一急切“救病”的前提而推论其国家观念太浓,忽略了李璜以救国为目的,实现民主社会这一预设,反而不被李璜所承认。其实,李璜根据中西教育之比较,主张学生与那种社会生活暂时隔离,甚至主张实行“儿童公育”,他的出发点在于,要去创设新鲜空气的社会,不是孤立,也不是卢梭的爱弥尔教育的主张。[94]其现实依据,一是中国青年为不正当之书所诱惑而为浪行者甚多,二是似是而非之理学书、哲学书(如先秦诸子以至宋明儒之说),亦非判断力未成的中小学生所宜;时事报章徒乱中小学生之心思,而丝毫无补于学识与政治,亦绝对禁止购阅。[95]这一主张是基于“实现真正的民主社会,启发创造之科学思想”的考虑,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教育主张。说它是一种教育救国论也未尝不可,问题就在于救国教育与民主教育孰先孰后,孰主孰从,则取决于时势与社会的要求。但是他着眼于国家的教育,自然是后来提倡国家主义教育的现实根源。由民主主义教育到国家主义教育或共产主义教育的转型是时势使然。会员吴俊升回忆当初写作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时说:“我的教育思想,由赞同当时以杜威思想为主的自由、民主及国际主义的立场,渐渐加以修正和补充而兼顾民族文化的延续与发扬和爱国主义的提倡,实与青年党人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诸会友所倡导的国家主义教育同调。”[96]由此可见,一些会员对于民主主义教育与国家主义教育没有严格的区分。此外,倾向国家主义的杨效春与信仰共产主义的恽代英讨论学生自治问题,也大致体现出不同的教育理念,从而走上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观诸近史,推崇教育,以教育为救国之唯一法门者不在少数;救国的教育,也不止国家主义教育一种。但是真正对国家主义教育作系统的有组织的宣传,是倡导教育建国论的国家主义派,其中又始于余家菊、李璜出版的《国家主义的教育》论文集,以及南京会员在《少年中国》公开讨论并确定新国家主义的定义。在1924—1925年间,国家主义教育“盛极一时”。许多教育刊物,如《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教育与人生周刊》《新教育评论》《国家主义与教育》等都刊登了大量研究和宣传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以教育救国,用教育来促进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在此基础上,《醒狮》的创办,成为国家主义运动兴起的一个显著标志。如陈启天所言,《醒狮》出版最大的影响为“各地爱国青年团体风起云涌”,最大的成就是“为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学会内部,《国家主义论文集》《国家主义讲演集》《建国政策发端》等宣传国家主义教育的著述作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出版,也可以说代表了学会的一种思想倾向。陈启天非常明确地说,“国家主义在我国建立起一种系统理论,可说是从我们这几本书开始”[97]。确如所言,这些著述奠定了国家主义教育救国论的理论基础,而且对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会员包括国家主义派都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致力于国家教育的统一与民族的独立。诚如余家菊所说:“我提出国家主义,纯然站在教育的立场。我要唤起青年以国家为至上,为国家而努力。”[98]
不仅如此,国家主义派会员试图容教育救国与经济救国于一体,联合共产主义派开展革命。李璜在1924年4月24日给恽代英的信中强调:主张教育救国,是先认定了教育的价值是能够在人的精神上产生很大限度的影响,所以才加以研究后,很诚恳地来提倡。“我们以为主张教育救国者固然该当去提倡爱国精神,而主张经济救国者也一样的该当去提倡爱国精神:这两种提倡是相辅而效益彰的。”[99]言下之意,国家主义派是教育救国论者,共产主义派是经济救国论者,两派会员应当联合开展革命,共同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但是,随着共产主义派反对国家主义日益激烈,国家主义派反“共产”意识进一步强化,在教育理念上鼓吹国家主义的教育以对抗共产主义者主张的世界主义的教育或革命教育,民主主义的教育就为国家主义教育所取代而在学会成为“主流”思想。由此,“国家主义教育”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国家主义教育成为盛极一时的社会思潮,并从中涌现出了对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宣传与研究最有力的余家菊、陈启天、李璜、曾琦等人。而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会员如吴俊升、舒新城、谢循初、左舜生、杨效春等也发表了一些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文章及参加一些国家主义派组织的教育活动,共同促成了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少年中国》是学会的机关刊物,也大致代表了学会的立场和观点。如果说前三卷或说在1922年底以前更多的内容关涉会员讨论学会主义问题和关于教育宗旨方法等社会改造理论层面的问题;那么,从第四卷开始则出现了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长篇大论以及频繁的通信讨论,涉及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且随着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的勃兴,国家主义教育在学会内部开始以团体主流思想的形式出现。这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会员努力奋斗和实践以顺应潮流的结果。尤其是旅欧归来的国家主义派与国内同情并宣传国家主义教育的会员合流,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宣传国家主义教育,迅速形成学会内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