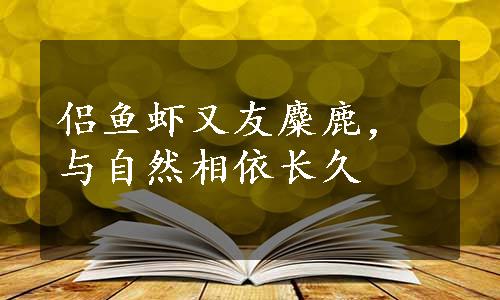
普利什文是谁?米哈伊尔·普利什文(1873—1954年)是俄国杰出的散文大师之一。
其散文内容,是以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唯一对象,因此普利什文获得了“俄国北方自然的发现者”“鸟儿、大地和星星的歌手”“大自然的歌者”等诸多称谓,而他曾自称“一位视万物皆似人的泛灵论者”。
其散文风格,特别在文体上有着清晰的识别符号,篇章放在任何一部合集中都可以轻易地被识别出来,普利什文将自己的体裁定义为“诗意地理学”。所谓“诗意”,是用言简义丰的诗歌来写散文,他自己说“一生都在为如何将诗歌置入散文而痛苦”。“地理学”,将自然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看到了一般人注意不到的现象,得出了一般人推断不出的结论,其关于自然和人类的体悟思考之深可知矣。对自然诗意的描摹、富有哲理的沉思,再加上日记体和格言式的文体、从容的节奏和亲切的语调等等,这一切合成了“普利什文风格”。这种散文风格已被公认为世纪俄语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阅读《普利什文散文》,最让我感动的莫过于两点。
第一,普利什文具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对事物明察秋毫。
普利什文一辈子住在森林里,一辈子写森林,对每一种动物、每一种植物、每一类现象和每一个瞬间,对它们的习性、生长和变化,如数家珍。其实一辈子写森林的作家不在少数,但是能达到普利什文水平的却少之又少,关键因素之一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普利什文在《林间小路》中如是说道:“我记得,当初我住在湖边一处废弃的豪宅里,从光的春天刚刚开始的日子起,每天都写观察日记……”“每天都写观察日记”,如此观察,连一丝纤尘也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普利什文曾写过一篇《沼泽》,一见“沼泽”二字,大多数人脑中立刻浮现出这样的情境:茫茫一片,望不到边;没有树木山岭,单调乏味;野兽踪迹罕至,毫无生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认为,可能看到好多书就是这样描写的。实际我们并未用自己的眼睛或者没有机会去观察,只是人云亦云罢了。
而普利什文笔下的“沼泽”,简直就是各种鸟儿的天堂:“我常常发现,远在曙色迷离之前,这音乐会的第一个音符是杓鹬唱出来的。那是细声细气的啼啭,全然不像人人熟悉的那种啁啾。后来白山鹬叫起来,黑琴鸡也就放出啾啾之声,发情的雄黑琴鸡有时就在棚子边嘟嘟囔囔起来。这时候,往往还听不到杓鹬的歌声,但是一等旭日东升,到了最辉煌的时刻,你一定会发现杓鹬便引吭高歌了。那歌声十分欢快,像是舞曲:为了迎太阳,这舞曲像鹤鸣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常常”一词说明作者并非观察一次,而是多次,否则怎能辨出“第一个音符是杓鹬唱出来的”,且声音有别于“人人熟悉的那种啁啾”的细声细气的啼啭,又在“曙色迷离之前”。“一等旭日东升”,杓鹬不会再“细声细气”了,一定“引吭高歌”。在众多的鸟儿中,作者能区分出哪种鸟儿先啼叫第一声,哪种鸟儿发出第二声;各种鸟儿的叫声各不相同,同一种鸟儿不同时间叫声也不相同,雄鸟、雌鸟叫声也有差别,人们熟知的是一种叫法,还有人们所不知的。
即便是一滴水,在普利什文的笔下也被描写得细致入微。“许多闪着金光的水滴直接落在地面上”,水滴在太阳光里着上了金色的外衣,“闪着金光”;“但是更多的水滴是从小树枝上流到大树枝上,又从大树枝弯弯曲曲地顺着树干向下流,一直流进土地中”,更多水滴流到土地的道路曲折,分三步走。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般,将水滴的曲折之路无限夸大,也将水滴奔向自由的快乐之感无尽渲染。“在阳光灿烂的白天,橡树整个巨大的树身都发出耀眼的银光”,水滴流满了橡树整个身躯,阳光之下,熠熠生辉。
是什么原因让普利什文如此兴致勃勃地在充满危险和艰辛的森林里耐心观察和不懈写作?应该是他对大自然的深情。这也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普利什文主张人类在面对自然和自然中的一切时应保持一种“亲人般的关注”,这种主张后来也成了他的生活和创作态度,成了他的世界观。大自然就是他温暖的家,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他的亲人。普利什文在《我母亲的梦》中如此抒写他的深情:“但自然却在安睡,和亲爱的母亲做着同样的梦;她睡着,和亲爱的母亲一样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关照我,我砰的一声关上车门,跳过壕沟,此刻正默不作声地坐着,而她却不安起来,——他哪儿去了?他出了什么事?”“我赶忙咳嗽了一声,她这才放下心来:他在某个地方坐着呢,也许在吃东西,也许在幻想着什么。”
自然就像亲爱的母亲一样关爱着“我”,“我”也像眷恋着母亲一般眷恋着自然。一位作家对自然的温情,也莫过于此了。(www.zuozong.com)
在普利什文看来,大自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甚至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和现象都有生命:沼泽里小鸟姬鹬,“在它那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中,也含有所有沼泽欲回忆点什么的永恒、枉然的一致企图”;森林里每一朵小花,“都是一轮小太阳,都在叙述阳光和大地相会的历史”;冷冷的冰块,“要在阳光下饱受煎熬,直到橡树体内的树汁开始活动的时候,它才会在一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突然滑进河里,变成水”。
如此的创作理念,让普利什文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站立,我成长,——我是植物。
我站立,我成长,我行走,——我是动物。
我站立,我成长,我行走,我思想,——我是人。
我站立,我感觉:在我的脚下是大地,整个大地。
脚踏大地,我挺起身体:在我的头顶是天空,我的整个天空。
这时,响起了贝多芬的交响乐,它的主题就是:整个天空都是我的天空。
这是一个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的形象。普利什文写自然,其实就是在写人,将自然视为“人的镜子”。他在《跟随魔力面包》中写道:“研究作为自然的民间生活形态,也就是在研究全人类的灵魂。”反过来,他又把对人类的情感投射到了自然里,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作为“大自然的歌者”的普利什文,他“对大自然伟大的爱来自他对人类的爱”。与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人和谐共生,普利什文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图。
《普利什文散文》让读者怦然心动的不仅仅有以上两点,那只是笔者一家之言罢了。要想获得更多的自己的感受,我向同学们建议:读一读普利什文吧!
【注释】
[1][苏]普里什文.普里什文散文[M].潘安荣,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