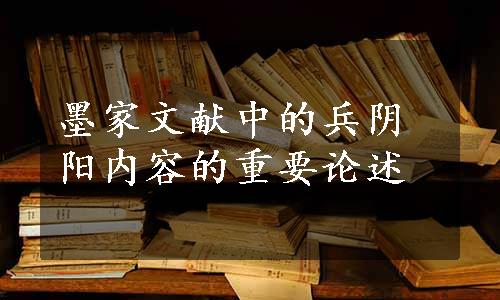
《迎敌祠》的部分内容,学者称之为迷信,如岑仲勉指出:“《墨子》这几篇,除了极少量的宗教迷信之外(如《迎敌祠篇》之一部)……”[152]史党社亦称其为“军中迷信”[153]。根据《汉书·艺文志》对兵学著作的分类,其中兵阴阳家16家,249篇,图10卷,今皆失传。现在出土文献已经发现了部分属兵阴阳家的文献,如张家山汉简《盖庐》[154]等,《墨子》一书中的《迎敌祠》《号令》从性质上来看,应属兵阴阳家,其时代更早,更弥足珍贵,我们以下对其主要内容进行论述。
首先,以望军气为代表的具有迷信色彩的内容。望气之法是古代一种通过观察云气变化来预测吉凶的方法,主要用于军事行动,因此称之为望军气。望气之法在当时是非常兴盛的一门方术,如,《汉志》“兵阴阳家”中就有《别成子望军气》《常从日月星气》等望气的专书。在《墨子》中就有类似的记载:“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155]望气术由来已久,我们在《左传》《国语》《周礼》等文献中都能看到相关的记载。所以说,我们与其说其为墨子特有的兵学思想,不如说是墨子对传统思想的一种继承或者认可。至于什么是“大将气”“小将气”“往气”“来气”“败气”,墨子并未有细致的描述,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根据《迎敌祠》的基本描述以及基本语境,我们认为这些记述应当是对敌方军气的描述与判断,所谓“大将气”“小将气”是指对敌方将领的判断,“往气”“来气”也是对敌方军事行动具体去向的判断,“败气”亦为敌方情况判定。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方术在具体的战争中往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如对“败气”的描述,在推翻王莽政权具有战略决定意义的昆阳之战中就有“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156]的记载,结果“吏士皆厌伏”[157],甚至成为了一个影响战局的重要事件。然后我们看唐代李筌《太白阴经·杂占·占云气篇》谈到“败军之气”时谈到“云气如坏山,从军营而坠,军必败”,相关的内容如出一辙。所以说,望气法的影响持久而稳定,因此《太白阴经·杂占·占云气篇》开篇便谈“天地相感,阴阳相薄,谓之气。久积而成云,皆物形于下而气应于上……积蜃之气而成宫阙,精之积必形于云之气,故曰:占气而知其事,望云而知其人也”。其具体描述的“猛将气”“胜军气”“败军气”等都是渊源有自,对我们理解望气法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望气法,现代学者往往斥之为迷信,因此,相关研究非常薄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我们今天认为非常不科学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军事行动中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号令》记载:“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上报守,守独知其请而已。”[158]因此,我们能够看出,这些负责望气的专职人员,属于主将的心腹人员,一定要居于主将的住所附近。同时,在消息传达方面也有着非常严格的控制。望气者必须将对己方有利的信息迅速及时地传达给全城的百姓,而具体的实际情况仅仅汇报给守城主将一人。若是望气者将不利于守城的信息传出,那必将杀无赦:“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弗赦。”[159]在《迎敌祠》中亦有几乎类似的记载:“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之,善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守,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160]在军中,这些望气者与巫祝有很高的地位,“善为舍”“必敬神之”,当然对于具体卜得的吉凶仅对主将负责,同时主将还对他们进行观察、监视,随时处罚那些“为流言”者,处罚也是非常严厉,“断罪不赦”。对于望气法,军中主将非常清醒,这仅仅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军、统军方式而已,类似于后世儒者所言的“神道设教”。因此可以看出,在军中,这更多是一种激励士气的方式。
《墨子》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非常具有仪式感的战场礼仪,其中一些内容也可以与儒家典籍相参照,这些内容也往往具有巫术和迷信的意味。我们认为其中大多还是以阴阳五行为基本的原理,或者其本身就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如根据敌人所来之方向,往往有不同的战前祭祀仪式,据《迎敌祠》记载:“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墨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祷焉,给祷牲。”[161]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套非常成熟、具有仪式感的战前礼仪。此段记载主要描述了战前根据敌人所来方向祭祀四方之神祈胜的相关巫术和礼仪。其中,对筑坛高、堂密[162],主祭者人数与年龄,祭旗颜色,神主规格,发弩数,主将服色以及所用牺牲,均有非常严格细致的讲究和规定。至于为什么对应如此的颜色与数字,我们仅以东方为例来说明其中的核心要素。东方对应的是青色,《说文解字》曰:“青,东方色也。”[163]《考工记·画缋》亦曰:“东方谓之青。”[164]而东方的礼仪中处处对应的数字均为“八”,如“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据《黄帝内经》曰:“东方青色……其数八。”[165]而为什么必须是“其牲以鸡”,同样根据《黄帝内经》:“东方青色……其畜鸡。”[166]其他方向亦是如此。我们认为这些礼仪细节都渊源有自,背后有一套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根据的理论。据学者研究,我们认为其也有可能与中国古代的式法有一定关联。[167](www.zuozong.com)
在《迎敌祠》中还有类似于后世儒家典籍所载的一些战前祭告山川社稷的具体仪式。[168]如,战前要进行相关的誓师:“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先于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庙,曰:‘其人为不道,不修义详,唯乃是王,曰:“予必怀亡尔社稷,灭尔百姓。”二参子尚夜自厦,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于中太庙之右,祝、史舍于社。”具体而言,战前由祝、史等祭祀专职人员主持具体祭祀,祭祀的对象主要包括四望、山川之神、社稷之主。这些内容在典籍中都有相应的记述,如,有关“四望”的记载,据《周礼》载:“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169]贾公彦对具体礼仪解释道:“言四望者,不可一往就祭,当四向望而为坛遥祭之,故云四望也。”[170]孙诒让更指出了“四望”礼仪的政治含义:“四望者,分方望祭之名,通言之,凡山川之祭皆曰‘望’,于山川之中,举其尤大者别祭之,则有四望。天子统治宇内,则四望之祭,亦外极四表。”[171]至于“社稷”更不必言:“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172]而君主与将士告于太庙的内容更是从宗教上保证战争无可怀疑的正义性。祭祀与誓师仪式结束后,国君则是居住于太庙之右,而祝、史等人则必须在社中进行祭祀或祈祷,以获得神灵的福佑。在此之后还有一些军礼性质的程序和仪式,当然祝、史等人员也参与其中,其曰:“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门,右置旗,左置旌于隅练名。射参发,告胜,五兵咸备,乃下,出挨,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马射自门右,蓬矢射之,茅参发,弓弩继之;校自门左,先以挥,木石继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173]而战争开始后,根据春秋时期的军礼,庙主与社主也是随军队而迁,在作战过程中,祝、史等人也随时祭祀并报告相关战事的进程,以求鬼神的福佑。
当然,这种方式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其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在《史记·田单列传》中记载的田单固守孤城即墨时,当士气并不振奋时,田单正是以一士卒为神人,“每出约束,必称神师”[174]。田单借助鬼神的举动在整个即墨城保卫战中对士气、民心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进而对齐国的历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先秦时期兵阴阳家的内容,甚至认为是迷信的一些举动,必须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理解,才能真正发现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而非简单予以批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