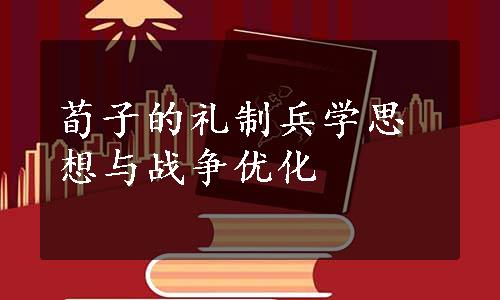
荀子,名况,号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汉人避汉宣帝刘询讳,称为孙卿,又称孙卿子。根据汪中《荀卿子通论》[48]之《荀卿子年表》考证,可知荀子的政治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赵惠文王元年(前298)至赵悼襄王九年(前236)这63年间。又根据廖名春[49]和梁涛[50]考证,荀子的生年约为公元前336年,卒年约为公元前238年或之后不久。在政治活动上,荀子与孔子、孟子经历相似,一生游说各国,推行自己的主张,虽受到各国统治者的礼遇,但不被重用,仅被楚春申君任用为兰陵令。但是荀子在学术上的成就是辉煌的,就当时学术影响而言,他在齐国稷下学宫“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为稷下“列大夫”之首。[51]《荀子》一书最先由汉代学者刘向编订为《孙卿子》32篇。唐代杨倞再次整理,仍为32篇。
就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而言,荀子是先秦继孟子之后的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创新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正如冯友兰所说,“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52];他同时也是战国“百家争鸣”后期对先秦诸子思想均有批判吸收的集大成者,正如胡适所言,“研究荀子学说的人,须要注意荀子和同时的各家学说有关系”[53]。作为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兵学思想也是先秦儒家兵学思想的最系统的总结者与最权威的诠释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形态,我们认为它的基本内涵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区分战争的性质,提倡以吊民伐罪为宗旨的“义战”。
荀子根据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十分强调对战争性质的区分,他把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战争明确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在他看来,凡是基于吊民伐罪、拯民于水火之中的立场而从事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合理的,应该拥护;反之,凡属于以满足统治者私欲为宗旨而进行的战争,则是非正义的、逆天背道的,应该加以谴责和反对。这是其兵学思想中的一个根本性观点。
荀子认为那种拯民于水火、吊民伐罪,为实施仁义而开辟道路性质的“义战”,不是虚幻的想象,而是普遍存在于历史上的:“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54]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义战”也是应该成立并积极推行的。荀子进而指出,“义战”顺乎天而应乎民心,“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因此必定是所向披靡,无敌于天下:“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55]
“义战”既然如此合乎天道人心,又这样成效显著,荀子据此而得出结论,从事“义战”,就是用兵的最理想境界,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应该执着追求的战争宗旨:“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56]
荀子既然将战争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礼治、德治原则的推行与实现,那么他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战争活动也就采取基本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了。在荀子看来,与“义战”相比,社会生活中“不义之战”要多得多,它们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
荀子生活的战国末期,正是战争高度频繁、激烈,其后果日益残酷的阶段。然而荀子拿自己的政治原则与当时的战争现实进行衡量,衡量的结果是将当时顺应历史进程的战争定性为“不义之战”,予以抨击和斥责,反对动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指出“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57],并强调倚恃武力的恶果:“非贵我名声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势,故民虽有离心,不敢有畔虑,若是则戎甲俞众,奉养必费,是故得地而权弥轻,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58]
由此可见,荀子所秉持的是“义兵”至上、“礼乐”为先的基本立场,对兵家“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59]的观点予以全盘的否定。《荀子·议兵》的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荀子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态度:“为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无礼义忠信,焉虑率用赏庆、刑罚、势诈?除阨其下,获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则至,使之持危城则必畔,遇敌处战则必北,劳苦烦辱则必奔,霍焉离耳,下反制其上。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60]
显而易见,荀子区分战争的性质,明确提出“义战”与“非义战”的对立范畴,这是其兵学思想,更是其战争观比较成熟的标志。先秦诸子中其他学派虽然也对战争的“义”与“不义”性质有所阐述,但就深度而言,却不如荀子。应该说,荀子的认识为中国古代兵学价值观的确立提供了坐标,也为后世兵学思想发展“兵儒兼容”主流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突出战争对政治的从属关系,表现出显著的民本主义色彩。(www.zuozong.com)
荀子的学说与孔、孟一样,是一种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其兵学思想在其整个理论建构中居于从属的地位,强调军事对于政治的依附从属关系,乃是其兵学思想的特色之一;而崇尚民本、重视民心归向对于战争成败的意义,则是荀子兵学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荀子是先秦儒家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对军事从属于政治、民心归向决定战争胜负的认识可谓是十分深刻与透彻。他肯定“仁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指出:“故古之人有以一国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修政其所莫不愿,如是而可以诛暴禁悍矣。”[61]
为了达到这一理想,荀子认为,一是要提倡附民爱下,力行仁义,其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轻为之死。”[62]又曰:“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63]二是要修礼。荀子视礼为“治辨之极”“威行之道”“功名之总”,认为只有尊奉礼义,遵循制度,尚贤使能,教化百姓,顺从民心,才能造就军事上的强盛:“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故藉敛忘费,事业忘劳,寇难忘死,城郭不待饰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劲。”[64]否则,便会民众离心,导致军破国亡:“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65]由此可见,荀子始终把政治清明、民心向背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强调只要赢得民心,便可以无敌于天下。而争取民心的关键,在于修明政治,推行“仁政”与“礼乐”。荀子兵学思想中的这种民本精神,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兵学思想的发展不无积极影响。
第三,文武并举,致力于军事建设;尊卑有序,提倡以“礼”治军。
荀子沿着孔子的思路前进,在具体的军队建设措施方面,提出了不少精彩的意见。首先,是要顺从民意,以民为本,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参加军队建设事业,尽可能使民众与统治者的意愿统一起来。其次,主张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建设起一支能征惯战的强大军队,并注意营造一种清明和谐的政治环境,以求在战争中牢牢立于不败之地:“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66]当然荀子军队建设的主张与法家等学派还是有重大区别的,这就是它以仁义为本,而不是一味推崇暴力,迷信武力,所谓“无兼并之心”和“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67]云云,正反映了荀子兵学思想的独特性格。
荀子在治军问题上也有比较系统的主张,其基本内容是提倡以“礼”治军,重视将帅道德品质的修养,强化军队内部的等级秩序,这一切正是荀子“礼治”理论在治军问题上的具体反映。荀子讲究“礼治”,在治军上就是主张运用“军礼”来治理军队,指导各方面的工作,以期行必中矩。孔子曾就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68]所谓“军礼”,就是军队根据儒家礼乐精神具体制定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到了荀子那里,对“礼治”的强调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礼乐”成为了军队强盛、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上不隆礼则兵弱。”[69]又曰:“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70]
在治军中认真贯彻“军礼”的基本前提下,荀子十分强调将帅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对将帅品德修养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发,其曰:“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71]又曰:“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72]荀子认为,能够做到以上几点,这样的将帅一定是杰出的将帅:“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73]
第四,荀子兵学思想的包容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之间交流的增强,先秦诸子代表人物也渐渐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自己思想主体性、肯定自己思想正确性这一前提下,借鉴和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荀子对此有比较集中的反映。他一方面同样尖锐地抨击除自己学说之外的诸子百家,撰写《非十二子》系统批判先秦诸子的学说,并提出了自己的统一思想:“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74]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承认和肯定不同学派具有某些合理内涵:“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75]这表明,从战国中期起,学术思想的交流兼容在思想对峙斗争的情况下,已渐渐地开展了起来。
这种学术发展史上的新气象,同样对荀子的兵学思想的构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之长的强烈的时代特色,这在其兵学思想方面也同样有鲜明的体现。他一方面同其他儒家一样,也崇尚人本精神,构筑用兵的理想境界,提倡“仁义”“礼乐”,主张行“仁义”之师。但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性,故退而求其次,也一定程度上肯定霸道的地位,将军事上的成功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次的,即王道的层次;二是低层次的,即霸道的层次。这样荀子比孟子等儒者就大大前进了一步,使自己对战争问题的思考从政治学领域真正跨入了兵学领域,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