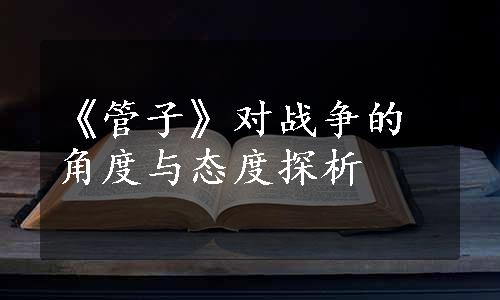
《管子》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305]《管子》指出,战争虽然算不上高尚的行为和道德的手段,但在当时天下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不可或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306]所以,《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务必“积务于兵”,即注重和开展军事活动,指出假如“主不积务于兵”[307],等于是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敌人,危险之至。基于这一认识,《管子》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认为兵不可废置。它说,即便是在黄帝、尧、舜那样的盛世,都不曾废弃兵事,那么“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308]。所以宋钘、尹文提倡的“禁攻寝兵”[309]和墨家鼓吹的“兼爱之说”,在《管子》作者的眼中,纯属于亡国覆军之道,必须痛加驳斥:“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310]从以上论述看,《管子》的基本立场是主战的。
《管子》在充分肯定战争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它认为战争本身是充满危险的事情,其曰:“兵事者,危物也。”[311]又曰:“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312]一个国家如果屡次发动战争,就会使得士民疲惫;即使能够屡战屡胜,也会诱使统治者骄傲自大,必将危及整个国家利益:“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313]《管子》认为战争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许多危害:“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314]所以战争尽管是必要手段,但却要防止穷兵黩武,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加以对待:“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315]基于这样的认识,《管子》在战争问题上追求“不战而胜”的境界,即便不得已而从事战争,也要争取一战而胜,避免旷日持久,损师疲民,“至善不战,其次一之”[316]。《管子》认为只有“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317],才是正确的做法。
《管子》这种对待战争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是其作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认真借鉴其他学派战争观有益因素的产物。当时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国家遭兼并的现实,使得齐国法家不得不面对天下大势,肯定战争的必要性。但是,魏惠王、齐湣王穷兵黩武招致丧师辱国的结果,又使得齐国法家认识到一味好战的危害性,因此主张慎战节兵。另外,齐国较开放的学术文化传统,也使得齐国法家善于吸取其他学派的长处。这在战争问题上就表现为借鉴齐国兵家中的“慎战”主张,如孙武和孙膑都是齐国人,均主张“慎战”。《孙子兵法》言“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并把这视为“安国全军之道”[318]。《孙膑兵法·见威王》言:“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319]这些都是齐兵家“慎战”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黄老学派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提倡适可而止。(www.zuozong.com)
《管子》战争观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是它对战争性质的区分。《管子》认为,战争的性质可以划分为“义”和“不义”两大类。所谓“义兵”,就是“案强助弱,禁暴止贪,存亡安危”,就是“至善之为兵也,非地是求也,罚人是君也。立义而加之以胜,至威而实之以德,守之而后修”[320]。所谓非义之兵,就是“贪于地”“不竞于德而竞于兵”[321]。《管子》认为,战争的正义性乃是决定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障:“行义胜之理。”[322]从事义战,方可“立于胜地”,又可“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323]。从这样的认识出发,《管子》主张“竞于德”,而“不竞于兵”[324]。强调用兵打仗要“举之必义”[325],即以正义战争对付非正义战争,从而实现“有义胜无义”[326]的目的。同时,《管子》对非正义战争也进行了有力的贬斥,明确指出军队强大、士兵勇敢而战争性质“不义”,则等同于“伤兵”“残兵”,“勇而不义伤兵”[327]。这种军队在战争中必然会遭到失败:“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328]虽然《管子》对战争性质“义”和“不义”的区分是相当肤浅的,仅仅局限于抽象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层面,但是这毕竟表明当时的思想家在战争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在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