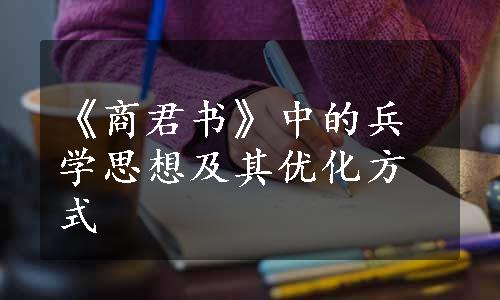
《商君书》,也称《商子》,战国时期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代表作之一。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商鞅是卫国人,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或公孙鞅。后受封商邑,号商君,故又称商鞅。早年曾师事尸佼,并为魏相公叔痤家臣,为公叔痤所赏识,但是始终不为魏惠王所用。公元前361年,商鞅听闻秦孝公试图恢复秦穆公霸业,求贤于天下,于是西行,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辅佐秦孝公在秦国执政近20年。在此期间曾顺应历史潮流,在秦孝公等人支持下,先后两次主持变法,在变法令中,展现了法家的基本立场:“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又载:“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157]可以看出,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是奖励军功,发展农桑,废除井田,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革除旧习,这些措施使得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为秦国日后的发展并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孝公死后,惠文王立,公子虔等人告发其“欲反”,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商鞅虽死,可其法未败,他的变法措施在秦国得到了保留。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成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也是秦国崛起的关键。
《商君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商鞅一派法家的政治立场、经济主张、哲学理念、兵学思想以及社会历史观点,也载有一些秦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及变法的史实。其书在战国末年就有传本,并流传很广,故有“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158]之说。《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商君》二十九篇”[159],现存24篇。其中第16篇、第21篇有目录而无内容。今本《商君书》中有不少商鞅的著作,如《垦令》《靳令》《外内》《开塞》《耕战》诸篇。但是也有许多篇可能出自其后学之手,这从文章内容和行文风格中可以看得出来,这方面的篇目有《徕民》《更法》《错法》《弱民》《定分》等。《商君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完整把握商鞅思想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地位。除《商君书》以外,《汉书·艺文志》兵家类还著录有《公孙鞅》27篇,入“兵权谋家”。据《汉书》载:“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160]据此可知,《公孙鞅》一书是商鞅学派的专门兵学理论著作,遗憾的是其书早已亡佚,使得我们今天在研究商鞅学派兵学思想时,只能以《商君书》作为最主要的依据。
《商君书》的兵学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积极主战的战争观、农战结合的战争指导思想、以重刑厚赏为主干的治军理论以及有关的具体作战指导思想等四个方面。
第一,“以战去战”的思想。
《商君书》认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武力征伐的时代,天下大乱,群雄兼并,一日无已,“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161]。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战争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162]因此,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并认为这才是“适于时”的做法。为此《商君书》积极主张战争,反对所谓“非兵”“羞战”之类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163]
为了论证其积极主战思想的合理性,《商君书》进而指出:“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164]意思是说,面对纷争之世,国家应积极进行战争,毒害就会输散到敌国那里。什么是“六虱”?《商君书》明确指出:“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165]《商君书》认为,这些人的存在有害于农战和国家,故称其为“六虱”。如果“六虱”在一个国家中毫无市场,贫弱的国家也必能走向强盛。相反,如果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那么国内就会产生苟且偷安的风气,“六虱”就有市场,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这最终会导致国力的削弱。因此,《商君书》肯定战争是建立强大国家的必要手段,是振奋民心、净化社会空气的有效措施。类似的观点在《去强》篇中也有明确的表述。这里,《商君书》将“非兵”“羞战”看作是和“仁义”“礼乐”一样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虱子”,予以坚决反对。这是和儒、墨“非战”、反战的思想根本对立的,也和兵家“慎战”的观点有所不同。由此可见,“以战去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166],乃是《商君书》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和坚定立场。
第二,农战结合,“多力者王”。
《商君书》对如何赢得战争的胜利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农战结合的战争指导思想。《商君书》认为,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建设,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作“多力者王”[167]。书中明确指出,国家的强盛与否是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并认为恩德也产生于实力,即所谓“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168]。
《商君书》进而指出,加强国家的实力关键在于政治措施是否得当。在《商君书》中,军事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明确表述:“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又曰:“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169]意思是说,政治上的胜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前提。
把战争与政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和分析,在先秦诸子中并不罕见,但在《商君书》中,将修明政治等同于厉行农战,则是它的特点。《商君书》所谓的“政胜”主要是指实行农战。它一再强调从事农战的重要性:“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170]又曰:“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亦曰:“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171]甚至认为,农战是富国强兵、实现霸王之业的关键:“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172]相反,如不进行农战,则一定会危及国家,丧失兼并战争的主动权:“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173]
《商君书》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两者互为关系不可分割,重战和重农必须紧密结合。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只有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这样既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驱使民众为保卫国土而竭力死战,正所谓:“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174]《商君书》把经济与军事联系起来,反复阐明农耕与兵战的关系及其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是较为辩证全面的认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具体的可操作性。(www.zuozong.com)
第三,重刑厚赏,以法治军。
《商君书》用大量的篇幅阐述其治军思想,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治军理论遗产。其基本特色是强调以法治军,而以法治军的核心内容则是提倡重刑厚赏。
《商君书》肯定严明法制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指出:“胜有三等:若兵未起则错(措)法,错法而俗成,(俗成)而用具。此三者必行于境内,而后兵可出也。”[175]又曰:“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76]这是与儒家以仁义治军的观点大相径庭的。《商君书》认为以法治军的有效手段是重刑厚赏,促使士兵勇敢杀敌,在战争中全力取胜。“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177],所以,唯有借助于重刑厚赏这一手段,使民众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178]又曰:“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179]如此方可保证“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180]。
《商君书》认为,要使重刑厚赏的思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制定具体的标准,辅之以必要的方法。这个标准和方法,就是指“壹赏、壹刑、壹教”[181]。所谓“壹赏”,就是“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182],即把奖赏统一到战功方面来。所谓“壹刑”,即统一刑罚,“刑无等级”,那么“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183]。所谓“壹教”,就是“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184],即把教育统一到农战上来。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使得“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185],形成民众“乐战”的社会风气:“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186]《商君书》指出,一旦做到了这三点,便可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无敌于天下了:“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187]
第四,《商君书》的作战指导思想。
《商君书》不是专门的兵学理论著作,因此,它对作战指导问题的论述相对显得比较单薄。但是仍有一些内容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首先,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商君书》曰:“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也。”[188]即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预知胜负。它还主张在作战中,应对敌情随时刺探,以采取适当的对策:“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189]
其次,用兵作战重“谨”。《商君书》主张“兵大律在谨”[190]。虽然其积极主战,而在具体作战指导上,它提倡谨慎从事,反对盲动,这也反映出其重战的态度,同时亦反映出在兼并战争下胜负对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如,在追击溃敌问题上,它要求适可而止,以免中敌埋伏:“见敌如溃,溃而不止,则免。故兵法:‘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小战胜,逐北无过五里。’”[191]
再次,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立本》篇论述了致胜的因素问题,指出取得作战的胜利,凭借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名声显赫是不可靠的,关键在于激发和利用士气:“恃其众者谓之葺,恃其备饰者谓之巧,恃誉目者谓之诈……故曰:强者必刚斗其意,斗则力尽,力尽则备,是故无敌于海内。”[192]
最后,探讨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战法。这在《商君书》中有精辟的论述。其中指出,守城防御作战,要用具有死守决心的军民,同进攻之敌决战到底,“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做到“无不尽死”。[193]守城还要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发动全体居民参加作战:“守城之道,盛力也。”又曰:“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194]根据男女老弱的不同情况,因材施用,适当分配各军的任务,团结协调,争取胜利。将这些同《墨子》书中有关守城作战论述的记载参看对照,可以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战国时期守城防御作战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其中亦可窥见墨家与秦国的密切关系。
《商君书》所包含的兵学思想,是比较丰富的。它反映了代表新兴阶层利益的法家在战争问题上积极进取的态度,它对农战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对以法治军、严刑厚赏问题的论述,在当时兵学思想领域中均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适应时代潮流的理论,并对后世兵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商君书》鼓吹战争,将战争抬高到不适宜的地位,将国家视为战争机器,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减弱乃至否定政治教化的作用,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它“胜强敌”“必先胜其民”[195]之类的观点,主张在国内采取高压政策以力压制民众,则突出体现了它与广大民众尖锐对立的立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