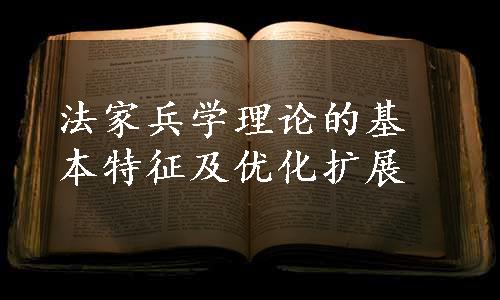
法家学说的基本特色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45]“信赏必罚,以辅礼制”[146]。法家所主张的理论和秩序是与礼乐文明相对的一种新的思想和秩序。法家学者力主变革,认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政治措施应该顺应变化了的情况:“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147]在战国时期由法家主持的具有代表性的改革分别是李悝在魏国主持的变法、吴起在楚国主持的变法和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等。其缺点也非常明显,主要包括轻视和否定教化,独任刑法,刻薄寡恩,往往会对旧贵族造成极大的冲击,主持变革者个人的结局往往不好。“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148]所以,一般而言,法家的改革成效往往能够收效于一时,但有其局限性。
法家内部的不同派别,由于师承关系的不同和地域环境的差异,还具有各自的个性。按地域考察,法家可以划分为三晋法家和齐地法家,商鞅、韩非是前者的代表,他们是法家的主流;管子则是后者的代表。在齐国特定的开放环境中,受学术兼容并取传统的影响,齐国法家在主张推行法治的同时,也主张容纳礼义教化,强调礼法并用,相辅相成,注重耕战的同时,仍不废工商,驱使民众的同时,又注意争取民心。这些都是与三晋法家有所区别的。按学派考察,前期法家可以区分为“法”“术”“势”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所谓“法”,就是成文法,“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49]。所谓“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150]。所谓“势”,就是势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力量,君主权势:“势者,胜众之资也。”[151]又曰:“主之所以尊者,权也。”[152]可见三派的侧重点各有不同,这种分歧一直到韩非子那里才得到综合。注意这些地域与派别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法家思想的内容与特点是非常有益的。
法家兵学思想是法家哲学、政治思想在兵学领域内的反映,亦是法家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而提出的系统军事理性认识。总括地说,法家兵学思想大抵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肯定战争是社会生活中的必然现象,拥护、支持并参与当时的兼并战争。法家认为,战争起源于人类的私欲,是人类争名夺利的自然结果。在战国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战争乃是消除割据,进行兼并,完成统一,再次实现和平的有效途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所以他们积极主张战争,提倡“战胜强立”,反对儒墨“非战”“羞兵”的观点。(www.zuozong.com)
第二,主张以耕战为本,富国强兵。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的环境中,哪个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哪个国家就能够在兼并战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并不断壮大发展。法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积极主张重视农业,发展经济,加强军力,奖励耕战。于是他们着重阐述了耕战的意义、方法、措施以及目的,如《商君书》明确指出:“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耕战……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王之道毕矣。”[153]因此,法家的著作也被称为“耕战书”。
第三,以法治军,严明赏罚。明赏罚、严法纪是战国大多数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主张,其中尤以法家对这一问题的强调最为显著突出。这也是法家政治观念反映于其兵学理论的必有之义。法家认为要使士兵勇敢作战,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通过重刑厚赏这一手段。所以主张严明军纪,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失人不北矣。”[154]在执行过程中,执法者一定要做到公正不阿,“不辟亲贵,法行所爱”[155]。这一点与兵家提倡“刑上极,赏下通”[156]的做法是相当接近的。为了激励民众踊跃参战,为兼并战争效命,法家倡导并推行军功爵制,如商鞅在秦国推行的二十等爵制,这既有力地推动了兼并战争的开展,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削弱了旧贵族的特权和势力。
当然,法家不同派别和人物,对兵学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也是有差异的,这既表现为认识深度的不一,也表现为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如,《商君书》主战态度最为积极,而《韩非子》《管子》则多少有所节制。又如,《管子》《商君书》对作战指导问题多有阐述,而《韩非子》在这方面则稍显逊色。同中有异,使得法家兵学思想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