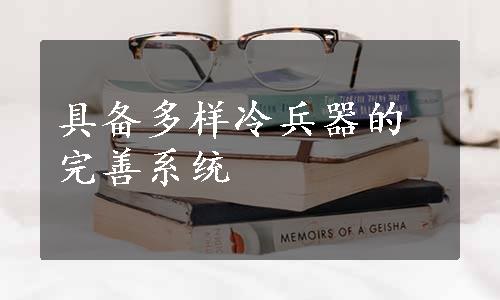
战国时期的冷兵器主要可以分为刺杀格斗兵器、抛射兵器、防御兵器、攻城守城器械等四种类型,我们以下分别简要予以论述。
(一)格斗兵器
格斗兵器种类主要有戈、矛、戟、殳、剑等。
戈是当时主要刺杀格斗兵器之一。春秋时期戈的形制较商、周时代又有所改进。戈援比前向上扬起,援部有脊,其上刃和下刃前伸后都作约135度的内折而聚成前锋,呈弧形而尖锐,即所谓“主锋”状,更利于啄击和勾割。战国时期戈的形制又有新的改进,戈体逐渐由宽变窄,更加灵活轻便;戈内上翘,并做出锐利的边刃,使这一部分也具有了击敌的功能。戈的长度不一,从80厘米到3米左右皆有。一般而言,步战所用之戈长度较短,车战所用之戈长度较长。
春秋时期的矛,其矛头多为青铜材质,但形制开始从凸脊扁体双叶形趋向三叶窄长棱锥形,前锋更加锐利,刺透力增强。战国时期青铜矛的形制更趋成熟,其特点是窄体、直刃、筒身、骹部有钉孔或双纽。战国后期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矛型,矛身中脊线上凸起两个刃,形成较深的血槽,具有更强的杀伤力。同时,钢铁矛头在当时也开始出现。矛的长度一般近3米,分别装备于车兵和步兵。
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常用兵器之一。根据《左传》等史籍的记载,有大量当时作战用戟的事件。它既被应用于车战,也被用于步战和骑战。当时青铜戟的戟刺(矛头)与戟援(戈头)分别铸制,然后再联装在木(竹)杆上。春秋晚期,在南方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在一根3米长左右的柄上联装两个或三个戈头的戟,有的不装戟刺,称为“多果(戈)戟”,勾割效果较好,是重要的车战兵器。由于戟具有勾刺兼备的优点,较戈和矛的杀伤效能为佳,因此大受欢迎,在战国时期已有取代铜戈的趋势。战国晚期,将块炼铁加热渗碳、折叠锻打的新工艺开始被采用,使通体呈“卜”字形的钢铁戟开始走上战争舞台,但数量极其有限,目前发现的实物多集中于当时燕、楚诸国的境内。
在春秋中期以前,中原地区只有青铜短剑,多用于近战护体,尚不是重要的格斗兵器。春秋后期起,情况有显著变化,青铜剑的剑身加长,从短剑发展为长剑,而且形制趋于统一化和规范化。尤其是地处东南丘陵水网地区的吴、越、楚诸国,为满足步兵战斗兵器轻便锋利的要求,剑的制作技术有更大的飞跃,出现了技艺精湛的铸剑大师(欧冶子、风胡子、干将、莫邪),冶铸出“利如霜雪,光如云霞,陆斩犀兕,水断蛟龙”[13]名传千古的宝剑。已出土的“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姑发间反剑”“越王勾践剑”,就集中代表了当时铸剑的工艺水平。战国时期,中原各国的铸剑术也有空前发展,钢铁剑开始出现,其制造工艺主要采用块炼铁固态渗碳制成低碳钢件,然后多层叠打而成,刃部一般经过淬火处理,异常锋利。剑的长度一般可达1米,个别的已达1.4米。
当时的格斗兵器还有殳、铍、钺、斧、匕首等。其中铍(锬、铦)由青铜铍头、长柄构成,铍头尖锋直刃、扁茎,刺透力很强,它出现于春秋时期,大量使用于战国时期。斧钺,在战国时期的实战中地位已大大降低,一般作为仪仗之用,象征军权。
(二)抛射兵器
抛射兵器的主要种类有弓箭和强弩,它们的使用,大大延伸了战场格斗的空间距离,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考工记》所载内容和出土的实物来看,当时弓的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弓的质量大为提高。制弓的主要材料有六种,称之为“六材”,即“干、角、筋、胶、丝、漆”,各有其用:“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14]其中,选材、配料、制作程序和规格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在竹、木材(干)的内侧粘贴动物角片,以增加弓体的坚韧和弹力,再粘缚筋、胶,然后用丝线缠紧,通体髹漆,挂弦的弭用动物角制作,弓弦采用丝或动物筋。这种弓已经是很成熟的复合弓,弹力大,经久耐用,文献中通常称为“角弓”。各诸侯国都用它装备部队,大量使用于战争之中。
弩是由弓发展而来的射远兵器,它通常由弓、木质弩臂和青铜弩机三部分组成,弓横装于臂的前端,弩机安装在臂的中部偏后尾处,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并供使用者托持。弩机用以扣弦、发射。使用时将弦张开,挂在弩机上,将箭镞装在弩臂的箭槽中,扳动弩机,使张开的弦脱钩,利用张开的弓所储存的能量,急速收弦化为动能,将箭镞弹射出去。由于弩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为两个动作,使得射手有瞄准目标和寻觅放箭时机的时间,因此既提高了命中率,又增加了弓的储能量,提高了箭镞的射程和穿透力。弩从春秋中后期起开始较广泛应用于战争之中,战国时期,弩的使用更为普遍,其种类主要有臂张上弦的臂张弩和足踏上弦的蹶张弩,在当时,强弩成为装备列国军队的利器。
弩特别有利于步兵野战布阵、设伏和守城防御作战,它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弩的构造要比弓远为复杂,是弓向机械操作迈出的重要一步,弩的发明称得上是抛射兵器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随着以弓弩为主体的远射兵器制作工艺水平提高,积弩齐发成为战场制胜的重要手段。现代考古发掘中已经发现了很多战国时期的弩机或者弩机上的铜部件。如,在湖南长沙扫把塘楚墓中出现了一件保存相当完整的战国弩。[15]甚至此时已经出现了能够连发的弩。1986年,在湖北江陵秦家嘴一座战国墓中就发现一件保存完好的弩,并与弩箭一起放在一个竹筒中。据学者研究,将其定名为“双矢并射连发弩”,“弩臂中插有一根可前后活动的木杆,前端伸出在弩臂之前。射手把这木杆抽插一次,可以同时射出两支箭并使弩回复待发射状态”[16],其活动木杆内部有铜质机件,比后世“诸葛弩”结构还要复杂。2015年,在秦兵马俑一号坑的第三次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一把保存完整的弩机上发现了用于平时养护弓弩的两根名为“檠”的配件,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秦兵马俑发掘以来所发现的最完整的一个弓弩,尤其是保护弓弩韧性的‘檠’的发现更为重要。作为弓弩的辅助构件之一,‘檠’在使用弓弩时需要拿掉,但其在弓弩闲置时,却是弓弩保持完整形象和材料韧性的重要方式。”[17]同时,据考古人员的推测,秦兵马俑发现主要有两种弓弩,其中小型弓弩的射程在150米左右,大型弓弩的最远射程可达800米,由此可见此一时期弓弩技术的发达。(www.zuozong.com)
箭(矢、镞)的制作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进步,制作上也更趋于科学化和规范化。如,箭镞、箭杆、羽毛间的比例,箭杆的长度与直径,箭杆的前后部的重量、比例,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规定。箭镞虽多青铜质,但形制有了较大变化,即由传统的双翼扁体形而改为三翼三棱锥体形,镞锋小而锐利,大大提高穿透力和杀伤力。战国时期还使用了铁镞,其中以三棱形居多,基本上承袭了铜镞的形制。箭杆多为竹制,也有木制,尾装羽毛,起平衡作用。弓用的箭较长,为70厘米左右;弩用之箭较短,在50厘米上下。
(三)防御兵器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激烈,因此防护装具的制作和使用也均有一定的进步。这反映了随着刺杀格斗兵器和抛射兵器的发展,以防御为目的的军事装备也必然会有所改进,这主要包括盾、甲、胄等。
当时的盾仍然以木和皮革为制作材料,其形状较西周时期稍有变化,其上部大多做成对称的双弧形,下部一般为长方形,表面髹漆,并大多绘有精美的图案。盾高一般有60多厘米,宽约45厘米。除此之外,长方形和梯形的盾牌也同时使用。当时,盾作为军中主要护体器具,用于车、步、骑、水等各种作战环境,以蔽刺兵和矢石。在防御战中,城头上遍设盾橹,以防御敌人自城下射上来的飞石与箭镞。
当时的甲一般由皮革制成,分人甲和马甲两种。甲片为长方形,用绳组、丝组或细皮条连缀在一起,表面髹漆。就人甲而言,由身甲、甲裙、甲袖三部分组成。另外,还有一种数量很少的木胎皮甲,以木为胎,外贴皮革,表面髹漆。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少量的铁铠甲,河北易县燕下都墓葬中就发现了铁甲片,这说明战国后期已有了铁制的防护装备。马甲用于保护拉战车的马匹。《左传》所谓“介马而驰”[18],即指将战车驾马披甲,然后发起冲锋。当时的马甲一般也是以皮革制作,工艺与人甲制作基本相同。
胄用以防护人或马的头部。春秋时期的胄多以皮革制作,其工艺与甲的制作基本相似,即由甲片编缀。胄一般中有脊梁,下有垂缘护颈。战国时除皮胄外,还出现了铁胄(铁兜鍪)。
(四)攻城守城器械
春秋战国攻守城器械多见于文献资料记载,其种类主要有云梯、轒辒、巢车、铁蒺藜、地听等,但目前尚无考古实物发现。
云梯是用于登城的工具。据《墨子》载,鲁国巧匠公输般曾为楚王造云梯攻打宋国。[19]战国时期的云梯据战国铜鉴水陆攻战纹饰所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斜靠在墙头,供士卒攀缘之用,至于是独竿式还是双竿式,则不可分辨。另一种是底部装有轮子,可移动,梯身仰俯角度可变化,用人力抬举,云梯前端有钩状物,可钩住城垣,利于士卒攀登和防止城上守敌推拒。
巢车又称楼车,是一种设有观察点,可登而望远的特种车辆。春秋时期,巢车已在战争中广泛使用。据《左传》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子(共王)登巢车,以望晋军”[20]。
据文献记载,铁蒺藜在战国时期已普遍用于城邑守备和要道布防,但实物目前考古尚未发现。后世所用蒺藜一般由四根铁刺组成,凡着地均有一刺朝上,状如草木植物蒺藜。其作用是撒布于敌人经过的交通要地,以迟滞敌军前进;再则布设于城池、军营四周,以防敌军突袭,增强防御能力。
地听又称瓮听,用于侦测有声源目标方位的器材,战国时已用于城防战中。当守城者发现敌人开掘地道时,立即在城内八方墙下凿出竖井,置一口新缸,上蒙薄牛皮,令听力好的人趴伏其上仔细辨听,以察知敌人挖掘的方位,从而采取迎敌对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