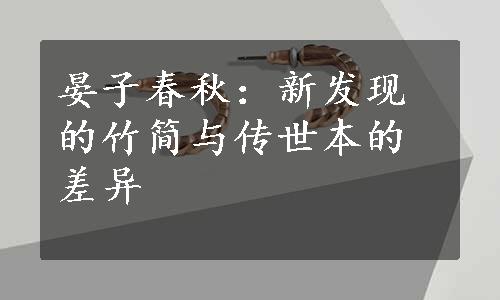
晏子,字仲,谥平,齐国“莱之夷维(今属山东高密)人”[134],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史籍多以晏平仲、晏子称之。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其父晏弱病逝,在世卿世禄制的选官制度下,晏婴继任上大夫,步入齐国的政坛。晏子曾先后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齐国君主,主政齐国长达半个世纪,盛名显扬天下。我们今天了解晏子的事迹主要依据《史记·管晏列传》和《晏子春秋》这两部典籍。晏婴给后人留下的重要印象,一个是他的身高,大约一米四的样子;一个是他的出众辩才,不辱使命,雄辩四方。晏婴主政齐国期间,在外交上多次维护齐国尊严。晏子为人所熟知和称道的外交活动有两件大事:一是他在樽俎之间成功地打消了晋平公出兵齐国的想法,孔子赞扬其“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135];二是晏子出使楚国,在具体外交礼仪中成功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晏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中后期,此时中原霸权已经为晋国所掌控,此时的齐国所采取的已经远非齐桓公称霸时期的国家战略,因此在晏子思想中更多体现的是内政治理思想。从思想倾向上来说,其与儒家思想非常接近,如,晏子主张爱民、节俭、重礼、尊贤等思想。晏子这一思想倾向在《汉志》《隋志》中亦可见一斑,如,《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儒家者流”中首列“《晏子》八篇”,《隋书·经籍志》亦因之,将“《晏子春秋》七卷”列入儒家。但是,在长期的儒学发展与研究中,《晏子》始终未产生重要的影响。清代《四库全书》又将“《晏子春秋》八卷”列入“史部传记类”。
《晏子春秋》以记言为主,主要为晏子与齐景公的对话,亦有齐灵公、齐庄公等君主与叔向、孔子等贤者的对话。全书包括内、外2篇3卷215章,其中《内篇》相对比较整齐,《外篇》显得比较杂乱。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的学派[136]、思想等相关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深入讨论。我们认为这可能与流传至今的《晏子春秋》一书长期被定为伪书,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有关。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发现《晏子》书16章,其内容均见于今本《晏子春秋》18章中,而且其中较为完整的9章与传世本相差不大。[137]同时,学者普遍认为,《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中第一篇《景公疟》亦当与《晏子春秋》相关。可见《晏子春秋》一书并非伪书,而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古籍,我们也基本认同其成书时代当在战国时期,正如裘锡圭根据银雀山汉简本所推断的基本结论:“字体看,其时代略早于墓葬,当属西汉前期。我们知道,从一部书的开始出现到广泛传抄,通常总要经历一段不太短的时间。西汉前期既然已经在传抄《晏子》,可以想见这部书的出现大概不会晚于战国,把它定为秦或汉初作品,仍嫌太晚。”[138]姑且不论其成书年代,我们基本上仍认为《晏子春秋》是“搜集晏婴的佚著、言辞、事迹及传说故事编成”[139],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够反映晏子的基本思想。(www.zuozong.com)
《晏子春秋》作者的争议也很大。在《隋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书中,均认为《晏子春秋》的作者为晏婴。柳宗元在《辩晏子春秋》率先质疑:“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140]北宋时期的《崇文总目》亦承袭柳宗元的基本观点:“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141]孙星衍在《晏子春秋序》认为:“《晏子》文最古质。”[142]并明确指出该书系晏婴宾客所作,“婴死,其宾客哀之,集其行事成书。虽无年月,尚仍旧名……书成在战国之世,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143]。而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说法主要有齐人说或稷下学者说,[144]亦有学者指不一定与稷下学者有关。[145]当然,我们基本认为《晏子春秋》当为齐国某位学者或学者群体整理的一部反映晏子思想的著作,但是对其作者具体化的处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显然风险很大,亦并非完全科学的态度。
《晏子春秋》以语录对话体的形式来反映晏子的思想,当与《论语》反映孔子基本思想的情况相类似。虽然即使到现在,学术界对《论语》的编纂者和时代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并不影响其作为研究孔子思想最基本、最可靠的典籍。所以,我们认为对《晏子春秋》与晏子思想关系的认识亦当如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