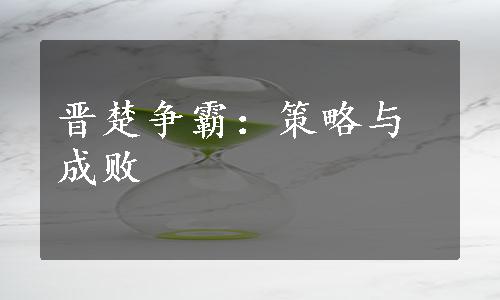
大国争霸是春秋历史的主旋律。一部春秋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大国争霸战争史。当时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的名号,控制其他中小国家,曾持续不断地从事征伐活动,先后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战争。
在大国争霸战争中,晋楚两国曾扮演了主要角色。春秋争霸战争,其实就是晋楚两国争夺中原霸主的冲突与斗争。在双方争霸过程中,有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战役,它们分别是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其中,晋国取得了城濮之战、鄢陵之战的胜利,而楚国则打赢了邲之战。三场战争的胜利归属,都反映出很高的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春秋争霸战争以及兵学学术发展的典型,亦是一个缩影。
(一)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其对当时中原局势的演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使屈服于楚国的鲁、曹、卫、陈、蔡、郑诸国得以脱离楚国,重新回到中原集团,结束了齐桓公死后十余年间中原“诸侯无伯”的混乱状态,确立了以晋文公为霸主的相对和平稳定局面,同时也决定了楚国最终不能独霸中原的命运。自此之后,在晋国的领导下,中原诸侯与楚国抗衡长达100年左右,春秋历史进入了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中原、互有攻守、相持不下的阶段。从这一点上说,城濮之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次重大战役的本身。
在城濮之战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相对的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出色的“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合理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161],雄踞中原。由此可见,双方在这场决战中的胜败,不仅仅在于军队的数量,而在于战争主观指导的正确和错误。
楚国在泓水之战获胜后,威震中原,俨然如同霸主。所以楚国应该乘势展开政治攻势,采取善邻政策,以调解中原诸侯之间矛盾为己任,争取各诸侯国向心于楚;应以军事威胁作为辅助手段,不宜轻易出兵攻伐。若此,则以楚国当时的军力与国势是有可能独霸中原的。但楚国不善于运用政治策略,无法做到政治与军事两种手段的巧妙结合,只一味仰仗军事力量和战争征服手段,企图单纯以武力压服他国,这就往往会导致在政治上陷自己于孤立的境地。
城濮之战的起因是齐鲁冲突。当时,楚国既然已经答应鲁国的请求,决定出兵伐齐救鲁,就应该以齐国为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力量对付齐国,然后西向击破晋、秦,采取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策略,而不应半途改变主要攻击方向,去对付宋国。因为在宋国背弃楚国倒向晋国的情势下,攻打宋国势必会引起晋国的干预,楚国会提前与强大的晋国交锋,难免陷于被动。但楚国君臣不能审时度势,贸然分兵伐宋、伐齐,这样就犯了两线作战的错误。此外,楚军在泓水之战胜利后骄傲自满,不重视争取与国和利用同盟军,既得不到鲁国等同盟军的配合策应,又轻率拒绝齐、秦主导的调停,为丛驱雀,陷于外交上的孤立,在战略指导上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
当晋国出师救宋之势已成,楚国本当适时调整,及早放弃围宋作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对付晋军,如在晋军渡河侵卫时,楚军若以优势兵力救卫,也许能挫败晋军的锋芒;或者在晋师攻曹时,若以大军逼迫晋军于曹国都城之下决战,亦有可能战胜晋国,因为当时齐、秦两国尚未打破中立,晋军远道征战,势单力孤,楚国若能和鲁国对晋军实施夹击,则晋军处境将会十分不利。无奈楚国留恋围宋的方略,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坐失时机,终陷被动。
在晋军已经攻占曹、卫,并取得齐、秦出兵相助之际,楚军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楚成王决心退兵是正确的,但楚军前敌统帅子玉却囿于个人名利地位,不顾大局,不听训令,刚愎自用,骄躁轻敌,遂加速了战局的恶化。而楚成王虽已决心退却,却又抱侥幸取胜心理,因此未能坚决制止子玉的错误决策,也不愿意增派更多的军队。这种内部的分歧以及由此引起的指挥混乱,注定了一支军队即将陷于失败的命运。
楚军的作战指导也笨拙呆板,缺乏机动灵活性。楚军为对手晋文公决战前夕“退三舍辟之”[162]的策略所迷惑,大举追击,既劳师疲众,又失道亏理,实为被动的做法。在战场上,楚军主将也只是固守一般战法,列阵对战,对战局上出现的异常情况不能及时判明真相,识破对方企图,灵活采取对策,而为对方的诡道战术所诱骗、迷惑,不断陷入混乱、被动。当楚军左、右军遭到攻击,情况危急之时,主力中军却迟迟按兵不动,未作及时策应,致使左、右军被晋军逐一歼灭。
总之,楚军方面君臣不睦,指挥不一,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战,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再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白白地将楚国争霸中原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
晋军胜利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胜于政治,即在政治清明的前提下,善于运用政治谋略。晋文公在秦国的协助下,回国即位后,稳定内部,改良吏治,选拔和任用了一批智能之士,又采取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抓住周襄王处于危难中的良机,出兵勤王,一下子把“尊王”的旗号掌握到手中,拥有了团结中原诸侯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同时,晋文公把握机遇,应宋国的请求出兵抗楚救宋,从而再次举起了“攘夷”这面大旗。这样,晋文公便造就了自己继承齐桓公霸业的政治态势,树立了“尊王攘夷”的霸主形象。晋文公此举对争取中原诸侯向晋国靠拢是关键的步骤。其次,晋国的取胜,也有其浓厚的经济和军事原因。晋国在统一后几十年中,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军队逐渐得到了扩充,尤其是在实行“作爰田”“作州兵”两项改革后,国力发展迅速。晋文公又在数年之内“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163],教民“知义”“知信”“知礼”,成为“可用”之民,从而能够在城濮之战前夕“作三军”,顺利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再次,晋国自西周初年分封建国后,一直和戎狄相邻,晋国军队习惯了戎狄的生活方式,而且在长期与戎狄部族的作战过程中,提升了晋军的作战能力,培养了士兵强悍善战的军事作风,使晋军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晋军内部和睦团结,指挥统一而又机动灵活,纪律严明,作战英勇,临战又能谨慎对敌,不骄不躁,这些条件都是楚军所不具备的。晋文公出兵抗楚救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的基础之上。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远在外线作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善察战机,虚心采纳先轸、狐偃等人的合理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即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采取先胜弱敌,调动楚军北上,解救宋围的作战方针,从而取得了以后作战前进的基地。随后,晋文公又根据楚军没有北上,解围目的未曾达到的这一新情况,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及时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个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并激怒敌人,诱使其失去理智而蛮干,从而使晋军夺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为赢得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城濮决战之时,晋军敢于贯彻诱敌深入、后发制人、伺机聚歼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赢得齐、秦、宋各国军队在战略上的遥相呼应,给敌人造成精神上的压力和战略上的威慑,并集中兵力,鼓励士气。一切就绪后,晋文公又能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利用敌人内部不团结的错误和兵力部署上的过失,乘隙蹈虚,灵活机智地选择主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先攻打楚军军阵的薄弱环节,并迅速加以击溃,带动全局,扩大战果,从而获得了这场关系到晋、楚命运及中原形势走向的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www.zuozong.com)
(二)邲之战
邲之战是春秋中期的一次著名会战,是当时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晋国和楚国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在作战中,楚军充分利用晋军内部分歧、指挥无力等弱点,适时出击,一举战胜对手,从而一洗城濮之战失败的耻辱,在中原争霸斗争中暂时占据上风。至于楚庄王本人,也正是由于此役的胜利,而无可争辩地挤入了为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春秋五霸”[164]之列。
邲之战的胜负与城濮之战不同,胜负易主。两场大战有某种类似之处,但胜负的原因,不在于双方军力强弱,而在于双方战争指导者主观指挥上的正确或谬误。我们认为晋军在邲之战中遭受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援郑之师出动过迟,尚未渡河而郑都已破,这时楚军已从围郑之战中解脱出来,得以腾出手来集中兵力,主动对晋军作战。正所谓主客地位不同,晋军一开始便处于被动。其二,晋军内部将帅不和,意见分歧。晋军主帅荀林父缺乏威信且遇事犹豫不决,不能集中统一指挥,为部属所强迫,被动应战。其三,晋方轻信楚军的求和请求,在和谈尚未取得成功之时就放松戒备,丧失警惕,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其四,当个别部将擅自挑战而引起战斗全面爆发后,晋军统帅惊慌失措,轻率下令军队渡河退却,自陷危险。其五,晋军在敌人威胁下贸然渡河,既未能组织战斗击退敌人,又未能妥善实施防御掩护退却,导致全军一片混乱,损失严重,由此而丧失作战的主动权,陷于失败。
楚军的胜利,则在于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的高明。楚军在围郑之前,即已在蔡地建立了战略前进基地,有了在中原持久作战的准备。故围郑之战持续数月后,仍能保持军队较旺盛的战斗力。楚军在晋军渡河前即已完成军队集结和战备动员,形成了以有备临无备的优势。楚庄王亲自统率楚军,指挥集中,军令统一,不像晋军那样各自为政。楚庄王正是善于利用晋军内部战和不定、意见分歧的弱点,在战前一再遣使侦察晋军的虚实,佯装求和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并松懈了晋军的防卫。在作战中,楚军又抓住晋军擅自挑战者的轻妄行动,由小战变为大战,迅速展开奇袭突击的攻势,一举击败了晋军。至于有论者以为楚军没有实施猛烈的追击,以致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这其实是不谙春秋前中期作战遵循“逐奔不远,纵缓不及”[165]军礼原则而产生的历史认识的错位。在当时军礼原则的规范下,楚军的选择只能是“不穷不能”[166],而我们无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以后世的兵学原则要求楚军去聚歼晋军。
邲之战的影响和意义均远不及城濮之战。是役,楚虽胜晋,但由于受到历史时代所限,并未予晋军以毁灭性的打击;晋军虽败,但并未真正大伤元气。这也就为尔后的晋国继续与楚国争霸中原保存了相当的实力。
(三)鄢陵之战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场战争,也是最后一次两国军队的主力会战。此后虽仍有湛阪之战(晋楚争霸最后一战)等战事,但其规模与影响均不能与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等三次会战相比。因此,鄢陵之战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楚国对中原霸权的争夺从此走向颓势;晋国方面虽然试图借此得以重振霸业(即所谓的晋悼公复霸),但事实上其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已经远不及前,且逐渐减弱了。
在鄢陵之战中,晋国谋定而动,先计后战,善察战机,巧妙指挥,击败同自己争霸中原的老对手——楚国,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优势地位,使其军事势力发展到鼎盛。这场战争后,晋楚两国都因各自的内外条件变化,而逐渐失去以武力争霸中原的强大势头,中原战场开始相对沉寂下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鄢陵之战也可以称作是当时晋楚争霸的最后一幕。[167]我们认为楚军遭到这场会战失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楚国在战略上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地位。当时除郑国之外,中原较重要的诸侯国如齐、鲁、宋、卫诸国均已集结在晋国的旗帜之下,战前形势明显对楚国不利。而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楚国又缺乏对晋国根本战略意图的了解,为晋国虚假的和好姿态所迷惑。楚国先与晋国举行西门之盟,后又自我毁坏秦楚联盟。这些举动使得晋国从容战胜秦国,并进而专力对付楚国。同时,晋国在吴国经营多年,吴国已经是晋国重要的支持者,此时吴国在侧后进行掣肘,楚国实际上已处于多面受敌的状态。在这种恶劣的战略环境下与晋国决战,其胜算本来就微乎其微。
第二,在具体军事决策方面,楚军也有严重失误之处。楚国出兵后,仓猝兴师,行军太急,“其行速,过险而不整”[168],结果造成军队疲劳,队列不整,士气难振,斗志削弱,楚军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要赶在齐、鲁、宋等国军队到达前与晋军会战,过于急躁,使晋国得以在预先待定的战场上,以逸待劳,而楚国自己却是以劳对逸,并且失去选择战场的主动权,一开始便处于会战的不利地位。
第三,楚军的战场指挥亦存在着重大失误,加速了其会战的失败。楚共王虽然能够注意“相敌”,观察到晋军具体活动情况,却未能判明晋军的真实作战意图,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在会战中,楚军除中军一度主动出击(但很快后退)外,其他军队基本上是消极防御。当晋军实施灵活打击时,楚军又缺乏权宜机变的能力,以致被动挨打,任人宰割。对于楚军中善战之士,如善射之士养由基[169]等,楚共王不仅不能善加使用,甚至还打击他们的积极性,限制他们的作战行动,致使楚军中精兵良将的作用根本得不到发挥。楚军主帅子反对局势判断失误,骄傲自大,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丧失再战的信心。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楚军遭到重大失败的结果。
相对而言,晋军的胜利亦绝非偶然。在战略上,晋国坚定不移地把同楚国决战、赢得中原霸权作为其长期奋斗的战略目标。国内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这个核心而进行。为此晋国联齐联吴,拆散秦楚联盟,使楚国陷于不利的战略地位。在这些基础上再寻求同楚国进行战场上的决战,从而始终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同时,晋军在此战中还表现出较高的作战指导能力。首先,晋国出动军队比较及时,先敌进入预定战场,“先处战地而待敌”[170],以逸待劳,以整击乱,赢得一定的主动。其次,会战之前,能够认真“相敌”,料敌察机,制订出较适宜的作战方案。再次,在会战过程中,晋军既能根据楚军的阵势和地形特点,灵活机动实施指挥,又能当机立断,先发制人。最后,晋军能在作战中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部署,加强两翼的兵力,对敌实行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针,从而一举击败楚、郑联军,达到称霸中原的战略目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