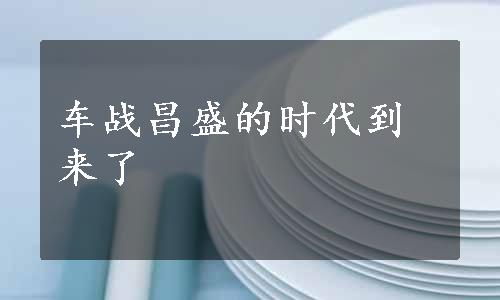
西周时期的兵种仍以车兵和步兵为主。随着战争的发展,车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车兵成为决定战场胜负、左右战局走向的核心力量。如在牧野之战时武王就出动“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59]。自周厉王改革后,由于“军”的编制开始出现,与之相适应,至周宣王时,已有“其车三千”[60]的规模,可见车兵的力量至西周晚期发展迅速。
夏商时期用于军事的马车可能已经出现,但是使用并不普遍,有可能在战争中仅仅充当运输的功能,并未出现在战阵中。根据考古发现,商代后期战车的装备还比较简陋,战车的组合兵器尚不发达,还难以达到组建克敌制胜的主力兵种的发展水平,战车兵种尚未取代步兵的核心地位。
而到了西周,车兵是西周时期的主力兵种之一,战车会战是当时最主要的作战方式,而西周至春秋前期则是车战的鼎盛阶段。当时的战车主要有两类:一类用于驰逐攻击,是为“攻车”;一类用于设屏障,塞路口,运辎重,是为“守车”。《周礼》将这两类战车分别命名为“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61]其中前三种属于“攻车”,后两种属于“守车”。“戎路”,又称“旄车”,通常是军队的指挥车,由国君、主将和部分禁卫军乘坐。“轻车”是“攻车”的主体,又称长毂、輶车、武车、战车等,在进攻中发挥核心作用。“阙车”,其结构和性能与轻车同,但因其担负的作战任务特殊而单独命名,主要用于填补方阵中因战车损缺而出现的空缺。“阙车”同时也担任警戒、掩护任务,可见其为机动的轻车,故《左传》又称其为“游阙”。“苹车”和“广车”属于防御用车。《孙子兵法》对战车则按其战术性质的不同而区分为两大类:一是驰车,即“轻车”“攻车”;一是“苹车”,即“守车”“重车”。这些名目繁多的战车,在当时都曾大展神威,在战场上扮演着类似现代主战坦克的角色,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杨泓曾指出配备在战车旁边的“这些徒兵装备简陋,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去为奴隶主卖命,所以当时决定战斗胜负的,主要是靠奴隶主阶级之间的车战。当一方的战车兵被击溃以后,真正的战争就结束了”[62]。
一辆“攻车”一般载乘甲士三人,偶尔也有载乘四人的,称为“驷乘”。甲士三人按左、中、右次序排列,并有不同的作战职能和任务。其中,左方甲士持弓主射,为一车之首,称“车左”或“甲首”。右方甲士称“车右”“戎右”“参乘”,手执戈、矛、戟等长兵器和盾牌,主格斗,同时兼管维修车辆并负责为战车排除障碍。在车轼前居中的是不直接参与作战的“御”,其职责是手握缰绳,驭马驾车,一般只佩带刀剑等随身短兵器。这样的战车通常采用一线横列作战,以便发挥远射兵器的威力。然后敌我互相驰冲,其近体格斗一般在两车相错时进行,近体格斗使用的兵器多为戈、矛、戟等。
指挥车“戎路”的乘员也为三人,但次序排列与职责分工则与一般轻车有别,即:主将居中,击鼓指挥;参乘仍居右,负责警卫与格斗;御者居左,驾驭车马。
守车大多也以马匹挽拉,当然也有用牛驾挽的。守车除了承担运输作战物资外,还被用作大军宿营时的临时防御设施,或撤退时连在一起形成阻止敌人追击的障碍物,为撤退时赢得必要的时间,可见守车(辎重车)也是军队车辆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63](www.zuozong.com)
西周是我国历史上车战全面兴起的时代,亦是车战的鼎盛时期。当时车兵已完全代替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与核心力量,战车数量激增,车战成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为了便于作战和管理,战车与步兵一般实行合同编组,以战车和甲士为主体,每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组成军队最基本的战术单位“乘”。“乘”主要包括战车甲士、车属徒兵、辎重车和后勤徒役,它也是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计算军事实力的基本单位。
关于车兵的编制,西周初期沿袭殷制,5乘组成一队,25乘为一正偏,100乘为一师,而每乘配甲士10名,故300乘,有甲士3000名,与《孟子》所记相合。当时的步兵则独立编组,在车战中协同作战。到西周晚期,车兵的编制在西周初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变化,每乘除甲士10人之外,另配有徒兵20人,即变成了每乘30人。每乘实行30人制,即战车1辆,官兵30人,挽马4匹,辎重车1辆。30名官兵中有甲士10人,其中车上3人(车左、御、参乘各1人),车下7人。甲士一般由“士”以上的贵族充当。战斗步兵15人,由普通国人担任;后勤厮役5人,由贵族的家内奴隶充任。此后,长期以来,这种“乘”的编制便成为车战时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64]就军的编组而言,据清代学者孔广森考证:“古者车战,故赋舆之法,以乘为主,而《周礼》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不言其车数,以《诗》考之,军盖五百乘,乘盖二十五人。天子六军,而《采芑》曰‘其车三千’……五百乘为军,是其明证。”[65]其所谓“盖乘二十五人”是“士十人,徒二十人”中除去“厩养五人”,与每乘30人并不矛盾。由此可见,到西周晚期实行的是以车兵为主的车步兵混合编组,即以战车为主体,每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组成军队最基本的建制单位,然后以五伍、四两、五卒、五旅、五师逐级编组成军。
当时,比较典型的车战的早期形态在牧野之战中有着生动的反映。如果把作战的全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其实施程序是首先展开步兵会战,然后以战车驰冲结束战斗。牧野之战中,双方的军队在商都朝歌的郊外牧野遭遇。纣王的军队,《史记》记载“发兵七十万”[66],我们认为显然失之于夸大,当然典籍中亦有17万的说法,但仍可以看出殷军是聚集了大量步兵参战。周军的战车部队为“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67],其基本编制与考古资料相符,而甲士的数目偏多;走在前阵的步兵,则是勇锐的巴师。[68]双方军队的部署,当是两线配置。第一线的步兵按左、中、右列成三个大排面的密集方阵,左、右阵为三列,中阵为五列。第二线的战车可能是以25辆为单位横向编组,排成左、中、右三个平列横队。[69]
会战以军前誓师发布作战命令开始,尔后,周军派出军将前往殷军阵前挑战(致师),然后第一线步兵(巴师等)以整齐的大方阵队形,唱着军歌缓慢地推进,“歌舞以凌”[70],“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71]。接敌后,周军仍以严正方阵队形进行刺杀格斗,“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72]。在如此沉重有力的攻击下,殷军第一线步兵终于被击败。于是武王亲率周军第二线的战车急驰攻击。面对连番冲击,商纣临时组织的军队,不论是士兵单兵军事素养还是军队整体协同作战的能力,都远远逊于周军,殷军阵形迅速被突破、被冲散,全线崩溃,甚至出现前线倒戈投降,典籍有多处记载:“鼓之而纣卒易乡”[73],“殷人倒戈”[74],“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75]。
牧野之战战况显示,典型早期车战中的军队为了保持方阵整体的阵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攻击能力,步兵和战车都必须以严整的队形来缓慢推进,因此军队的接敌和攻击行动均在统一号令的严格规范之下。正是这一特点使得车战战术相当程式化,一般要待双方列好阵形后,才以击鼓为号,发起攻击,即所谓“成列而鼓”[76],推崇“不鼓不成列”[77]。尽管这种战术表面上看似呆板,但是在广阔的平原战场上,战车横队的攻击力量较之战术同样呆板的步兵阵形仍然要大得多。到了西周后期,人们对战车的形制进行了改进,正如《司马法》所载,周人已着意于提高战车的综合战术性能,“周曰元戎,先良也”[78]。在战车形制设计上,周人开始缩短轨距和辕长,加大车舆面积,增加车轮的辐条数,关键部位增加青铜紧固件,从而提高了战车的机动性和坚固性,增大了战车的车速和载重能力。在此基础上,周人开始以战车为中心组建部队,从此车战全面兴盛,并取代步战而成为最主要的作战方式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