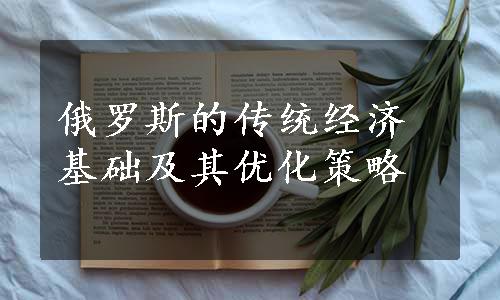
俄罗斯文化植根于其中的传统经济基础主要有经济生产方式、生产组织、经济制度等。
(一)农耕经济是俄罗斯传统经济的主体
众所周知,20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是农业国,以农为主。他们吃的主要是农产品,因而谷物、面包、稀饭、食物、面粉等与农业相关的词汇,很早就出现在东斯拉夫人的语言中。而有关经济事务的俄罗斯谚语主要也是反映农业劳动的。这些都突出地证明,农业经济早就成为俄罗斯民族的主要生产形态。到公元8—9世纪,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犁、锄、镰、斧等铁制农具已广泛使用在农业中。伐林耕作逐渐被田地耕作取而代之,农耕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完全确立。
俄罗斯平原自然气候条件十分恶劣,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农业生产不得不进行粗放式经营,广种薄收,成效并不理想。因此,俄罗斯民族的先民们为了弥补农业经营的不足,在从事农耕业的同时,往往也经营林业和畜牧业。而东欧平原上森林密布,草原辽阔,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为经营林业和畜牧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林业和畜牧业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一直与农耕经济相生相伴,成为俄罗斯民族先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村社是贯穿俄罗斯历史的最基本的生产组织
村社是俄罗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结构。俄语中有几个表达:在北方称作“米尔”,与世界是同一个词;在南方叫“维尔福”,另外一个词是oбщинa。“米尔”除了表示“村社”“世界”之外,还有“和平”“和睦”“安宁”等含义。oбщинa在俄语中除表示村社外,还有公共交往等意思。
俄罗斯的农村村社是在东斯拉夫人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性社会经济组织。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以血缘、地缘和宗教缘为纽带,以习惯和传统法则为基础。它的组成单位是家庭,若干家庭组成一个农村公社。农村公社在疆界上往往与自然村落相同,因而人们又称之为村社。
村社之所以成为俄罗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形式,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地的地理环境关系决定的。俄罗斯平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森林茂密,开垦困难,且气候寒冷,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时间短暂,加上生产水平低下,使得集体劳动和团结协作更为迫切和必要。为了便于组织生产和交往,村社这种集中居住,共同开发土地的地城联合体便应运而生。
其次,村社能够成为俄罗斯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结构,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政权对其进行的强化、改造和保护。俄罗斯村社从国家政权形成之日起,就不断受到政权有意识的改造,逐渐成为有利于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和收入来源的基层行政和纳税组织。因此,国家政权总是有意识地强化和积极保护村社。统治者中甚至有人声称:“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
俄罗斯村社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辅罗斯时期。基辅罗斯时期的农村村社在北方称作米尔,在南方叫维尔福,与绳子是同一个词。为什么用绳子来称呼农村村社呢?通行的说法是,村社用绳子来丈量土地。但俄罗斯历史学家巴甫洛夫-西利万斯基反对这种解释。他认为,维尔福可能源自日耳曼的北方部族的会场“神圣的套索”,能表示一乡领土上的一个中心点,也就是召开米尔大会的地方。
尽管基辅罗斯时村社的经济和生产职能在史料中记载不多,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作为国家的基层组织,行政司法自治,是统一的集体和纳税单位,得到王公政权的承认。
俄罗斯村社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莫斯科公国时期,村社的主要形式是黑乡。巴甫洛夫-西利万斯基把黑乡叫做乡社,按照他的说法,“乡”这个词在税册中用于两个意义:一是新的意义——行政区,另一个是古代意义——作为农民联盟的村社。黑乡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提供徭役,实行行政司法税收自治,全部土地属于黑乡集体所有,个体农民只有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
俄罗斯村社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17世纪以后至19世纪前半叶。这个时期俄罗斯村社的主要形式是重分型村社,它是随着农奴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这一体制中,农民隶属于村社,村社隶属国家,而国家将其赐予贵族并形成村社社员与农奴的身份合一,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农民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重分型村社的特征是政社合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连环保、赋税统一分摊等等。
俄罗斯村社以后的发展经历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和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并在20世纪苏联的农村集体化中寿终正寝。
1861年的改革废除了农奴制,保留了农村村社。村社的基本特征犹存,只是村社农民由贵族之奴变为村社之奴。村社社员从村社领取的份地因贵族割地成立贵族农庄而大为减少,而负担却因获得身份的解放而向贵族集体支付赎金而加重。
斯托雷平改革旨在摧毁俄罗斯传统的村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从而为沙皇专制统治培植社会支柱。(www.zuozong.com)
历史上,俄罗斯农村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它与专制主义的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俄国宗法制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温床,具有鲜明的特点。村社在经济方面的职能有:(1)组织管理生产劳动协作;(2)重分土地;(3)分摊赋税徭役;(4)提供社会救济。
(三)农奴制是俄罗斯中世纪主要的经济制度
农奴制是俄罗斯中世纪农业经济生活中长期保持绝对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俄罗斯的农奴制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连带产物,是封建制度下封建主对农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超经济强制行为,实质上是封建专制主义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极端体现。
在俄罗斯,农奴制的形成开始于地主把农民逐渐农奴化。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出现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农奴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早在基辅罗斯时期(公元9—12世纪)就出现了依附农民和家奴。依附农民往往是因为债务关系而沦为典身奴、契约奴。家奴主要来源于战俘、罪犯、家奴后代和卖身为奴的人。依附农民和家奴可以说是最早的农奴。然而,农奴制度在俄罗斯的最终确立和普遍实行,却是封建地主把农民逐渐农奴化和国家政权逐渐强化农奴法相结合的结果。
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是俄罗斯农奴制形成的关键时期。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以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特别是服役贵族的封地制的迅猛发展,国家政权和封建主都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控制。在此背景下,完成俄罗斯国家统一的伊凡三世颁布1497年法典。该法典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规定农民只能在每年的尤利节(农历11月26日)前后一周内才能迁往他乡。1497年法典实际上把农民对封建主的依附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到16世纪80年代,政权还连续实行禁年,废除尤利节,禁止农民迁徙,把农民最后一点合法权利彻底剥夺。
标志农奴制在俄罗斯最终确立是政府颁布的1649年法典。该法典规定,凡是登记在地主名下的农民,不但个人终身而且连同子女亲属世世代代都依附于地主。1649年法典以后,农奴制在俄罗斯不断发展,政权通过人口调查、征收人头税、颁发身份证、扩大农奴制使用领域等措施,强化对农民的控制。到18世纪,农奴制发展到顶峰。
农奴制是野蛮和效率低下的经济体制。与西欧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农奴制形成较晚。当西欧国家喊着天赋人权的口号纷纷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俄罗斯却还在发展和巩固惨无人道的农奴制,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农奴制得以在俄罗斯确立和发展,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形成和巩固的需要。可以说,俄罗斯的农奴制是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连带产物,国家政权在农奴制确立中起了主导作用。
其次,农奴制得以在俄罗斯确立和发展,是由于封建主出于剥削农民的需要而不断推进农民的农奴化。俄罗斯劳动力匮乏,封建主要想获得更多的剩余产品,在掌握土地的同时,更需要耕种土地的劳动力。而且在粗放经营条件下,要提高经济效率,必须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因此,封建主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的依附。而农奴制正是用强制性手段强化地主对农民的控制,从而保证其对农民的剥削。
再次,农奴制得以在俄罗斯确立和发展,与农村村社被纳入封建制度轨道,成为地主控制农民的绝佳工具不无联系。
俄罗斯村社是农民的农业合作组织,在俄罗斯封建化过程中,它曾顽强地抵抗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保护村社农民不受农奴制束缚。然而随着俄罗斯封建化过程的不断深入,农村村社不断被改造,最终被纳入封建制度的轨道,不仅村社组织在封建领地被保留下来,而且与农奴制相得益彰,成为政权和地主控制农民的绝佳工具。
总之,在农奴化过程中,地主为了方便剥削和管理,把地主土地制度与村社结合起来,保留村社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使村社成为农奴制村社。在农奴制下,作为农奴的村社成员,生活中的一切越是受到村社周到细致的安排和监督,就越是安分守己地履行村社成员应尽的义务,也就老老实实世世代代地居于农奴的地位,农奴制也可年复一年地发展巩固。
农奴制是野蛮和效率低下的社会经济制度,“渗透到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它促进了指令性经济、政治专制制度、社会和家庭中极权主义关系的形成,阻碍了城市、资产阶级、私所制及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发展,限制了社会的人口流动,用普遍的奴性观念毒化了人民的社会心理,造成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一些负面特征。”
然而农奴制毕竟是适应俄罗斯地缘政治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正如O.克里斯普所说:“俄罗斯经济落后不是由于农奴制关系在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经济落后才产生了农奴制。”因而,农奴制的历史作用不应抹杀。
由于农奴制的野蛮残酷,效率低下,随着农民的反抗日益增多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农奴制存在的道德根基逐渐丧失,反对农奴制的社会舆论和进步力量坚决要求改革农奴制。而俄罗斯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直接推动俄罗斯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本主义的改革。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铺平道路。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关于废除俄罗斯农奴制的法令,同时签署了特别宣言,在俄罗斯延续了几百年的农奴制寿终正寝。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