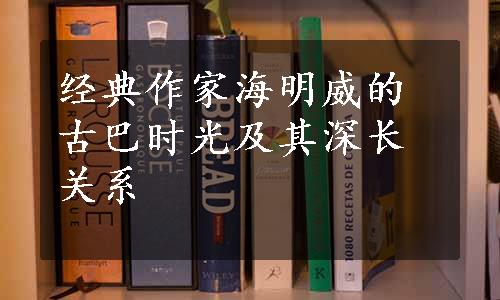
经典作家的古巴时光
撰文/夏榆
“即使印第安人消失不见,甚至所有人类都消失不见,墨西哥湾流也会一直静静地流淌下去”,这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旅居古巴时写下来的文字。
一生行旅不羁、四海漫游的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长期旅居古巴。“他的房子位于哈瓦那近郊的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地区。在房子西南一个外形方正的角落里,有一间特设的工作室,但他偏爱卧室,唯有小说里的角色能驱使他爬上角楼。”1958年,《巴黎评论》记者乔治·普林顿在古巴访问海明威时对他在哈瓦那的居所和工作状态有详尽的描述:“他是个严于律己、自我约束力极强的人,直到晌午时分,他才会拿起圆头手杖离开房子,到泳池边开始每日半英里的游泳。”
作为逝去时代的文学英雄,海明威影响过很多杰出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声称,海明威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时候,马尔克斯在巴黎遇到时为美国著名时装模特儿的海明威孙女玛尔戈·海明威,他们一起吃饭。“她滔滔不绝地谈她的祖父,而我则谈我的祖父”,马尔克斯说。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期间马尔克斯向外界讲述当年他初到墨西哥接到朋友的电话被告知:“海明威那老东西前一天早晨7点30分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凯特丘姆拿猎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了”,马尔克斯追忆道:“这件荒唐事如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留在我的脑海里。”
海明威将古巴看作伊甸园和钓大鱼的天堂。如今,他用一种决不妥协的目光凝视着这个正在转型的国家以及那些幻想着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
强悍而脆弱——海明威在古巴
1957年秋天,海明威在古巴的寓所观景庄开始动笔写作《流动的盛宴》。
这是他对青年时期在巴黎生活的回忆。辞去新闻职业、决心从事职业文学写作的海明威饱尝生活的艰辛,经常要忍受饥饿、物质匮乏以及写出的作品被出版机构频繁拒绝。然而他有美好的爱情,有坚定的信念和持久写作的毅力。那段时光艰辛而精进,困顿而甜美。这是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对往昔岁月的追念。在此期间他偶尔回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在西班牙旅行时也在写作这本书。1960年春重返古巴观景庄完成初稿,同年秋天返回美国,在凯彻姆他的家中做最后润饰。就在这部回忆录完成的第二年,海明威在他的凯彻姆住所用一支猎枪向头颅开枪自杀了。
“他自杀那天,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威尔士·海明威睡在爱达荷州克川市海明威居所楼上的主卧室里,1961年7月2日早晨她被几声以为是‘抽屉砰砰关上’的声音吵醒”,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后来追忆他的文学榜样海明威。
强悍而脆弱,乐观又绝望,这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显示出来的双重性。1954年是海明威祸福相随的年头,这年,海明威遭遇意外事故的频率达到了最高峰。先是乘坐飞机到东非打猎时,两次遭遇飞机失事,落下脑震荡、脊柱碎裂、烧伤和内伤并被通报死亡。他幸存下来,也因此有了一次独特的读自己讣告的经历。据卡佛回忆,他在少年时看到过晚报刊登的海明威相关消息的新闻照片。“他正满脸笑容地举着一张报纸,那上面登着他的照片和宣布他死讯的通栏标题。”也是在这一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12月7日,我应邀赴斯德哥尔摩报道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瑞典学院常务秘书斯图尔·艾伦先生相邀参访瑞典学院。艾伦先生作为常务秘书在1987年为俄裔美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和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授过奖。满头银发的老人翔实解说诺奖历史上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或者缺席颁奖的作家。
海明威当年因为头部重伤而缺席颁奖典礼,在那次颁奖仪式上,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发表给海明威的授奖词:
一位老人坐在科希玛海边凝视那位与他极为相似的大文豪。
Floridita酒吧被作家海明威看作代基里酒的发源地。图为吧台一角的海明威青铜像。
现在我们大家谈论的正是这样一位先行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他的任何一位美国同道比,海明威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寻求准确方式来表达意见的朝气蓬勃的民族。海明威本人也与一般文人迥然不同,他在许多方面表现了戏剧性的气质和鲜明的性格。在他身上,那股勃勃的生机按照它自己特有的方式发展着,没有一点这个时代的悲观色彩和幻灭感。
诺贝尔博物馆与瑞典学院相邻,博物馆陈列着百年历史中获奖者的遗迹—生平影像、书籍影印、手稿、演讲音频。观众走进纪念馆可以通过遥控器,任意选择想要了解的获奖者的情况,戴上耳机就可以听到获奖者的演讲实况。海明威是我热爱的作家,记得当时特意找寻他的文学演讲而未得。现在我手里存有《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和获奖言说》,再次读到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授奖词:“人们应该记住,勇气是海明威作品的中心主题—具有勇气的人被置于各种环境中考验、锻炼,以便面对冷酷、残忍的世界,而不抱怨那个伟大而宽容的时代。”人性是复杂的。仿佛是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做否定式证明,海明威后来生病,患上偏执狂和忧郁症,在接连两次监禁于梅约诊所时,因为接受了电痉挛疗法而失去记忆,最后用猎枪自杀身亡。
海明威生于1899年,可以算作20世纪的同龄人。他这一代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残酷、冷漠和没有意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在幸存者身上留下了烙印,海明威本人也亲历其中,并于19岁在前线身负重伤。他说:“人类莫名地疯狂。让自己陷入最巨大的、致人于死地的大屠杀中,这只有在人类的土地上才会发生。”
海明威的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其中三次离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意大利当救护车司机并为此负伤,在西班牙内战(1937-1939年)、中国抗日战争(1941年)和欧洲反法西斯战争(1944-1945年)中他作为战地记者表现优异。战后他的个人生活发生逆转,打猎、钓鱼、狩猎旅行、在法国和古巴寄居、斗牛、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最后在爱达荷州自杀,这是跌宕起伏、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当我再次阅读海明威,从他的生平轨迹寻访他的生命故事时,遥想他在古巴的岁月,或许就如他所言:“必须天天面对永恒,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海明威与古巴的关系可谓深长。1940年他在出版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之后,与第二任妻子离婚,同作家玛瑟·盖尔荷恩结婚。次年,他与玛瑟来到中国采访抗日战争,当时还会见了蒋介石与宋美龄;之后旅居古巴,在哈瓦那的瞭望农场住下来。海明威在哈瓦那多有惊人之举,改装私人渔船“皮拉尔号”,追缉古巴近海的德军潜艇;在此期间他以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在伦敦遭遇车祸,头部负伤。为解放巴黎与游击队一起搜集情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明威返回古巴。同年与玛瑟·盖尔荷恩离婚。
海明威使用过的打字机和他生前的护照。
海明威使用过的打字机和他生前的护照。
海明威一生都在谈论自杀,在他的有生之年,身体遭到种种重创,就像是和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一场拳击赛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打猎,还是在创作中上前线打仗,海明威的意识中总抹不去“杀戮”的念头。他的一生都在狩猎:在非洲猎杀狮子、豹子和大羚羊,在落基山脉搏杀灰斑熊,在怀俄明农州射杀松鸡,在法国射杀鸽子,走到哪里他都会有可杀的猎物。即使在猎杀之后,这些动物仍然没有逃离他的视野。“杀戮”的意识使他饱受争议。
他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曾经讲述,在古巴时的某一天,海明威颇费了一番周折,钓到一条重达512磅(约合232公斤)的马林鱼,并将它运回港口,引起公众的一片欢呼。但他对这一切还不满足,大家喝酒庆祝之后的凌晨两三点钟,他又独自回到了码头,借着月色,用滑轮把大鱼吊了起来,当沙袋练习拳击。
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就是讲述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与大鲨鱼搏斗的故事,老人就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以北的海面上捕鱼。《老人与海》的写作,证明海明威是猎手兼博物学家,这部作品塑造了文学史上经典的硬汉形象,成为海明威最具代表性作品。《老人与海》出版于1952年,最初发表于9月1日的《生活》杂志。小说出版后获得批评界一致推崇,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并最终助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来好莱坞以重金购得摄制权,由斯宾塞·屈塞主演,拍成电影获得第31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www.zuozong.com)
《老人与海》原作只有2.7万字,据海明威自述,他曾先后修改此书达200遍之多,可谓千锤百炼,炉火纯青。老渔夫圣地亚哥的状态来自海明威多年来在湾流中钓鱼的经历。他观察、研究海洋生态物候。“大海也同人一样值得描述。这是我的运气好,我见过马林鱼交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在那一片水面上,我见过五十多头抹香鲸的鲸群,有一次我叉住了一头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鲸鱼,却让它逃走了”,1958年海明威对来访的《巴黎评论》记者说道。
海明威在写作《老人与海》时有一句名言被广为传播:“一个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老人与海》的主题,也是海明威的人生信念。然而十年之后,海明威被他自己打败了。
魔幻超现实——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
说到作家与古巴的关系,不能不说到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交往。
1956年的巴黎。在圣米歇尔大酒店,当时还是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与同为新闻记者的朋友普利尼奥·门多萨喝咖啡。其时他们都是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讨论到当时拉美的政治局势,包括古巴的政治变革。他们认为古巴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小伙子的努力上。“那个固执、莽撞的瘦高个儿的青年,正在墨西哥四处活动”,马尔克斯在他的自述中写道。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阿拉卡塔卡。少年时因哥伦比亚内战中途辍学。青年时期时任新闻记者的马尔克斯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海难而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后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不久该报被哥伦比亚政府查封,他被困在欧洲。同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枯枝败叶》。1959年马尔克斯为古巴通讯社“拉丁社”在波哥大和古巴工作。“拉丁社”由切·格瓦拉领导,同年,马尔克斯应邀参加古巴革命胜利庆典。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其时,对马尔克斯来说,卡斯特罗的名字并非完全陌生。保守派政府在1948年企图将卡斯特罗和另外几名大学生以某桩凶杀案的嫌疑凶犯逮捕。卡斯特罗在1959年革命成功后,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在加拉加斯美岭区旅馆的阳台上庆祝卡斯特罗的胜利。在马尔克斯看来,古巴革命意味着一个与以往迥异的、具有质的飞跃的唯一运动。“不是资产阶级抑或人们早已熟悉的政治寡头打败一个先前按照顺序篡夺权力的独裁者,而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些大胡子游击队员领导全体人民夺取了政权。这在整个拉丁美洲引起人们的赞叹、支持和深深地忧虑。”
当年的拉丁美洲,独裁者们像熟透的果子落地一样纷纷垮台。首先是阿根廷的胡安·庇隆,继而是哥伦比亚的罗哈斯·皮尼利亚,随后是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内斯。后来就轮到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倒台。同许多拉丁美洲人一样,马尔克斯希望到哈瓦那亲眼看一看那场汹涌澎湃的革命。1959年的春夏之际,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带着简单的行李,被一架由古巴人驾驶的双引擎飞机带往哈瓦那。飞机是革命者从前政府军缴获而来,是一件散发出难以忍受的尿骚味儿的老古董。他们参加报道“真相行动”—由卡斯特罗指挥的对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战犯的公开审判。
到达哈瓦那,马尔克斯和他的同行者立即被淹没在旗帜、橄榄绿军服和睡不着觉的人海中。人们没有工夫睡觉,对获得自由的庆祝与欢呼使他们难以入眠。马尔克斯与同伴走遍了哈瓦那,与人交谈,听卡斯特罗面对百万同胞讲话,从而触摸到了古巴革命的脉搏。为了让世界知道革命之后的古巴对独裁者的审判,卡斯特罗请来一些国家的观察员和记者旁听审判。
《马尔克斯传》描述了这次哈瓦那之行:“体育场内人山人海,正中央的四方框架里是身穿蓝色囚服面对法庭的罪犯。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直接面对着被审讯者,因而感觉到一个人死到临头的冷漠和恐惧。戴着手铐的被告惊愕于急切等待将他明正典刑的观众的呼喊、谩骂和笑声,他的眼睛呆滞,一直盯着脚上的意大利皮鞋的尖端,直至黎明时分听到死刑的判决。”这次审判给马尔克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从没直接写过这一审判,然而他从对战犯的审讯、审讯时出示的大量的证据材料中受到启发,构思了他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
马尔克斯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也是在哈瓦那。当时他途径卡马圭市作短暂停留。担任司令官的卡斯特罗在古巴腹地参加几个养鸡场的开工典礼也抵达卡马圭市。到了这里的小机场,饿坏了的司令官命人拿鸡给他吃,可是没有鸡。于是,卡斯特罗就以在美国旅客仍然经过的一个机场没有鸡吃这一弊端为题,发表了冗长而激动人心的演讲。经过他人的引荐,马尔克斯跟卡斯特罗会面握手,简要交谈,说明他的记者身份。
马尔克斯在哈瓦那待过90个日夜。当时的哈瓦那成为一座巨大的街垒,因为毒瘤般的反革命活动天天发生,而且古巴人还得防备着美国即将发动的入侵。马尔克斯所在的拉美通讯社所在的斜街不像街道,更像一条准备战斗的战壕:房上堆着沙袋,地下铺着厚厚的木板,枪支时刻处于伸手可及的位置。“哈瓦那是个不眠之城,犹如整个古巴是个不眠之国。拉美通讯社的工作人员在电传打字机、打字机或者照相机旁边困得要命,却几乎没有工夫打个盹”,《马尔克斯传》的作者达索·萨尔迪瓦尔写道。
后来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成为密友。据说卡斯特罗拨给马尔克斯一辆奔驰280,在哈瓦那市中心给了他一所带游泳池的房子,里面有4个佣人和1个花匠,还有一条只有极个别接待外宾的宾馆才能安装的国际电话线。据说卡斯特罗和马尔克斯无话不谈,包括倾诉内心的秘密。
“你仔细听着,我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亲密的、以真挚的感情维系的友谊是从文学开始的。1960年我们在拉美通讯社工作的时候,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跟他打过交道。我当时觉得,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讲。后来我成了著名的作家,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家,我们双方怀着非常尊敬、友好的心情见了好几次面,不过当时我并不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能超越我们在政治倾向上的亲近。”这是马尔克斯与友人浦里尼奥·门多萨的对话。
马尔克斯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合影。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拉美文学热潮开始飙袭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就在这一年,马尔克斯与门多萨做过一次长篇对话,对话集《番石榴飘香》也风靡中国。这次对话中,门多萨评论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的关系时说道: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不同,马尔克斯不热衷意识形态的问题。他和卡斯特罗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看待现实和理解问题的方式,加以加勒比海地区所特有的共同语言。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罗的密友,但是他和苏联政府官员以及统治共产主义世界的阴郁的官僚没什么交情。如果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苛刻眼光来看待马尔克斯,那么很难在政治上理解他。对于他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一回事,而卡斯特罗是另一回事,尽管古巴制度的许多特征来自苏联模式。然而支持军事独裁的拉丁美洲右派对马尔克斯深恶痛绝,把他视为卡斯特罗的代理人。“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呢?”他的敌人责问他。
在访谈中门多萨向马尔克斯提问:“如果古巴把苏联那一套制度作为自己的样板,那么你说的‘更加公正、更加民主的社会制度’肯定会像在苏联那样受到非议。你难道没有这种顾虑?”马尔克斯回答:“依我看来,古巴革命在经历了最初几场巨大的风暴之后,正在艰难地有时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进,不过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们大家满意的社会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你们始终坚持‘古巴是苏联的卫星’的偏见,而我却不以为然。你只需跟菲德尔·卡斯特罗打一分钟交道,就会知道他不听任何人发号施令。”
1962年,加勒比海地区发生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弹道导弹雷神导弹和朱比特导弹,苏联为挽回战略劣势,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谈到古巴和美国长期以来的紧张关系,马尔克斯说:
我认为,二十多年来,古巴革命一直处于危急状态,这要归咎于美国所持的不谅解和敌视的态度,他们不能容忍在离佛罗里达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样板。不能责怪苏联,如果没有他们的援助,就不会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这种敌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处在危急状态之中,被迫进行自卫以谋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在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区域之外。哪一天这一切都正常了,我们哪一天才能进行对话。
2014年4月17日,马尔克斯病逝于墨西哥。
2015年7月,美国与古巴恢复自1960年以来断绝的外交关系。
敌对长达五十多年的“宿敌”终于“冰释前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