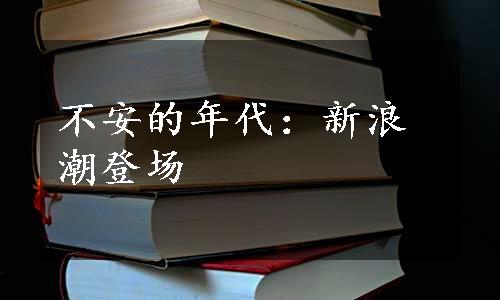
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新浪潮”一词最初来源于一次社会调查,“新浪潮”最开始并不是一个艺术名词,它只是用来形容战后的一批“新青年”的。在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过这样一批全新的青年。在美国,有“婴儿潮”“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等形容战后伴随经济繁荣成长的这批年轻人。在日本,则是“团块世代”和“太阳族”,他们大都出生在昭和前十年(1925—1935),童年大都伴随着战争,在少年时经历了战败以及战后社会的凋敝。他们经历过痛苦,即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了过来,但是少时的痛苦令他们难以忘怀。此时的社会不公现象又极大地刺激了这批年轻人的神经,经济发展的果实大都被有势力的财阀掠夺而去。同时又因为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势力之间的对抗,以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这些都促成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再度流行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之中,日本共产党1949年在议会得到了三十九席,成为了当时日本议会中的第三大党,青年学生们也在日本共产党的支持下走上街头,开始大胆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日后成为“新浪潮”骨干的三位导演都有年轻时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大岛渚更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位。在京都大学法学部就读的他,对自己所读的专业并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把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学生运动。他加入了京都大学学生联盟,并且经过选举成为了这个联盟的副主席。1951年天皇莅临了京都大学,大岛渚作为学生组织的带头人被拒绝进入会场向天皇提问,愤怒的学生在大岛渚的带领下在会场外高唱反战歌曲,同时同学们还将准备好的大字报张贴在会场外,这些大字报措辞激烈,甚至直斥“天皇是骗子”。这次运动很快就被警方和校方一起镇压了。
1953年,在大学毕业一年前,大岛渚当选了学生联盟的主席,他再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这次游行得到了因坚持武装斗争而被开除出议会的“在野党”日本共产党的支持。但是很快,这次游行在军警的镇压之下失败了,多名学生受伤或者被捕。作为领导人的大岛渚的毕业档案被贴上了“赤色分子”的标签。
这一时期日本的几大名校中,有许多年轻大学生都和大岛渚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在大学里把他们的青春投入变革社会的运动中去了,可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成为了整个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他们的热血和正义感反而让他们本该激扬的青春蒙上了灰尘,带着“赤色分子”标签的他们在毕业后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大岛渚此时也面临着失业的困扰。时值冷战期间,美国“麦卡锡主义”[29]之风也吹到了日本。在这股压力之下,各用人单位都不敢聘用这些“赤色分子”。而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恢复,日本人的观影需求愈发旺盛,各大片厂原有的学徒培养体制难以培养出足够的导演进行电影创作,各大电影公司不得不向社会广纳人才。本不喜爱电影的大岛渚为了解决自己的职业问题,终于在1954年进入了松竹电影公司做一名助理导演。
日后与他齐名为“新浪潮三杰”之一的吉田喜重,这时也是刚刚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毕业,在刚刚进入片厂工作时,不喜欢电影的他本想回到学校。正在迷茫之时,他听取了老师渡边一夫(Kazuo Watanabe)[30]的建议,决定继续留在电影圈。同时,因为市场对电影的需求旺盛,他的薪水也跟着水涨船高,高额的薪酬和老师的建议让他打消了离开电影圈的想法。也就是在这之后,他结识了有着相似经历的助理导演大岛渚。
2-10 吉田喜重在影片执导现场。(Alexander Jacoby, Rea Amit拍摄)
大岛渚和吉田喜重并不是此时日本影视圈新人的个例。此时的日本电影圈吸收了一大批刚刚从各大名校毕业的高才生做助理导演。据吉田喜重回忆,与他同年进入松竹公司的八位助理导演中有五位是来自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剩下三位分别来自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和庆应私塾大学。所以大岛渚和吉田喜重也很快就在公司内部找到了自己的同道,他们创办了一本名为《七人》(Shichijin)的杂志以刊载他们写出的剧本。吉田喜重还与他在东京大学的好朋友,同样在松竹公司工作的大学同窗石堂淑朗[31]以及在进入片场工作时认识的校友仲村继宏[32]和宫川淳[33]一起写作,同样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田村孟[34]也加入了他们[35]。这些名校毕业生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于艺术有着自己独特的品位。他们对于旧制片厂那套“陈词滥调”,自然是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他们在大片厂体制内形成了自己的团体,这些团体成为了日后塑造“新浪潮”和1960—1970年代日本艺术电影行会(Art Theater Guilt,以下简称ATG)电影的主力。
与此同时,增村保造刚刚结束了罗马电影实验中心的学习,回国加入了松竹电影公司。他曾经在1948—1950年间短暂加入过松竹公司,在担任了成濑巳喜男和沟口健二的助理导演之后,他离开了松竹公司到东京大学哲学部读书。在东京大学读书时,他深受英伦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36]和洛克[37]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同时自1940年代末以来,为了彻底肃清日本的军国主义,许多日本的知识分子主张进行一场“主体革命”(The transformation of shutaisei)。他们认为,一场彻底的社会变革必须要先从变革每个个体的主体观念开始。此时在东京大学读书的增村保造就深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在毕业以后增村保造有幸得到了一份由意大利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帮助他在意大利继续修读电影。在电影实验中心读书之余,他还兼职做了一名专门报道日本电影的记者,并且1954年他在《黑白》(Bianco e nero)杂志发表了西方第一篇介绍日本电影史的文章。这篇文章写了整整六十页,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用西方电影艺术更新暮气沉沉的日本电影。在意大利读书的时光给了他独特的品位,同时也让他深入了解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及意大利即兴喜剧传统。这些都帮助他塑造了电影观念。他曾经在1958年这样描述自己初到欧洲时的感受,“直到我呼吸到欧洲的空气时,我才第一次感觉我明白了‘人’这个词的含义,在日本,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一直是缺失的,即使人的价值和美好在日本已经被当作一种抽象的概念而被接受,但是却是不能变为现实的。一个日本人,只能在贫穷、衣衫褴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挣扎,只有当我踏上欧洲的土地时,我才感受到了‘美妙,富有力量的人性’(beautiful, powerful humanity)的真谛”。[38]
这一时期,松竹公司仍然在坚持制作他们传统的“大船调电影”,公司最为倚重的是老导演小津安二郎,而他的助理导演就是筱田正浩。在早稻田大学修读戏剧史的筱田正浩比之前提到的“新浪潮”导演要早两年进入松竹公司。他曾这样描述他那时的工作以及对小津安二郎的印象,“我1953年进入松竹的时候,松竹有位卓越的绅士,那就是小津安二郎。他穿着纯白的衬衫,戴着纯白的帽子,坐在黄色的面包车里,周围一尘不染,摄影棚也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我们这些当副导演的觉得,打扫卫生就是副导演的主要工作。那种严肃的工作作风令人十分感动。可是我觉得,在他的画面中所反映的那种美,根本就没有反映政治啊!不但是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的政治,制片厂之外的政治、日本之外的政治根本都没有得到反映”。[39]渴望反映现实以及政治,渴望揭开道德的“伪善”,渴望对日本电影来一次彻底的革命,是这一批年轻导演想要独立执导电影的最大动力。
这一批导演中第一个获得长片拍摄机会的是增村保造,得益于他曾经在沟口健二等大导演手下工作的经历,他在1957年就率先拍摄了由川口浩等人主演的影片《吻》(1957)。这部电影在风格上延续了松竹公司“大船调”的风格,影片讲述了几个日本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影片整体节奏较为平缓。这部电影在市场的表现还算不错。这让他得到了执导第二部作品的机会,也就是他的成名作《巨人与玩具》。
《巨人与玩具》是增村保造的成名作,影片通过宣传课课长和职员的中心视点,表现了正常人被商品社会所扭曲的生活。这部电影直接暴露了在消费主义社会,女性作为一个“消费品”的现实。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人都有着商业社会“精于算计”的特点,出身平凡的女主角京子为了得到代言人的职位与宣传课职员阿西恋爱,在获得代言人职位之后,想要进一步成为大明星,所以甩掉了阿西。而课长大田也有自己的算盘,在挖掘京子后,他先让摄影师拍摄了京子大量的挑逗照片,让京子成为一个写真明星,再让她成为代言人,进而促进公司糖果的销量。影片最后大田的计划失败了,在激烈的竞争之下甚至不得不自己带病穿上闷热厚重的航空服上街宣传,他的手下阿西同情他并代替他忍受了这份屈辱。
这部电影推出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同年的《电影旬报》年度十佳中位列第十,据说增村保造在片场有一句口头禅,“他们说我总是提前了十年”。这部电影在战后经济刚刚腾飞之时就预言了之后日本社会的状况。在消费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变成了只为自己利益计算的“理性人”(rational people)和“经济动物”(economical animals),每个人的价值都被商品系统所物化、定价。所谓的“人性”在冷冰冰的社会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这部电影在当时的日本电影中独树一帜,一来增村保造在这部电影里表现了他别具一格的蒙太奇手法,同时这部电影就如同上了发条一样,以一种极其亢进的速度进行叙事。片中所有人的台词都说得很快,每个镜头的时间也都很短,日本电影中传统的镜头与镜头之间的留白也一并被取消了,再配上严谨的几何构图和极致的配色。整部电影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代浮世绘。这幅浮世绘所描绘的世界,高速运转容不得半点喘息,人情淡漠容不得丝毫的同情。所有人都在向着冷冰冰的数字——绩效看齐。
2-11 大岛渚导演《爱与希望之街》(1959)
在狭义上,这部电影不属于“新浪潮电影”,然而这部电影又有着与同时代传统日本电影完全不同的风格,其影片风格大胆前卫。而社会批判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后来的狭义“新浪潮电影”对社会的关切形成了呼应,是一部完全不同于之前松竹公司出品的“大船调”的家庭情节剧,所以也有人把它当作“新浪潮”运动的一个开端。实际上,增村保造对大岛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等新导演们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一派全新的日本电影马上就要破土而出了。
1959年,因为在一次剧本征集中大岛渚表现优异,获得了松竹总监城户四郎的赏识,终于赢得了自己独立执导电影的机会,他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爱与希望之街》是一部典型的带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影片讲述了一个出身贫穷的少年正夫,不得不靠卖鸽子的小伎俩维持生活——因为鸽子记路,所以卖出去的鸽子又会飞回到正夫这里。富家女京子向他买了鸽子,京子的天真善良打动了少年,少年为自己的欺骗行为感到内疚。少女京子原谅了少年正夫,并且推荐正夫参加自己哥哥负责的工厂的录用考试。但是正夫因为卖鸽子经历被拒录了,一怒之下少年砸坏了自己的鸽笼。在影片最后,京子的哥哥打死了飞向远处的白鸽,也打碎了少年正夫回归社会的希望。
影片中阴暗潮湿的街道,低矮压抑、封闭的空间无时无刻不在控诉着社会的不公对于少年正夫的摧残。影片通过对于贫民窟的空间展示直接指出了“贫穷”是由社会导致的,而不是由所谓的“道德沦丧”才让正夫不得不卖鸽子求生。
这部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松竹公司的领导们曾经多次要求大岛渚更改剧本,按照大岛渚原本的构思,影片本来应该叫《卖鸽子的少年》。公司为了让影片在市场上销路更广,又把影片改为了《爱与希望之街》,好让影片更加“乐观”一些。但是大岛渚仍然在影片内容部分坚持自己的想法,在影片制作完成后,大岛渚马上就被公司雪藏,影片本身也只被松竹公司投放到了一些二线影院进行小规模的放映。虽然影响不大,但是这部电影仍然得到了一些影评家的注意,这部电影以其社会批判的主题、左翼的立场以及在日本电影中全新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日本电影史上被广泛地认为是狭义上的日本“新浪潮电影”的开端。
据大岛渚的回忆,时任松竹总监的城户四郎在剪辑台上看完这部电影后对大岛渚说,“行了,你也是个明白人,好好反省再拍下一部吧”[40],这一反省就是大半年。直到1960年,大岛渚拍出了真正让他名声大噪的《青春残酷物语》,这部电影的成功,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www.zuozong.com)
1960年,是日本历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日美安保条约》签署,这一条约几乎正式宣告了日本对美国的附属地位。《日美安保条约》允许美军在日本各地驻军,同时规定了日本有协助美国共同防卫敌国入侵的任务。日本全国因此爆发了大范围的反美游行,国会从1959—1960年一共收到了17万封请愿书,一年内新成立了1637个请愿组织,一共有330万日本人参与了反美游行。日本人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附庸,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人中再次高涨起来。同时日本电影工业在经历了五年的高速增长后,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日本电影上映数量在196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47部,全日本境内一共有7457块电影银幕。然而盛极必衰,繁荣表象下的泡沫也开始逐渐破灭。随着电视占有量的逐步提升以及录像带的出现,电影业在这之后每况愈下,同时又因为许多公司在这几年为了赚取票房粗制滥造了一批本土电影,使本国观众对于本土电影的信赖程度逐步下降,导致越来越多的观众不愿意观看日本本土电影。另外,在工业方面,日本也开始了自己的能源结构转型,煤炭在供能中的主导地位逐渐开始被石油取代。这引起了日本许多地区煤矿业工人的不满,进而爆发了全国性的煤炭工人罢工。再加上由于日本共产党在1950年代初期的斗争失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有关斯大林的讲话[41]外泄和匈牙利十月事件[42],原先团结一致的日本共产党内部也开始分裂,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脱离了日本共产党开始自立门户,成为了所谓的“新左派”,以区别日本共产党等“老左派”。而区别“老左派”与“新左派”的标志之一,就是是否坚持日本革命由日本共产党领导,是否要继续坚持正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
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电影《青春残酷物语》诞生了,这部电影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片表现了两个年轻人藤井清和真琴在当时一片混乱的社会背景中的爱欲纠葛以及他们理想的幻灭。这部电影为了表现电影中年轻人的焦躁不安大量采用运动摄影,剪辑凌厉,带有法国“新浪潮”的气质。同时这部电影还和当时刚刚出现的彩色宽银幕技术进行了极佳的结合。
2-12 大岛渚导演《青春残酷物语》(1960)
影片中第一个游行的场景就展现了大岛渚惊人的才华和离经叛道的气质,虽然几乎只是一笔带过,但是在当时的日本电影中,很少有导演敢于在影片中放入政治性意味如此浓厚的场景。在这个游行场景之后,大岛渚紧接着加入了一个新闻片段,这个片段来自电视台对警察和学生冲突的报道。在开篇这样的政治场景之后,影片开始展现主人公。处在游行队伍旁的两位主人公是完全处于这场游行和政治之外的角色。这种“局外人”的感觉本身也代表了那一代许多处在政治漩涡中的日本青年身上的虚无感和幻灭感。不过影片中仍然有这样一个场景,大岛渚通过四个角色的对话明显地表达了导演对当时政治情势的看法。在影片中真琴有个姐姐由纪,由纪和她的前恋人秋本医生都是195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曾经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秋本在影片里是一名做非法堕胎手术的医生,这种安排本身就表现了导演的一种悲观态度。秋本医生这个角色身上就有导演大岛渚的影子,就像本来不想做电影导演的学生运动领袖大岛渚在毕业后为了生计不得不成为一名电影导演一样,秋本也是因为学生运动影响不得不成为了一名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在这个场景中,秋本和由纪显示了和其他年轻人完全不一样的悲观神态。
秋本告诉藤井清:“我们曾经年轻过,我们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努力过,但是墙壁坚固如故。”在谈到1950年代的学生运动时,他似乎也已经预感到了下一个十年的学生会和他们一样遭遇失败。然而藤井清却是这样回答秋本的,“我们没有梦想,我们不如你们”。这个场景深刻地揭示了藤井清和真琴那一代青年人的心理处境,他们夹在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左翼的“革命”与“平等”,以及日本传统的“礼数”与“民族”的价值冲突之中。所以迷茫焦虑的他们对于一切“主义”和“价值”都失去了信任,既然所有的路都走不通,那么我们就好好放纵自己吧!电影中这对年轻情侣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只是一种单纯的为了“叛逆”而“叛逆”的行为,是无任何目标的。大岛渚借这部电影,真正地表达出了“新浪潮”的一大精神主题,那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而这部电影正好让我们冷静地看到了那一代年轻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青春残酷物语》在市场获得成功以后,大岛渚在四个月内拍摄完成了《太阳的墓场》(1960)和《日本之夜与雾》(1960)两部作品,《太阳的墓场》明显与曾经风靡的“太阳族电影”有关,在影片中出现了大量日本国旗的镜头,日本国旗中间的太阳明显指涉了“太阳族”。而影片中出现的釜崎贫民窟则明显是人为建造的,大岛渚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影片中拍摄的贫民窟,指出了他这样拍摄的用意,“当时天皇出访俄罗斯,途经广岛,他不希望见到任何贫民窟”。所以日本政府将沿线贫民窟全部拆除。片中的贫民窟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方,片中所有的角色都没有走出过贫民窟,这个贫民窟里充斥着犯罪和凶杀,似乎没有任何文明世界的规则可言。影片最后结束于一场大火,结束于虚无之中,这部作品甚至比《青春残酷物语》更加虚无。
在紧接着的两个月后出品的《日本之夜与雾》中,大岛渚对自己的电影美学作了一次彻底的颠覆性尝试。与之前的作品不同,这部长达一百零七分钟的影片只有四十三个镜头,影片借助一场婚礼展现了两派左翼青年对待“安保斗争”和日本历史的观点冲突。由于之后日本出现了一起社会事件,一位右翼少年刺杀了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松竹公司迫于经济和政治压力,在影片上映四天后就将电影撤档。大岛渚借这部电影中两派青年人的辩论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威权面前,手无任何权力的学生们能够改变现实吗?大岛渚在这部电影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能。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大岛渚拍出了四部作品,平均下来制作每部电影只花费了三个月,而且每部作品几乎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杰作,这在世界电影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2-13 《日本之夜与雾》电影海报。
同年,筱田正浩、吉田喜重等人和大岛渚一起晋升为了导演,这批曾经只能聚在一起喝酒助兴,大谈特谈电影美学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执导自己的电影了。在大岛渚之后,筱田正浩拍出了《恋爱单程票》(1960),影片名字明显受到了美国流行歌手尼尔·萨达卡(Neil Sadaka)的“忧伤单程车票”(One-way ticket to blues)的影响。筱田正浩在一次接受专访时,直言这首歌引起了他对摇滚市场虚假营销的愤怒[43]。导演在这部电影中把目光投向了摇滚乐,这部影片几乎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同步引爆了摇滚电影的潮流。吉田喜重也迎来了自己的拍片机会,他在1960年拍出了自己的处女作《一无是处》和《血的饥渴》。在大学修读法国文学的吉田喜重关切的问题显然比他的同代人更加形而上。这两部作品的主题都与死亡有关,其主人公都有“两次死亡”的经历,第一次死亡往往是虚构的、符号化的。例如在《一无是处》中,男主人公淳刚在开场表演“被枪杀”,在影片最后,他才真正地、生物性地死去。这三位导演的作品,在1960年的电影圈引起了轰动,这些电影一改往日松竹公司主流家庭电影的底色,都把目光放在了离经叛道的年轻人身上,风格大胆前卫,电影的表现方式更加具有现代艺术气息。
1960年5月5日,《读卖周刊》为了配合《青春残酷物语》一片的上映,记者长部日出雄和大昭正写了《日本电影的“新浪潮”》一文。这篇文章用当时正在法国流行的“新浪潮”一词来形容以大岛渚为首的这批松竹新导演的电影作品,文章中一共提到了三位导演,他们分别是大岛渚、筱田正浩和吉田喜重,在最狭义的概念上,这三人才是松竹“新浪潮”的主力。但是许多史学家愿意把羽仁进、增村保造等导演一并列入“新浪潮”这股运动之中,因为他们的电影都有着颠覆日本传统电影美学的特征。在1960年5月5日,日本电影史翻开了全新的、璀璨的一页。
“新浪潮”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影评概念,和超现实主义运动或者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艺术运动不同,后两者都是由艺术家自主发起,并发表创作宣言,自己制定艺术纲领的。而“新浪潮”则是由影评人对于一类作品的总结,在大岛渚和吉田喜重看来,他们并不属于“新浪潮”这个流派,或者压根就没有“新浪潮”这样的一个流派。在1966年,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曾经访问日本,筱田正浩拒绝出席戈达尔的见面会,大岛渚和吉田喜重在见面会上与戈达尔并无交流,吉田喜重表示他和大岛渚都不会在“新浪潮”的旗帜下单独与戈达尔见面[44]。而影响大岛渚、吉田喜重和筱田正浩的电影导演也都和“新浪潮”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岛渚表示路易·马勒和瓦伊达对他影响很大,吉田喜重则表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安东尼奥尼和伯格曼。当时的日本导演似乎对法国“新浪潮”导演们也不怎么感冒,受到特吕佛称赞的中平康曾经这样评价法国“新浪潮电影”,“怎么说呢,(看法国‘新浪潮电影’)就像看到朋友写在一张粗糙纸上的满是错别字的小说”。四方田犬彦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法国的“新浪潮”导演中除了里维特,都没有在片场做助理导演的经历,他们对于“新浪潮”中那些违反“语法规则”的镜头组接方式很是反感。或者说,他们当中的另一部分人,在拍摄那些被后世称为“新浪潮电影”之前,完全没有看过法国“新浪潮电影”,认为自己不属于他们的流派,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同时,“新浪潮”也没有一个像法国“新浪潮”的《电影手册》杂志一样的策源地。在一定程度上,在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和《日本之夜与雾》之间的风格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新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主题先于表现风格的。在筱田正浩的专访里,他就承认那个时候的自己认为电影一定要与政治有关的想法是“极其愚蠢的”。这种对于政治直接的介入,渗透在这一时期所有日本导演的创作中。所以“政治”可以作为日本“新浪潮”的一个母题,而风格和“方法”在“政治”面前则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几千个镜头拍摄一部“政治”电影,当然也可以用四十八个镜头拍摄一部“政治”电影。
但是“新浪潮”也确实有一个团体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有明确的指向——就是日本的传统电影,这种电影的代表就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日本传统家庭情节剧电影“大船调”。就像法国“新浪潮”把他们的矛头指向“优质电影”,将其讥讽为“老父亲电影”(Papas kino)一样。美国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经提出“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解释这种新艺术家对老艺术家的反动。在这个情境里,小津安二郎等老导演就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里提到的“父亲”一样,而这些新导演就像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俄狄浦斯一样,渴望摆脱这种笼罩,在焦虑中他们实现了对“父亲”的反动,即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弑父”。但是在后期,这些“父亲”又会以强者的姿态回归到创作者身上来,所以在二三十年后的1980—1990年代,这一批日本“新浪潮”导演也逐渐开始理解了小津安二郎那一批老电影人。吉田喜重在晚年息影五年,专心致志地研究了他的前辈,同时也是他们那一批人的“敌人”——小津安二郎,写作了《小津安二郎的反电影》一书。在这本书里吉田喜重一边重新观看小津的电影,一边回忆了在松竹公司时与小津前辈交往的点点滴滴。同时借着这些他与小津交往的经历重新思考了小津当年对他们这一批年轻电影人的许多教诲,在书中他写到小津安二郎在病榻上对他的叮嘱,“电影不是事件,而是剧情”。吉田喜重在书中坦白,“现在这句话犹如幻听似的,仍在我耳边回响。但我至今仍然不明白小津这段话的含义”。然而年近古稀的他似乎已经有所得,“不过,从这句极其短暂的格言般的话语中,我还是能够理解到其中蕴涵着的某种启示。或许小津在对比性地使用‘剧情’和‘事件’这两个词语的同时,极其敏锐地区分开与我们人类相关的剧情和无非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最终,他想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思想:电影是描绘人的戏剧,无论这个戏剧具有多么大的冲击力,都不应该呈现偶然发生的事件”。[45]在筱田正浩的专访里,他承认,小津安二郎对于人类存在的那种乐观描写是“具有全世界意义的”。当他们年华老去,回首曾经被他们视为敌人的小津安二郎的作品,发现其实他们所反对的东西,不过只是小津安二郎电影中最表层的东西罢了。他们反对,只是因为他们还无法理解。毕竟经历过军国主义、战争、核爆、战后重建的小津安二郎比他们走过更加曲折、更加坎坷的道路,而这些对于在当时二十多岁,心里满怀着愤怒和怀疑的新导演而言显然是无法理解他们这位前辈的心境的。而小津安二郎也一直履行着他作为一名长辈和老师的责任,维持着他一贯的绅士风度,没有对于他们的意见作任何回应,只是继续坚持自己的美学立场,拍摄自己的电影。同时尽力向那时仍然处在叛逆期的徒弟们传授一些拍摄电影的经验,虽然那时年轻的他们听不进去,小津安二郎也不会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立场和风格。很多时候,一个青年会对长辈说出的一些违背他/她意愿的观念本能地逆反,然而这种反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不理解。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有句名言:“不惋惜,不嘲笑,不憎恶,唯求理解。”而不求理解,立场先行,恰恰是全世界荷尔蒙过剩的青年人都有的通病。黑格尔说过,“人类唯一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他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而对于一个青年来说,他们唯一从长辈那里吸取的教训就是他们没有听从长辈的任何经验,似乎这就是青春所要经历的宿命。
2-14 法国导演戈达尔
在“新浪潮”过去五十年后,筱田正浩曾经在造访北京电影学院时向台下和他们成为“新浪潮”一代时一样大的年轻学生这样形容过他们那一代人的心境,“现代日本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年轻人不再相信国家。年轻人不用再忠实于国家,人是自由的。通过战败,我们思考的是国家还能再相信吗,国家的权力还值得尊重吗?这种愤怒,即使已经过去六十多年,我们心中仍然不能释怀”。或许也正是这种愤怒,让他们那一代人无法静下心来好好审视他们所处的环境,好好地思考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正是这些才让1960年代的日本陷入了一种更大的混乱。
或许也得益于当时日本电影公司的导演培养体制,让他们在30岁左右时能够拍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而30岁左右的他们,正处在青年和中年的交叉口。相较于那些老导演,他们对于青春有着更大的兴趣,同时他们也比青年人积累了更多的人生经验,这些人生经验让他们对于当时的青年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这让他们能够有足够的能力拍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电影,表达他们对于历史、民族、社会的困惑,无力、彷徨以及愤怒。
有一种看法认为这些电影是纯粹“政治”的,进而否定了他们在“艺术”上的贡献,这种看法似乎把“政治”和“艺术”截然分开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咬文嚼字的话,政治本身就是我们作为社会人的组织方式,而当政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中的人的时候,反映“人”,由“人”所创作的艺术作品是不可能对此毫无回应的。许多艺术史、电影史的佳作,也恰恰是因为对于处于典型环境中“人”的生动的刻画而获得了他在艺术阶梯中的地位。持有这种看法的批评家似乎仍然沉迷于“犬儒”式的艺术观,虽然这一时期“新浪潮电影”在创作中确实是主题先行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主题先行,才让他们作为青年导演的愤怒、彷徨和困惑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实际上,在他们之后,在现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里,“政治”和“艺术”似乎越来越难分开了。
这种困惑、迷茫和被撕裂的无力感也都被表现在了他们的电影里,这样的无力感,我们曾经在20世纪初的中国青年身上看到过;在1980年代的中国青年身上看到过;今天的我们也同样可以感同身受。当我们面对社会不公,当我们发现现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残酷时,我们会和六十年前的他们一样,在愤怒后感受到迷茫和无力。虽然处在不同的时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会发现,在面对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时,我们会和他们一样感受他们曾经感受过的情感。联系历史,过去我们的青年也曾经寄希望于外来的东西彻底改造掉我们旧有的、腐朽的传统,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惨痛的失败。我们和他们虽然处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然而青春的我们有着与他们一样的情感,或许这就是他们的作品为何能留在电影史中,因为他们所描绘的青年,不仅仅只是日本的青年,也是一个作为普通人,有着共同普世情感的青年。他们和我们一样满怀热血,想要改变这个世界的种种弊端。然而成长之一大痛苦就在于,我们都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西,并不是我们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而且还有许多,是根本就无法改变的。这或许是全世界青年成长的一大难题,因为我们或许都面临着小说家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抛出的关于成熟的难题,“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下去”[4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