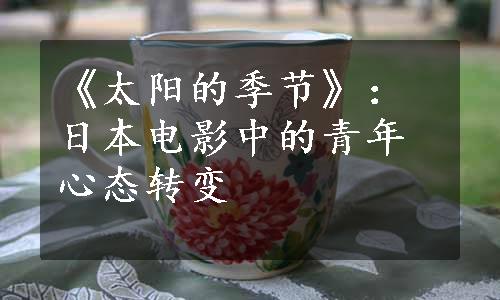
1955年,随着尼古拉斯·雷(Nicolas Ray)导演的《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以及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导演的《伊甸园之东》(East of Eden)和《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在全球的大热,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和马龙·白兰度(Malone Brando)也成为了全球青年人的偶像。这几部电影中的男性主人公,都具有超越常人的魅力。在《伊甸园之东》和《无因的反叛》里,詹姆斯·迪恩所饰演的都是叛逆的儿子。在《伊甸园之东》里,他的父亲是严厉的,甚至有些暴君色彩的人,作为儿子的詹姆斯·迪恩一直无法得到父辈的爱;而在《无因的反叛》里,父亲则是一个无聊、呆板的中产阶级绅士。而在这两部电影里,詹姆斯·迪恩都是一个富有活力,同时又有些好惹是生非的青年,尤其在《无因的反叛》里,身穿一身红色哈灵顿夹克的詹姆斯·迪恩,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吸引力,热衷在乡间公路上驾驶跑车飞驰。这部电影里的詹姆斯·迪恩几乎成为了那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文化图腾,几乎成为了战后第一位全球知名的明星。
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也迅速引起了日本人的追捧,伴随着派拉蒙(Paramount Pictures)等美国电影公司重新进军日本市场,日本人开始有机会在家门口与大洋彼岸观众几乎同时收看到好莱坞的电影。同时,这些新好莱坞电影也对这一时期的新日本电影影响很大。战前,日本电影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对于“影像为本”(Visual Superiority)这一条西方电影的创作铁律重视程度不够,在战后的这段时间,得益于这些美国电影的大量进口,许多日本导演们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好莱坞电影的剪辑和摄影技法,这些技法在1950—1960年代的日本电影风格形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4年,富家公子石原慎太郎写出了《太阳的季节》,作为石原慎太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次年就获得了芥川奖,同时日活公司也加紧跟进,花费四十万日元买断了拍摄权。次年,《太阳的季节》上映,成为了当年日本的票房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石原慎太郎在写作这部小说时承认,这部小说“带有自己的影子”。同时,在石原慎太郎之后的采访中,他也承认“那时的自己仍然对爱情、梦想等抱有幻想”。这部年少轻狂的作品充满着为传统的日本社会所不容的性爱和暴力场面的描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争议。
不过,我们可以从《太阳的季节》里读出“青年”在日本电影中的某种变化。在这部《太阳的季节》里,年轻人再也不是之前日本老家庭电影中孝顺的儿子或者像小津安二郎的“大船调”[21]电影一样,塑造的只是一味地顺从或者希望服侍父亲的女儿,他们都恪守道德和传统的伦理,形象温润。而出现在《太阳的季节》里的年轻人却浑身上下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富有吸引力。片中主角龙哉(长门裕之饰)在学校里是一名业余拳击手——富有男性阳刚气质的角色设定。同时片中也有大量与之前日本电影不同的青春肉体的展示(比如英子穿着低胸泳装在海边走来走去)。该片富有活力的情爱场面和影片虚无的道德观念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2-6 《无因的反叛》里穿着红色哈灵顿夹克的詹姆斯·迪恩成为了无数青少年模仿的对象。
2-7 影片《太阳的季节》中富有活力的情爱场景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实际上,即使是当时的芥川奖评委们,对这部作品也持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派认为石原不惧社会舆论,他坦诚地、鲜活地将青春的实际感受毫无保留地描写出来,这种态度值得肯定;而另外一派则对小说中随处可见的露骨的性描写颇有微词,认为“作者的时代敏锐感并未超越普通记者,作品缺乏应有的美感”。而日本战后著名的电影史学者岩崎昶则评价说,“它不是文学,而是一代青年的爆发”。[22]
影片上映后更是引起风波,由于当时的日活公司缺乏明星和资金,为了获取更高的票房,影片着重渲染了小说里的性爱和暴力场面,却忽视了小说中大量描写当时年轻人心理的片段,我们在电影里只能看到一群表面浪荡的年轻人,却根本无法深入到他们内心的忧虑当中去。
不过影片还是暗合了当时青年人的一种心境,如果我们套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电影导论》
(Preface to Film)中所提到的一个经典概念“情感结构”(Sturucture of Feelings)[23],我们会发现影片所反映的心理正像岩崎昶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政治上受到挫折以及其反面经济上的安定感所产生的反抗一切的心理”。而这种“太阳族心理”正是影片中反叛一切道德,蔑视一切权威的基础。
在影片《太阳的季节》大获成功以后,日活公司又趁热打铁,在同年发力拍摄了《疯狂的果实》(1956),影片导演中平康是刚刚从松竹公司跳槽的年轻助理导演,而《疯狂的果实》是他的长片处女作,同时,这部电影还捧红了有“日本的詹姆斯·迪恩”之称的石原慎太郎的弟弟——石原裕次郎。影片仅仅用了十七天就摄制完成,中平康曾说自己对于影片中拍摄的游艇运动毫无了解,所以使用多机位拍了很多镜头备用,不过他也承认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十分过瘾”。当然,这部典型的充斥着性和暴力的“太阳族电影”得到了一位当时还是《电影手册》影评人的特吕佛的高度赞扬,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剪辑”把所有的素材平等化处理[24],还用这部片子揶揄了法国的高等电影教育,他说:“法国高等电影学院常务院长索泰诺真应该把这部电影的拷贝买下来,每月给他们的学生都放上一次,教教他们的学生怎样成为一位有自己独立想法的导演,而不总是当助手的思维。”
《疯狂的果实》仍然由《太阳的季节》原小说的作者石原慎太郎编剧,影片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三角恋的故事,这个剧本有着石原慎太郎年轻时的影子。影片讲述了两兄弟——哥哥夏久与弟弟春次,为了争夺一个美少女天草惠梨的爱,进而反目成仇,最后弟弟在一个晚上驾驶快艇将哥哥和少女杀死的故事。这部电影取得了很高的票房,观众达到了四百七十万人次。在五十年之后《电影旬报》评选的20世纪百佳影片中排名第九十五位。
《疯狂的果实》似乎和之前的《太阳的季节》在主题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们甚至共享着相似的故事结构,一个美貌的、纯情的少女和两个阳刚的、叛逆的年轻男子产生了一段理不清的关系。在《太阳的季节》和《疯狂的果实》里,如伊索尔德在《新日本电影史:故事片的一个世纪》中所评价的那样,“在《太阳的季节》里,男性在叙事中都被演化为一个主动的、求爱的位置,而女性则是一个欲望的客体(Subjects),这个客体在这个主体眼中几乎毫无自主性和人格可言。而电影里所摄制的男主人公,都是高中生或大学生,通过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经济法则,表现一种特殊的男子气概”。[25]我们会发现,两部电影都有意地让主人公有一项运动爱好,在《太阳的季节》里,是拳击;而在《疯狂的果实》里,则是赛艇。这两项运动都有着从美国舶来的特征,带着某种特殊的“西方先进生活方式”的味道,片中的主人公都有优越的教育背景和家庭背景。同时在美国,拳击和赛艇也被认为是“属于男人的运动”,观众会自觉地把这些运动与“英俊”“富有”的“男性青年”联系起来,片中主人公的生活方式更加“西方化”,而不再是之前“大船调”的婚丧嫁娶的传统生活。这两部电影也都有大量海滨的场面,海滨和沙滩历来是好莱坞青春片中十分重要的元素。同时,海滨在影片本身的场景设计上也为年轻肉体的展现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场所。海滨的泳装、时髦的运动、优越的教育一起成为了这两部“太阳族电影”的特定元素,这些元素向我们描绘了消费主义在日本登陆的情景。“叛逆青年”的生活方式席卷了整个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突破了文化的壁垒入侵到了遥远的东方——日本。
2-8 中平康导演《疯狂的果实》(1956)
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曾经在他的《日本电影:电影风格与民族性格》(Japanese Cinema:Film style and National Character)一书中这样评价《疯狂的果实》,“虽然这部电影只是同时期一系列青少年犯罪电影中的一部,但是导演中平康制作了一部有着自己独特韵味的电影,即使其中有些小小的俗套”。同时他也指出,“这些电影中的人物就像乔治·斯蒂文斯导演的《郎心似铁》(一部在内容上对这类电影影响至深的作品——这类电影甚至有几乎相同的镜头:在海滨码头上的无线电)一样,主人公都是有些叛逆,同时残酷和愚蠢的年轻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活力和想象力去做任何事情。毕竟,他们还是青少年,还在慢慢迈向成年的途中”。[26](www.zuozong.com)
同年,还有市川昆的《处刑的房间》(1956)、中平康导演的另外一部作品《夏日骤雨》以及堀川弘通导演的《日蚀的夏天》。这几部电影的编剧都有石原慎太郎的参与,所谓的“太阳族电影”狭义上就仅指这五部电影。
市川昆导演的《处刑的房间》,讲述了一个早稻田大学的大学生——岛田胜三的反叛罪恶的生活。
这部作品一改之前“太阳族”流于表面、只注重商业的风格。它尝试着从多方面深入地剖析他的主人公——岛田胜三。岛田几乎就是当时代“太阳族”的翻版,他们蔑视一切,反对一切。在之前的“太阳族电影”里,导演们都主要描写青年人之间的性爱场面和暴力情节,恰恰忽视了对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家庭环境进行细致的分析。市川昆在他的这部作品里增添了关于家庭的副线,影片的开场是在一场盛大的、欢乐的游行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个全景镜头。前后两个镜头之间形成了极大的视觉反差,在当时保守僵化的日本电影圈里,这种组接方式显得十分离经叛道。在这个场景里,岛田的父亲——一个虚弱的中年男人,在去拜访一位冷漠的部门主管的路上胃病突然发作,作为一名推销员,他要带病推销公司的贷款业务。市川昆刻画的这位父亲,正是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期被畸形社会折磨的一群人中的一个,这个被病态社会折磨的虚弱的父亲,只能撑起一个病态的家庭,而在这样的家庭里,也只能成长出一个病态的少年。在之前的“太阳族电影”里,父亲都是“缺席”于影片叙事之内的,“父亲”的形象在那些电影里只是一个模糊的、扁平的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电影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无父电影”(Fatherless Film),而《处刑的房间》里的父亲形象,却是饱满的、有说服力的。
影片中另一个引起轰动性的段落就是男主角对外校女生显子的诱奸戏,这段戏在当时的社会中也引起了轰动,不过市川昆对这个场景的处理明显不同于之前的“太阳族电影”。之前的“太阳族电影”对待性爱的态度是游戏的、轻佻的,这些游戏式的性爱场景加到影片中明显是为了增加电影的票房。而市川昆所表现的性爱段落则更加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影片中被诱奸的女生显子,表面上有着明显的新时代女性的特征——她们对待性的态度更加开放,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说,显子仍然没有逃离出该时期日本电影中被物化的、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形象。
市川昆作为战后日本电影的“四骑士”之一,显然具有更为深厚的艺术修养和人文关怀。他的地位也决定了他在影片拍摄中具有比年轻导演更多的主动权,所以他能够在他的电影中对于“太阳族”作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同时更多地运用自己所钟情的表现主义风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助理导演,就是日后“新浪潮”的旗手导演增村保造,而大岛渚在之后的电影中也对市川昆这部作品中的诸多元素致敬,可以说,这部作品对后来发生的“新浪潮电影”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打着“太阳族”名号的电影还有许多,大名鼎鼎的木下惠介在这时也拍出了《太阳与玫瑰》(1956),在这些打着“太阳族”旗号的电影中,《幕末太阳传》(川岛雄三导演,1957)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部作品。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因为导演川岛雄三觉得江户时代的许多青年也有“太阳族”的特征,所以拍摄时戏仿古装“太阳族电影”,这部电影汇集了石原裕次郎和南田洋子(《太阳的季节》的女主角)这样的“太阳族明星”,而电影的最大亮点则是弗兰克·堺(Frankie Sakai)的滑稽表演。这部电影戏谑的形式给当时的日本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2-9 川岛雄三导演《幕末太阳传》(1957)
那么,这一时期的“太阳族电影”到底反映了怎样的青春呢?即使岩崎昶曾经在他的《日本电影史》中批评过,“‘太阳族’所表现的中心内容不过是性和暴力罢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电影都是以极端营利思想制作的坏作品”。多数青年们只是“借助这些影片,把他们对于大人们的伪善和保守、政治与文化的停滞和腐败,以及对反动路线所作的挑战,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发泄出来”。[27]但是,这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太阳族电影”会在日本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为既然“多数向上的青年都是批判电影中那些‘太阳族’青年的”,他们又何以会一批又一批地走进电影院,给这些他们所“批判”的青年的电影贡献票房呢?
或许我们还要回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原因。首先,我们都知道战后日本经济蓬勃发展,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民文化中保守的、属于传统的宗法制的规则仍然没有被破除。愈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机会愈多,社会竞争也开始愈发激烈。青年们选择到美国电影、性和暴力里逃避现实。1950年,日本发生了一起轰动社会的案件,一个青年偷窃大学基金,在被逮捕时才发现他偷窃的大学基金,已经被他和他18岁的女友全部花光了,而他只是学着他们痴迷的美国黑帮片中人物的口吻,用蹩脚的英语感叹“oh, mistake”。[28]他们在电影里逃避现实的同时,也渴望用电影里的方式把他们想要的变为现实。年轻人渴望像电影里那样轰轰烈烈的享乐,不用忍受平庸而又重复的一生。
其次,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席卷了整个战后的美国盟友们,全球化的趋势初显,同样地,与资本主义相生相辅的消费主义、好莱坞电影也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同时,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就对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有着近乎狂热的执著追求。而那些消费主义所驯化下的理想的、“个性的”“玩世不恭的”“叛逆”的形象也随着好莱坞电影销往了全球,这些形象成为了那一代青年的精神图腾。
再次,日本的政治环境也较战时和战前有所改观,没有了战时日本政府严格的思想管控,再加上驻日盟军司令部的接管,日本青年可以相对比较自由地表达自我。同时日本国内政坛两大保守势力合并,形成了自民党。日本的政权从此开始被长期控制在自民党手中,其他社会力量很难得到执政机会。从这个层面上讲,日本青年的政治抱负难以通过正常的在野党选举或者普通学生游行来实现,这种苦闷的心情难以排解,只能在电影里寻回一丝慰藉。
最后,此时的日本电影产业蓬勃发展,大量新导演进入业界,这些年轻的力量大大推动了日本电影风格的革新,促进日本电影产生了“新浪潮”这样在东亚独具风格的电影流派。
在马克斯·泰西埃的《日本电影导论》中曾经提到大岛渚在拍摄《太阳的墓场》(1960)时,曾试图证明“太阳族”这个流派也存在过,尽管他认为这不是事实。“太阳族电影”虽然与“新浪潮电影”一样有着叛逆的、蔑视权威的精神,甚至在很多元素上,“新浪潮电影”对“太阳族电影”也有所借鉴。不过“太阳族”和之后要提到的“新浪潮”最为根本的不同是,“太阳族电影”不能算是一个自觉的艺术运动和流派,“太阳族电影”的大部分创作者们只是按照市场的喜好在他们的电影里堆砌“太阳族”所要求的元素——性、暴力、无所事事的俊美青年,他们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创作流派,没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他们对于石原慎太郎小说的阐释和表达也是根据导演自己的喜好和片长以及市场的要求进行的。所以,“太阳族电影”或许可以算作一种潮流下产生的一批热门且有着相同元素的电影,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过是“太阳族”的“IP”电影。与后文要提到的“新浪潮电影”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