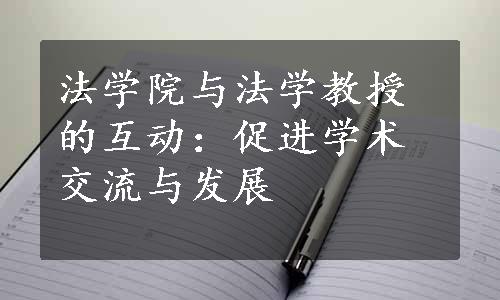
如果说律师、法官等法律实务界人士是现代法治国的建构者的话,那么,法学教授是法治国的最初奠基者。这种奠基作用肇始于法学院对法科学生的传授之功。在法学院中,无论再华美的建筑,再先进的教育设施,皆是法学院的皮相而已,而法学教授则是法学院的真正灵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指出:“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其中的旨趣就在于此。法学教授对法学院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如下:其一,法学教授是法学院真正影响力之所在。一所法学院能够在法学教育领域立足,吸引法科学生纷纷报考的最主要动力之一就在于法学教授。法学教授成为法学院的著名徽章,这甚至超越了地理、经济、政治等因素。可以说,法学院真正是围绕法学教授而建。并不是法学院决定了法学教授,而是法学教授决定及造就了法学院。在西方社会,11世纪末大学法学专业最初创设时,著名的法学教授往往引得广大法律学子踊跃来投,当时甚至可以靠某个著名法学教授的一己之力,支撑起整个法学院的运行。其实,在现代社会亦有如此之现实及趋向。譬如,美国法学院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著名教授的竞争。著名教授的多少在决定法学院的排序中占有很大分量。纽约大学法学院近十年来为了提高自己的排序名次,不惜重金争聘全国著名的法学教授,使其从排名二流的法学院跃升成为一流并且排名靠前的法学院。法学院排名靠前意味着有充足的优秀学生报考和源源不断的高额学费收入。[26]虽然由院长或者其他管理人员具体负责法学院的行政运作,然而,其在实质上只是处于辅助者的角色,并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利用行政性权力对法学教授形成压制性力量。虽然,法学院行政权力与法学教授的学术性权力具有一定的内部紧张关系,但这也只是法治尚未完善之国家或者法学院之乱象而已。在法治进步国家,教授和学生是法学院的主角,行政人员就是临时聘用的服务人员,“处长一走廊、科长一操场”的现象在美国难以想象,只有教师才可能获得终身职位,就连握有重权的法学院院长也面临排名下滑就被解聘的风险。[27]其二,法学教授决定了法学院的运作程序及制度。特别是对于推崇教授治校的西方大学法学院而言,法学教授决定了法学院的运作制度及方向。如果法学教授的教育或者研究是职业型的或者实用型的,法学院的运作制度、程序可能同样具有这种特点;如果法学教授的教育或者研究是务虚型的,法学院的运作程序及制度也应当与此相匹配。因此,学校制度的形成取决于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教师,还包括学者和研究者。正如美国人对它的理解:“大学要具有超前的认识论——要能够以当前的理解力判断知识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创造的,它又如何被用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关于知识的理念对一种新型法学院的形成和运作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28]
但是,现代法学院中法学教授群体亦有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向。其一,基于法律学术性权力的支撑,以及法律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支持,法学教授往往不容挑战,不思进取。由于法学教授基本上是长期聘任制,特别是在狭小的法学学科领域内,少数法学教授的学术地位无人撼动,所以往往形成唯我独尊的地位及傲慢态度,这无疑对法律教育及研究是不利的。当然,法学教授这种在某些法学特定领域中的霸主地位不仅体现在学术领域或者其与法科学生的关系上,即使是法学院的管理层对法学教授也往往有尾大不掉之感。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称,美国法学院院长像动物园中的猛兽饲养员,而且猛兽的笼门都是开着的。换句话说,法学院的教授之猛猛于虎。[29]这主要是因为法学教授基于其法律知识性权力形成的学术霸主地位,不容不同意见之挑战,使得其从权力的批评者,变为真正的权力垄断者。“法学教育的发展以及政治环境的逐步宽容,使得原来好像大一统的法律界也逐渐发生分化,出现了司法界、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区别。法学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一方面高唱法律共同体的宣言,另一方面则试图在这个共同体中争取自身的正统性、话语权甚至利益,而其依仗的主要就是法官并不擅长的‘学术话语’和法学人垄断性占有的法学文凭发放权。”[30]对于同一领域或者背景的法律学术圈,法学教授因为都是学术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且他们都是教导法科学生如何处理复杂局势的佼佼者,所以能够彼此融洽、相安无事,共同分享法律学术共同体带来的垄断利益。然而,对于外来权力竞争,不论是学术方面的还是行政方面的,法学教授则往往不容他人置喙,结果易于形成不受制约之权力,这本身即会成为法学教育及学术研究的桎梏。同时,在法学教授与法科学生的关系中,法学教授也往往有领袖或者君主之姿态,这也是没有领悟到教育真谛之表现,或者是学术性权力过分膨胀造成的不恰当后果。对此,韦伯就曾指出:“如果听任所有的学院老师在课堂上扮演领袖的角色,情况将更为严重。因为大多数以领袖自居的人,往往是最不具备这种角色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不管他们是不是领袖,他们的位置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就此做出自我证明的机会。”[31]其二,法学教授一般过于清高,因此不能把握社会有机体发展中先进的趋势、力量及情势。法学教授往往有坐而论道之缺憾。对于一部分法学教授而言,其往往喜欢清谈,而不注重法学教育之实用性特征,结果往往成为纸上谈兵者,或者书斋里的法学家,从而有食古不化之弊端。“显然,部分法学教授将自己封闭在‘知识的象牙塔’中了。在大学里,这些教授可以熟练地教授法律学子自己所熟悉的法律知识,但至于‘政府’是否连ABC都违反,却非他们所问。换而言之,法学教授也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工匠化’,可以对‘法律实践的关心’与‘法律知识的传授’一刀划开。”[32]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亦有如此之趋向。在美国,法律教授们的另一种普遍的态度对法学院的整个结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墨里·施瓦茨指出:“除了少数人以外,法律教授都试图进行法律实践,结果发现他们并不喜欢律师或者法官的工作。因此,你无法指望他们的教学会以法律实践为目标。”[33](www.zuozong.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