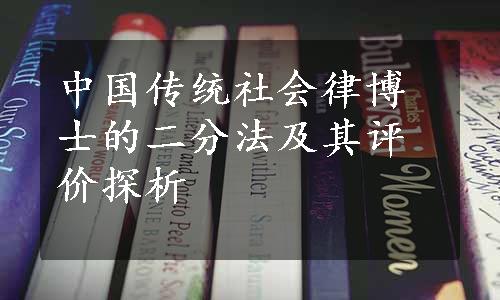
在相对缺乏法律内涵之中国传统社会中,律博士无疑属于重要的法律人物。然而,对律博士的评价却并不是单面的,其具有较强的两面性,对其评价既具有正面的部分,也具有负面的部分。在正面意义上,这包括:其一,律博士是律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律学是中国传统社会重要的法律成果之一,而律博士在推动律学研究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帝制中国的立法工作。“律学在帝制中国的前半期受到相当重视而颇有力量,成为产生出唐律那样优秀的刑法典的原动力。”[64]应当说,律学的发展是与律博士的作用密切相关的。律博士是律学的专职教育者。律博士在律学教学中,为其门生传授律学知识后,由于这些学生本身可能就是以后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官员,所以其必然会推动律学的传播及发展。同时,这也会增强律学与司法实践的结合,使得律学从学堂、书斋走向社会,这亦为律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方面的生命力。其二,律博士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律博士对其门生的法律传授,其法律知识和思想会通过后者具化于司法实践,从而保证了现实社会中的法律纠纷解决及法律秩序维护。同时,律博士有时还负有民间法律宣传之职责,这其实也是维护、建构帝制中国法律秩序的路径之一。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律博士虽然并不一定会亲身实践法律,然而其却是间接的法律秩序维护者,这也是中国诸多王朝设立律博士的内在因由之一。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发达的法律教育体系中,律博士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正式制度性教育者,是与当时帝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文明相适应的,而且在我国以法学家(律学家)为师、以吏为师、以律博士为师以及以生员为师的四元法律教育体制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其三,律博士对中华法系的建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正是由于律博士的法律研究及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中国法律体系的成熟。特别在唐朝就是如此。当时,中华法系成为诸多国家纷纷效仿的法律建设模板。“当唐律以其规范内容的完备和立法技术的精湛吸引周边诸国‘遣唐使’竞相研习时,律学教育对于传播中国法律文化、构建中华法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65]
然而,律博士制度的缺憾也是存在的,这主要包括:其一,律博士对律学的研究并不包含权利意识及正义理念,其对于封建义务或者秩序的追求远胜过对普民权利的关注,从而使得律博士成为君主意志的传声筒,而不能反映普民的权利诉求。可以说,律博士对律学的教育研究缺乏理性及独立思考的精神,从而限制了学术自由的发展。这是因为,律博士属于官方人士,具有官位及品级,专制国家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律博士进行控制,务必使其法律活动符合国家的利益,而不能脱离专制主义的轨道。易言之,律博士对律学的教育及研究不能超越帝制国家的主流思想,不得违背传统礼教的基本规范,特别是其应当符合君主的利益,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其二,帝制中国的统治者对律博士教育地位重视不足,使得其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虽然律博士属于官方的教育者,但是,其地位却并不高。譬如,在唐朝,律博士品级属于从八品下,虽然稍微高于书学、算学博士,但是,却低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博士。实际上,在元朝以后律博士就基本被废止。这也与当时统治者意识到法律并不是维护其专制治理方式的最有效工具,有时反而会成为其独裁的障碍有关。这也导致律博士制度逐渐式微,法律教育也因而走向低谷。到了清代,“正规学校和科举考试都不重视法学,当时直接从事法制工作的官吏、书役等人所需的法律知识,大致都是由自修自练而得。这种方法因人而异,不成制度,因而成果也难预测,所以中下层官司都要依赖幕友”。[66]其三,律博士的法律教育虽然能够宣传法律,达到法令应用于实践的目的,然而,这种教育只是一种少数人的教育。在律博士的法律教育中,其教学的主要对象是低等级官员及其子弟,虽然他们并不是高官显贵,但是,其毕竟与普通百姓有差别。这种根据等级身份而设的律学教育制度,使得受教育权被掌控在少数官僚手中,而普通百姓则不能享受到法律教育的权利,这无疑就是赤裸裸的法律教育权的不平等。其四,中国传统社会律博士的法律教育“礼法不分”现象严重。按照常理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教育主要应当重视法家的精神,而法家的最大特点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本身倡扬的是无论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各色人等不应在法律面前有等级之分,应平等接受法律对待。而自汉代董仲舒“引经决狱”起,律学成为根据儒家之礼诠释后的法律。儒家强调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有分寸、等差,这与法家的核心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礼”是中国古代的法权形式,“法”也是中国古代的法权形式,然而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因为‘礼’是讲上下尊贱之别的,是不能在所谓一个标准之下来‘齐’的,然而‘法’却不然,‘法’是要讲一个标准的,所谓‘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之于一’。所以,‘礼’在于别,而‘法’在于‘齐’。中国古代社会的刑与礼是对立的。”[67]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礼是对法排斥的。同时,儒家先礼后法的思想,也使得法律的位阶要低于礼的要求,这使得法律本质含义被礼之教义所修改,导致律博士教授的律学内容礼法不分,情、理、法交融混杂,这本身就成为法治发展的一大桎梏。
【注释】
[1]胡加祥:“世界一流大学法学院比较与启示”,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8期。
[2][美]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刘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
[3]孙季萍:“古代希腊、罗马、中国法学方法的比较分析”,载《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4][美]约翰·麦·赞恩:《法律的故事》,刘昕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5]司莉:《律师职业属性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6]高燕、郝梅梅:“罗马法高度发达之原因解析”,载《淮海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7][美]弗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102页。
[8][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卷),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9]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载强世功:《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12页。
[10]Davies J.,Florence and Its University during the Early Renaissance,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1998:27,转引自孙益:“大学与近代西方职业阶层的兴起——以医学和法律为视角”,载《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6期。
[11][英]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奚瑞森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1~32页。
[12][美]孟罗·斯密:《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13][英]梅特兰等:《欧陆法律史概览》,屈文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14][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15]朱景文:《比较法导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6]何勤华:《法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7]参见[英]梅特兰等:《欧陆法律史概览》,屈文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9~80页。
[18][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19][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下),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2~903页。
[20][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1卷),贺卫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21][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22][英]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的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刘四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译者前言第6页。
[23][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下),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8页。
[24][比]R.C.范·卡内冈:《英国普通法的诞生》(第2版),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25]大陆法在英国的大学中被作为人文学科传授,牛津和剑桥从12世纪开始就设有大陆法的讲席。See J.Baker,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Legal History,27(2nd ed.1979),转引自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26]朱景文:《比较法导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27]See Richard L.Abel,The Leg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and Wales,1988,pp.263~265,转引自周汉华:“法律教育的双重性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28][美]罗伯特·斯蒂文斯:《法学院: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法学教育》,阎亚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9][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30][美]罗伯特·斯蒂文斯:《法学院: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法学教育》,阎亚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31]此处法学家包括法学教授,但是并不限于法学教授,也可以包括其他具有精深法律思想的专家。
[32][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正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33][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www.zuozong.com)
[34][英]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的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刘四新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译者前言第6页。
[35][比]R.C.范·卡内冈:《法官、立法者与法学教授——欧洲法律史篇》,薛张敏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36][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正东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
[37]当然,法国法学教授的教学也有偏重理论的特点,但是,相比较英国而言,其具有更多的实用成分。参见[日]大木雅夫:《比较法》(修订译本),范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38]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虽然从宋代就出现律学教授的记载,元代各路州府儒学及明清两代的府学也都设教授一职,但是,教授承担律学教育之事在我国传统社会史学资料中很少有记载,更多的是律博士教育制度的记载,因此,实际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律博士承担了大学或者法学院中教授的法律教育职责。
[39]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页。
[40][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127页。
[4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页。
[42]《韩非子·五蠹》。
[4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38页。
[44]郑显文:“走出中国古代法学教育的误区”,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45](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132页。
[4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29页。
[47](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2页。
[48]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49](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设律博士议》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58~2059页。
[50](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国子监》卷二十一,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版,第561~562页。
[51]《宋大诏令集·卷二百·刑法上之改窃盗贼计钱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转引自魏磊:“宋代法律教育研究”,河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52](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设律博士议》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60页。
[53]郑显文:“走出中国古代法学教育的误区”,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54]魏淑君:“中国古代律学教育探析”,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11期。
[55]胡旭晟:“清代法律教育之评估与当今法学教育之改进”,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56]转引自胡旭晟:“清代法律教育之评估与当今法学教育之改进”,载《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2期。
[57]何敏:“传统注释律学发展成因探析”,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
[58]杜文忠:“‘王官学’与中国古代法学样式及法学教育”,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59]胡旭晟、罗昶:“试论中国律学传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60]何敏:“传统注释律学发展成因探析”,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
[6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73页。
[6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载《光明日报》2002年8月20日。
[63]郑显文:“走出中国古代法学教育的误区”,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64][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65]魏淑君:“中国古代律学教育探析”,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11期。
[66]转引自张中秋:“论传统中国的律学——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67]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古代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8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