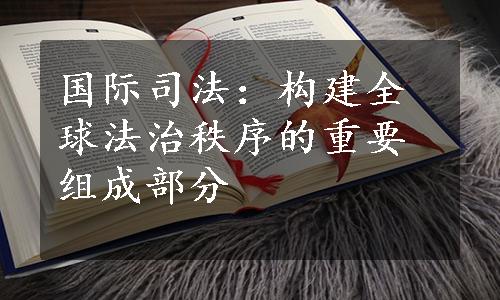
这里所说的“国际司法”,也可以称之为跨国司法,即拥有国际裁判权的裁判者(大都数情况下为“盟主”),根据一定的裁判原则、规则及惯例,对发生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诸侯国(周王室在计算单位上相当于一个诸侯国)之间的纠纷和诉讼进行裁判的司法形态。前面在论述司法权的时候提到过盟主司法权,如果从司法形态的角度看,盟主司法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国际司法。民国以来有些学者将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称为“国际法”关系,将春秋时期的争端(或纠纷)认为是国际争端(或纠纷),这是将中国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关系与现代西方国际法中国与国之间关系比附的结果。[66]本书将以盟主司法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司法形态称之为“国际司法”,只是出于行文的便利而借用“国际司法”这一概念,并不是说其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司法。关于春秋时期的国际司法问题,主要表现形式为“盟主”司法,其中大部分为晋国和楚国主导下的解决诸侯国之间的纠纷案例,由于本书在讨论盟主司法权时讨论已较为详细,具体的案例兹不重复。
可以说,春秋时期的纠纷和诉讼案例,无论是行政纠纷、刑事纠纷还是田土纠纷,表现形态都体现出其“国际性”,而对纠纷和诉讼进行裁判的,大多为盟主国,如晋国、楚国。但这样说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时候,特别是涉及到朝聘礼仪方面的纠纷时,受朝聘国也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裁决。据《隐公十一年》载:
春,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后之。”公使羽父请于薛侯曰:“君为滕君辱在寡人,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君若辱贶寡人,则愿以滕君为请。”薛侯许之,乃长滕侯。
滕国和薛国在同一天朝聘鲁国,因此产生了礼仪上的纠纷。“争长”,即争聘礼中行礼的先后次序。按照周礼,在朝聘活动中,行礼的先后次序体现了浓厚的亲疏、贵贱等级色彩,故滕国和薛国皆争之。最后是由受朝聘国鲁国依据“宗盟”的原则(在本例中主要体现为同姓和异姓之别)解决的。(www.zuozong.com)
如果说藤、薛皆小国,似乎不足以说明受朝聘国有权裁决此类纠纷,下面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大国来聘,受朝聘之国亦有权裁决产生的纠纷。晋国、卫国同时到鲁国聘问,也同样产生了上面类似的纠纷。据《成公三年》载:
冬,十一月,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臧孙许)曰:“中行伯(荀庚)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孙良夫)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丙午,盟晋;丁未,盟卫,礼也。
晋国大夫荀庚(中行伯)与卫国大夫孙良夫同时到鲁国聘问,关于应该先接待哪国的问题,使得鲁成公犯了难。在本例中,涉及到晋国、卫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与两国使者在本国中的地位的问题。从晋国与卫国在当时诸侯国的地位而言,晋国为诸侯盟主,自然属于大国,卫国显然不能与之相比;但从两人在本国的地位来说,卫国使者孙良夫在卫国为上卿(位列第一),而晋国使者荀庚则只是下卿(位列第三),[67]应该以诸侯国的地位还是使者的地位作为标准呢?鲁国大夫臧宣叔(臧孙许)首先根据先例(“古之制”)原则,对晋国与卫国卿大夫的地位进行了换算,即小国的上卿等同于大国的下卿,即差两个级别;其次,确定卫国与晋国相比,不能算次国,而只能算小国,因此,孙林夫与荀庚在地位上属于平级;最后,在使者地位相当的情况下,晋国为盟主,自然要高于卫国。所以,裁决的结果是先接待晋国,后接待卫国。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的“国际”聘问中,是有着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的。除了上例滕、薛聘鲁提到的“宗盟”原则外,还要考虑到诸侯国的地位、使者的地位等因素,但决定聘问礼先后次序的仍是受聘国。在本例中,因为晋国、卫国皆为姬姓,即周之“宗盟”,故“宗盟原则”失去裁决的标准,鲁国是按照两国的地位进行裁决的。正因为鲁国遵循了当时通行的惯例,晋国、卫国对于最后的裁决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