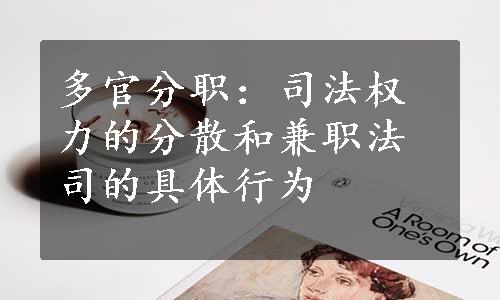
所谓“多官分职司法”,是指司法职权不是由单一的部门掌握,而是分散在多个职能部门,按照所管辖的事务承担相应的司法职能。具体到春秋时期,就是除了司寇、士、理等“专职法司”外,还有若干职能部门也有司法职能,这些职能部门至少有司徒、司马、司空、尉氏等。关于司寇、士、理等“专职法司”,本书将在下一章进行专门论述,此处只就司徒、司马、司空、尉氏等“兼职法司”的具体司法行为进行简要地勾勒。
(一)司徒
司徒为西周春秋时期的要职,在西周时,司徒与司马、司空经常并称,为卿事寮之下第二层级的大夫,[27]春秋时期为六卿之一,《左传》中多有记载,在鲁、晋、郑、宋等国地位相当于执政卿(或执政卿之一)。如鲁国,执政卿通常为被称为“三桓”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而季孙氏在春秋后期世为正卿,其官职即为司徒。昭公四年,鲁国执政卿之一的叔孙豹被其庶子竖牛饿死,鲁昭公赐其车,命其家宰杜洩葬之(当时称为“路葬”)。季孙宿的家宰南遗劝其阻止这件事,理由是:“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杜洩却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认为国君赐给叔孙豹路葬的礼遇,是对其功勋的认可,君命不可废,但同时也承认季孙宿(季武子)的正卿地位要高于叔孙豹:“吾子(指季孙宿)为司徒,实书名;夫子(叔孙豹)为司马,与工正书服;孟孙为司空,以书勋。”(《昭公四年》)因此,结合南遗与杜洩的说法,则知季孙、叔孙、孟孙虽皆为鲁国执政卿,但以季孙为首(冢卿),其职位为司徒,序位在叔孙担任的司马(介卿)、孟孙担任的司空之上。[28]晋国无司徒之官名,是因为避讳而改为中军,而中军帅为晋国实际上的执政卿。宋国也有大司徒(《昭公二十二年》),为执政卿之一。这样看来,似乎司徒并无掌握具体司法权。其实不然,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在某种情况下,司马其实也具有司法权,即上文提到的中义司法权。据《襄公二十一》载:
栾盈过于周,周西鄙掠之。辞于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于王之守臣,将逃罪。罪重于郊甸,无所伏窜,敢布其死:昔陪臣书能输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黡不能保任其父之劳。大君若不弃书之力,亡臣犹有所逃。若弃书之力,而思黡之罪,臣戮余也,将归死于尉氏,不敢还矣。敢布四体,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使候出诸轘辕。
栾盈为晋国前执政栾书的孙子、大夫栾黡的儿子,当时执政范宣子的外孙,但范宣子因害怕栾盈“多士”危及范氏的执政地位,且栾氏与范氏有旧怨,故范宣子将其逐出晋国,杀栾氏一党多人(晋国贤大夫叔向亦受牵连),栾盈出奔楚,经过周王室西郊时,遭到周人抢劫财物,栾盈向周王诉苦,并力数栾氏对王室昔年之功勋,故周王命司徒禁止掠夺,并归还抢夺的财物。可见,司徒具有一定的司法职能。但此项职能本当为司寇所掌,为何由司徒行使之?主要原因是与司徒的具体管辖职能有关。杜注:“乡遂都鄙,皆司徒所掌,不使司寇而使司徒者,谓及行刑,唯禁掠耳。”[29]孔颖达进一步解释到:“周官司寇掌诘奸慝、刑暴乱。当使司寇而云司徒者,以司徒掌会万民之卒伍,以起徒役,以比追胥,以此追寇盗是其所掌,获得罪人乃使司寇刑之耳。”[30]
上面的解释是从管辖权的角度出发的,大体可从。但需要补充的是,司徒的职能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在其管辖业务范围内有司法职能是理所当然的。司徒通常负责民事事务,故郑打败陈国以后,子产做的事是:“子美(子产)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襄公二十五年》)司徒又掌管赋役事务,陈国后期的司徒就是这样:“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公女;有余,以为己大器。国人逐之,故出。”(《哀公十一年》)有时掌徒役,如宋国发生大火,“使华臣具正徒”。(《襄公九年》)华臣的官制就是司徒。甚至有军事权,如王子朝与周敬王争位之时,“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昭公二十二年》)上述事例说明,春秋时期司徒可能分为多种,且职能具有多样性,但是,其职能之间还是有关联的。因为徒役本为居住在乡遂都鄙的庶人组成,平时务农,战时打仗,这正是兵农合一的体现,故司徒能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司法权。[31]
司徒的司法权在《周礼》中得到了系统化的论述。《周礼》“六官”之二即为地官司徒,其主要的职能为“掌邦教”,即管理土地、人民之数和教化百姓。但其中多有关乎通过法律和司法解决解决者,如大司徒十二教中,其二为“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其三为“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其四为“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其七为“以刑教中,则民不暴”。荒政十二项措施中,其三为“缓刑”,其十二为“除盗贼”。大司徒教化的重要手段为“乡八刑”,即对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乱民八种行为施加刑罚。如有因百姓因不服从教化而产生纠纷的,则与当地官吏共同审判,如果属于刑事方面的问题,则移交到士审理:“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小司徒的职能中,有“凡用众庶,则掌其政教与其戒禁,听其辞讼,施其刑罚,诛其犯命者”。即审理征发“众庶”的诉讼纠纷,惩罚其违犯命令之人。对于人口、土地方面的纠纷,还有具体的审理要求:“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每年正月,大司徒、小司徒还要悬“教象之法”于象魏,帅属下及使万民观教象。司法系统下辖职官多有司法职能者,乡师、调人、媒氏、司市、遂师、遂大夫等皆是,兹不具列。[32]《周礼》中关于司徒司法权的论述,当然要较之《左传》的记载详细、完备,两者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的讨论,但如果我们说《周礼》的系统性记载是建立在包括春秋时期在内的司法实践基础上体系化和理论化的结果,应当有较大的可能性。
(二)司马
司马作为官职,很早就出现在文献之中。《尚书·牧誓》云:“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可见在西周初期,司马与司徒、司空一样,地位非常之高。在西周初期的官制中,司马居“三事”之一,为朝廷要职,其主要职能就是负责军事。对于这一点,学者没有什么分歧。《说文》云:“马,武也。”郑《目录》云:“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人应劭曰:“司马,主武也,诸武官亦以为号。”[33]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有各种司马职官,如鲁、卫、晋、郑、宋、楚、陈、蔡等。有些诸侯国的大司马地位相当于执政者或执政者之一,如上文提到的鲁国的情况[34],除此以外,宋国[35]、郑国[36]、楚国[37]等国的司马地位也很高。各国司马的职能多以军事为主,但也有与军事有关的其他职能。比如,楚国司马的情况就是如此。据《襄公二十五年》载:
楚蔿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蔿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这段史料大意是:楚康王时令尹屈建(子木)使司马蒍掩整顿全国军赋,清点武器之数,蒍掩于是把全国的土地进行重新丈量,按土质、地形不同分为九等,定出全国可出战车、战马及各种兵器之数,然后上报给令尹屈建。再来看郑国司马的情况。昭公十八年,郑国大火,执政子产调配各种人员救火,其中有“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昭公十八年》)此处的“司马”与作为执政卿的司马显然有别。甚至,有些诸侯国卿大夫亦设有“家司马”一职,如鲁国有“叔孙氏之司马”。(《昭公二十年》)可见,司马作为职官体系在春秋时期已经比较复杂,要根据具体语境考察其职能。
司马的司法权主要体现为军事司法权。楚国设有左司马和右司马,具体负责军事司法职能。据《文公十年》载,楚穆王与宋昭公、郑穆公田猎,
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命夙驾载燧。宋公违命,无畏抶其仆以徇。
宋昭公在田猎中违反军纪,左司马文之无畏将其御者笞打以示众(“抶其仆以徇”)。楚平王听信费无忌的谗言,认为太子建将谋反,审问太子傅伍奢,伍奢劝平王不要听信谗言,结果:“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太子。”虽然奋扬并未执行命令,而是将太子建放跑,但亦可说明司马具有司法权。(《昭公二十年》)(www.zuozong.com)
在晋国,司马的地位没有鲁、宋、郑、楚等国这么高,因其执政卿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与军事权有关(如正卿即称为“中军帅”),故齐败于鞌之战后,晋国使齐国归还鲁国汶阳之地,鲁成公“赐(晋)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中军、上军、下军帅为三命之服,而司马只有一命之服(《成公二年》)。上例中之司马指韩厥,韩厥之前已任司马之职(《宣公十二年》),后来升为晋国执政中军帅,说明司马亦为晋国要职。晋国的司马一职,具体行使军事司法职能,“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僖公二十八年》)晋国司马的军事司法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即使是军中主帅都不能干预。齐晋鞌之战前夕,韩厥为司马,斩杀违反军令之人,中军帅郤克也无可奈何。(《成公二年》)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魏绛当时为晋国中军司马。春秋后期,晋国司马的地位更高,有代表晋国分配诸侯军事任务的权力。《昭公十三年》载:“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羊舌鲋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羊舌鲋即叔鱼,为叔向之族弟,曾代行士景伯审理邢侯与雍子的争田案。羊舌鲋作为司马,能代表晋国“合诸侯”,可见司马地位之重要。
《周礼》“六官”之四为夏官司马,其主要职能为“掌邦政”,即军事方面的各项事务,其中多有通过司法解决者。如大司马以“九伐之法”规范邦国,其中就有“放弑其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的规定。田猎大阅之时,如有不从军令者,则“斩之”。正月,大司马要悬“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其属官亦有司法职能者,如马质掌“马讼”,如侯人掌“道治与其禁令”,司士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等。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司马的职能源于《周礼》的记载,[38]其实刚好把二者的关系颠倒了:实际上,《周礼》关于司马职能的记载,恰好是春秋时期司马职能具体实践系统化的概括。
(三)司空
司空与司徒、司马同为西周春秋时期要职之一,已见上面对司徒和司马的分析。下面,略对文献中记载的司空进行分析。据《定公四年》载:“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聃季为司空,与周公、康叔并列,其地位要高于管叔、蔡叔等其他五个兄弟,可见司空职位在西周应该是较高的。但是,传统向来又有司空兼任司寇的说法,且认为司空之职位要高于司寇。[39]比如,郭沫若根据西周中晚期的金文《杨簋》的记载,认为:“以司空兼任司寇,足证司寇之职本不重要,古有三事大夫,仅司徒、司马、司空而不及司寇也。”[40]从文献记载的互相抵牾来看,说明司空与司寇的关系比较复杂,可能是周王室与各国的情况不太一样的缘故。《左传》记载的司空,其职能以工程管理为主。据《昭公三十二年》载:
冬十一月……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
上述史事发生于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说的是晋国平定周王室王子朝之乱后,周敬王畏惧王子朝在王城之余党,故迁都成周,然成周偏小,故请求晋国会诸侯营建之事。从上可知,筑城之设计规划,包括分派诸侯筑城人数、粮食等事务皆由士弥牟(士景伯)具体负责,制定好具体方案后交给周王室卿士刘子(刘文公),晋国大夫韩简子(韩不信)负责监督工程。按当时制度,负责工程建造之事的应为司空之职。士弥牟又称士景伯、士伯、司马弥牟,之前担任晋国专职司法官(“士”或“理”),审理邢侯与雍子争田案子(《昭公十四年》);处理过邾国诉鲁国叔孙婼的案子(《昭公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四年》),魏舒(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他以司马的身份任邬大夫(《昭公二十八年》)。此时盖又任司空,故筑城之规划设计由其制定。而司空在解决工程赋役方面的纠纷时,就有司法裁判权。次年,在营建成周时,发生了宋国不愿意承担赋役之事。据《定公元年》载: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为无道,绝我小国于周,以我适楚,故我常从宋。晋文公为践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复旧职。’若从践土,若从宋,亦唯命。”仲幾曰:“践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何故以役诸侯?”仲幾曰:“三代各异物,薛焉得有旧?为宋役,亦其职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仲幾曰:“纵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诸乎?”士伯怒,谓韩简子曰:“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且己无辞,而抑我以神,诬我也。‘启宠纳侮’,其此之谓矣。必以仲幾为戮。”乃执仲幾以归。三月,归诸京师。
在本案中,宋国因想薛国等附属国代替其承担筑城的义务,但薛国提出异议,因而与薛国产生纠纷。最后是身为盟主的晋国进行裁决,具体是由负责工程分配的士景伯进行裁决的。可见司空之职,具有一定的司法权。
(四)尉氏
根据《左传》的记载,周王室有尉氏,郑国亦有尉氏,而晋国则有军尉。前引《襄公二十一年》载栾盈经过周王室西郊,遭掠夺财物,栾盈向王室的使者陈辞时说到其父有罪,故其有罪,将“归死于尉氏”。然则,尉氏的具体职能何在?杜注:“讨奸之官也”。《会笺》云:“《周礼》司寇之属官无尉氏之官,盖周室既衰,官名改易,于时有此官耳。晋之军尉,亦纠察之官,悼公命羊舌赤杀魏绛,以其为军尉也。籍偃曰:‘偃以斧钺从于张孟。’亦上军尉也。郑之狱官,亦曰尉氏。汉以廷尉主刑名,盖因于此。”[41]竹添光鸿认为,尉氏为春秋时期出现,其职能相当于晋国之军尉、郑国之尉氏,且为汉代廷尉之渊源。春秋时期的尉氏是否就为后世廷尉之前身,尚需其他史料印证,仅据此推测恐有推测过度之嫌,因汉代之廷尉直接源于秦代,应无疑义,而周、晋、郑皆为姬姓之国,而秦制与周制多有异,为学界所公认。但观此处“归死于尉氏”语,与“归死于司寇”、“归死于司败”等语几同,则可知尉氏之职能与司寇、司败相差无几也。
春秋时期多官司法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这里只从两个方面说明。
其一,这是由春秋时期官职的复杂性决定的。春秋时期职官与西周时期因此已经有很多变化,而且,各国的职官名称和系统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异。春秋时期有些国家没有司徒之名,如晋国因晋僖侯名司徒而改司徒为中军帅;有些国家没有司空之名,如宋国因宋武公名司空而改司空为司城。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桓公六年》)从《左传》所载主要职官来看,单一职能的职官很少,以本职兼任他职为常态,如司徒通常的职能为管理土地、财政赋役等民事事务,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军事权;司马通常为军职,但又常任外交事务,如鲁国的叔孙氏;又比如鲁国的司空同时可兼任司寇,等等。即使是同为一种名称的职官,其职能不一定相同,比如本书在前面论述的司寇,各国中多有,但也不能说其职能完全相同。司徒一职,在鲁国、晋国、宋国等国,地位相当于执政卿,但在楚国却负责工程事务,职能似相当于晋国、鲁国的司空。“令尹蔿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榦,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餱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宣公十一年》)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也说明了春秋时期职官的职能不可能像后世那么整齐划一,所以,某些在后世看来不可能具有司法职能的职官却同时兼具司法职能。
其二,春秋时期的多官分职司法的现象,在《周礼》中被体系化,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源于春秋时期的事实。据学者研究,春秋时期的官制,从名称到职能,其与《周礼》的职官体系的相似度要高于西周官制,说明《周礼》的职官设计相当大的一部分取材于春秋时期。[42]笔者赞同此说法。那么,《周礼》中记载的各种职官具有司法职官的现象,也与《左传》的关于多官分职司法的记载相符合,这应该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综上,笔者认为,春秋时期存在多官分职司法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