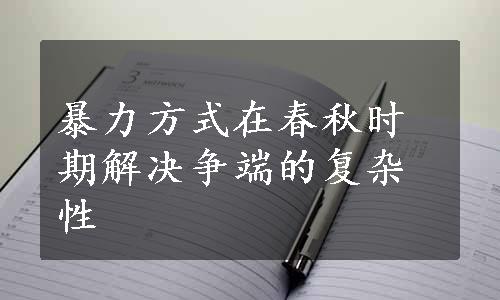
(一)战争
用战争解决纠纷在人类社会有着十分古老的历史。在春秋时期,这种解决方式主要用于解决诸侯国之间的争端。《左传》中常用的语词是“征”、“讨”、“伐”等。春秋时期,战争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点,战争次数之多、之频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孟子曾说过:“春秋无义战”。[92]又有人称《左传》为“相斫书”。[93]春秋时期,不仅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诸侯国内部也时常爆发战争。据学者统计,仅《春秋》、《左传》记载的战争数,就达到531次,平均每年两次以上。[94]春秋时期战争爆发的原因很复杂,有学者将其分为掠夺性、兼并性、报复性、干涉性和争霸性五类[95],其中有些战争就是因为纠纷所引起的。比如,国与国之间的纠纷而以战争解决的。据《隐公十一年》载:
郑、息有违言。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竟,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所谓“有违言”,即双方产生纠纷的意思,表现为“君子”所评论的“五不韪”。[96]春秋时期,因纠纷而引起战争比较著名的事例有:
1.郑国与宋国、卫国之间的战争。春秋初年,郑国的共叔段与郑庄公争夺君位失败,其子公孙滑出奔卫国,卫国为其伐郑。(《隐公元年》)两年后,宋穆公将君位传与侄儿宋殇公(穆公兄宣公之子),反令其子公子冯(即后来的宋庄公)出居郑,(《隐公三年》)故宋、卫联合与郑战争,持续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直到齐桓公为霸主才停止。
2.秦国与晋国之间的战争。秦晋之间因纠纷而引起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春秋中期,秦穆公有恩于晋惠公、晋文公,故秦、晋结好,互为婚姻。但两国在联合伐郑的过程中,秦国私自与郑和解,还灭了晋国的同姓之国滑国,因此两国发生崤之战(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晋襄公卒,秦康公欲使公子雍继承晋国君位,但执政赵盾已立晋灵公,故秦晋发生令狐之战(文公七年,公元前624年)。此后,秦晋之间较大的战争还有多次,断断续续持续到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4年)才告一段落,两国相互征伐前后长达70多年。[97]
从前面论述的五种纠纷类型来看,诸侯国之间的许多纠纷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解决的。上面所列举的郑国与宋国、卫国之间,晋国与秦国之间因君位继承引发的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又如,周王子朝与周敬王之争,卫惠公与公子黔牟的君位之争,郑昭公与郑厉公、公子仪、子亹之间的君位纠纷,齐桓公诸子君位之争,卫献公子孙之间的君位之争,都是通过战争方式解决的,而且双方还皆有对立的诸侯国的参与,使得春秋时期君位之争更为复杂。
即便婚姻纠纷中,亦有通过战争解决者,如齐国伐蔡之例。齐桓公将蔡姬逐回娘家,蔡国将其改嫁,齐桓公就发兵攻讨伐。(《僖公三年》)莒国伐向国之例。《隐公二年》:“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
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卿大夫之间发生纠纷,亦有互相征伐者。这与春秋时期卿大夫特别是本族的大宗(宗子)较强的独立性,包括拥有私人武装有关。故个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亦有通过征伐解决者。如楚庄王伐若敖氏(子越椒)而灭其族(《宣公四年》),这是君主对大夫的讨伐;孙林父与国君卫献公发生纠纷,据戚叛而伐卫献公(《襄公二十六年》),这是卿大夫对国君的征伐;郑国的伯有与公孙黑发生纠纷,公孙黑伐伯有;[98]晋国大夫赵鞅伐邯郸午、与范氏、中行氏互相征伐(《定公十三年》),这是卿大夫之间的征伐的例子;晋国的郤克受到齐顷公之辱,欲以其私属伐齐(《宣公十七年》),这是卿大夫伐他国之例。
(二)报复
“报”是中国古代很有特色的概念和观念,其中的内涵极其丰富。“报”的中心意义为“反映”或“还报”,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杨联陞认为,“报”之所以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观念,是因为“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映”或“还报”。[99]比如,《诗经·卫风·木瓜》云:“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论语·宪问》云:“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见,“报”注重的是行为的交互性和对等性,这在中国传统就是“礼”的体现。故《礼记·曲礼上》云:“太上贵德,其次务报施。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杨联陞是从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角度观察“报”的观念的。其实,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报”的观念还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交互关系上。在《左传》中,“报”也有多种含义。[100]比如,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会盟朝聘,是春秋时期经常发生的事,称为“报聘”。见下表:
表5 春秋时期“报聘”事例表
续表
春秋时期,与纠纷解决有关者,有“报恩”与“报复”正反两种情况。报恩在《左传》中通常与“施”相联系。如“结草报恩”即为其显例。据《宣公十五年》载:
秋七月,秦桓公伐晋,……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魏武子(魏犨)妾之父为报魏颗活女之恩,在秦晋辅氏之战中帮助魏颗打败秦军。
晋文公的例子可以较好地用来说明报恩与报复之间的对等性特征。晋文公在登上国君之位前,曾长期出奔在外,既有对之礼遇之国和人,也碰到过无礼的待遇。据《僖公二十八年》载:
(晋文公)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浴,薄而观之。……(曹大夫僖负羁)乃馈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弗听。及楚,楚子飧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榖?”……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乃送诸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
之后,晋文公在秦国的护送返回晋国做了国君。晋国用不同的行为加以回报。首先是对施恩的回报。对于宋襄公的厚待,当楚国侵宋时,宋国向晋国告急,晋国统帅先轸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僖公二十七年》)明确援救宋国的理由之一为报答宋襄公当年的恩惠。对于齐桓公的礼遇,晋国平定齐国君位继承之争。对楚成王的礼遇,虽为敌国,亦退避三舍。对秦穆公的恩惠,当秦国侵犯晋国时,晋相让以报,对秦国伐丧的无礼行为,晋才加以反击。对郑文公、曹共公的无礼行为,晋国伐之以报,但伐曹时,为了报答曹国大夫僖负羁的恩惠,晋文公“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并对违反规定的将领加以严惩。(《襄公二十八年》)
相对于晋文公报恩的“有礼”行为,晋惠公有恩不报的“无礼”行为导致的是被俘虏的后果。据《僖公十三年》载:
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与诸乎?”对曰:“重施而报,君将何求?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秦穆公在晋国大灾之时,给予晋国粮食的援助,于晋可谓有大恩,但第二年秦国大灾,晋惠公却背恩弃义,没有给予援助,晋大夫庆郑认为晋惠公这样做会失去民心,“背施幸灾,民所弃也”。果然,秦国伐晋,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军俘虏。如果不是穆姬(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女,晋惠公姊)及晋国大夫的请求,晋惠公恐怕不可能还能回到晋国。有恩不报,甚至会因此而遭到灭顶之灾。据《庄公十六年》载:
初,晋武公伐夷,执夷诡诸。蔿国请而免之。既而弗报,故子国作乱,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
夷诡诸与蔿国皆为周王室的大夫。之前晋武公伐夷,并将夷诡诸关押。蔿国为其求情,晋武公释放了夷诡诸,但夷诡诸没有按照礼的要求表示相应的报答酬谢,故而蔿国转而建议晋武公出兵杀掉夷诡诸,并瓜分了他的采邑。
“反报”和“报复”皆为近代国际法上的专业用语。现代国际法理论是将“反报”与“报复”进行区分的,如王铁崖认为,“所谓反报,就是一国以同样或类似的行为回答另一国的不礼貌、不友好、不公平的行为。”“所谓报复,是一国针对另一国的国际不法行为而采取的相应强制措施,以迫使对方同意接受由其国际不法行为所引起的国际争端的解决。”[101]但民国学者亦对两者不严格区分者,“报复”亦可称为“反报”。报复的特点是双方采取的措施针锋相对,就有一定的对等性,多用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外交行为。[102]我们在研究春秋时期的纠纷解决方式时亦不作严格区分。《左传》中关于“报复”的例子甚多,通常是以“报”作为常见的表达方式。先列表如下:
表6 春秋时期诸侯国“报复”事例表
续表(www.zuozong.com)
续表
上表所列,皆为国与国之间之战争报复行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就文献中出现“报”字统计,尚不包括那些虽没有说明“报”但实际上的报复行为,如越王勾践的报吴行为。但上表基本上反映春秋时期的基本情形,也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演变之脉络相吻合。现以春秋初年郑国、宋国、卫国的纠纷为例进行说明。据《隐公四年》载:
宋殇公之即位也,公子冯出奔郑。郑人欲纳之。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围其东门,五日而还。
宋殇公为宋宣公之子,公子冯(即后来的宋庄公)为宋穆公之子,两人为从兄弟关系。隐公三年,宋穆公临终前决定让侄子宋殇公继承国君之位(宋穆公就是从其兄宋宣公那继承君位的),而让其子公子冯出居到郑国避嫌,郑国打算支持公子冯与宋殇公争夺君位。恰好卫国与郑国有旧仇,故宋、卫联合陈、蔡等国伐郑,围攻其东门达5日之久。第二年,郑国侵犯卫国的郊外,并以王师(郑庄公为周王室卿士)联合被宋国占领田土的邾国伐宋,进入宋国的外城。《隐公五年》: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以报东门之役。[103]
但接着,“宋人伐郑,围长葛,以报入郛之役也。”(《隐公五年》)五年后,郑国又伐宋。“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隐公十年》)又过了十五年,宋国再次报复郑国,焚烧了郑国都城的渠门,进入郑国都城中大街上,并占领了牛首,将郑国太庙的椽子拿回去作为宋国的卢门的椽子。[104]郑国与卫国、宋国互相报复的军事行动持续几十年,真可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三)报仇
报仇又称“复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也是传统中国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现代学者中也多有讨论。[105]春秋时期,报仇也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提到的各种报复事例针对的是国家行为,而报仇则主要是个人之间的行为(具体到国君的报仇,则家国为一体,又另当别论[106])。比如,齐懿公夺大夫阎职之妻,阎职弑君(《文公十八年》)。又如,宋国乐师曹被卫献公鞭打三百,便利用演奏乐曲的机会挑拨大夫孙林父与国君的关系,致使卫献公被孙林父逐出卫国流亡十几年之久。(《襄公十四年》)
通常情况下,个人的报仇举动经常会伴随着国家的征伐行为。如楚平王为太子建聘妻于秦而夺为己有,并废除太子之君位继承权。(《昭公十九年》)四年后,吴国伐楚,“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昭公二十三年》)楚国的申公巫臣劝说楚王和令尹子反放弃娶夏姬,而自己却私下聘之,且不惜放弃在楚国的政治地位,带着夏姬出奔晋国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在楚王的制止下作罢。(《成公二年》)子重请楚王赏赐申、吕之田,亦为巫臣所阻,故巫臣奔晋国后,“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申公巫臣发誓报仇,遂请使于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成公七年》)申公巫臣与子重、子反的互相报复行为,不仅使双方皆遭到重大伤害,而且由于吴国的崛起,还改变了春秋后期的国际政治格局。有时,个人之间的恩怨会引起诸侯之间的一场大战。据《宣公十七年》载:
春,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献子先归,使栾京庐待命于齐,曰:“不得齐事,无复命矣。”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
郤克(又称为郤献子)为晋国卿大夫。晋景公欲伐附于楚的宋、郑、陈、蔡等国,命郤克到齐国聘问,要求齐国参加会盟伐楚(即引文中所指的“征会”)。据文献记载,当时到齐国聘问的除了郤克外,还有鲁、卫、曹等国的使者。诸国使者中,郤克是跛子,而鲁、卫、曹等国的使者中,或秃、或眇、或驼,齐顷公为了取悦于母亲萧同叔子,在举行聘问礼时派出接待的使者也是或跛、或秃、或眇、或驼,并让她在帷幕之后观看。萧同叔子看到各国使者的表情,忍不住大笑起来。郤克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对着河发誓报仇。回国后,郤克请求晋景公伐齐,没有得到同意。又想以郤氏家族的武装(“私属”)攻打齐国,但晋景公仍然不允许。三年后,郤克作为晋国中军帅,率领鲁、卫、曹等国诸侯在鞌之战中打败齐国,齐顷公差点被俘。齐国被迫求和,郤克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将齐顷公母亲萧同叔子送到晋国作为人质,在鲁、卫等国的劝说下,才作罢。次年,齐顷公到晋国朝见,郤克仍对当年受辱之事念念不忘,当着面对齐顷公数落一番:“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成公三年》)
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是倾向复仇还是反对复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以纪国亡国之事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春秋·庄公四年》载:“纪侯大去其国。”但《左传》与《公羊传》对此事的解释却大相径庭。《左传》的解释是:“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在春秋初年,齐国就不断地伐纪国。上年,纪侯之弟纪季以酅入于齐,为附庸,纪国开始分为两半(“始判”)。(《庄公三年》)但纪侯不愿意屈服于齐,又无力保国,故离开纪国避难。但是,到了《公羊传》那里,就变成了齐襄公“九世复仇”的经典版本:
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易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
原来,齐襄公九世祖齐哀公在周夷王时受到纪侯祖先的谗言而被烹杀。《公羊传》认为齐襄公灭纪是在为祖先复仇,故《春秋》讳之而书“纪侯大去其国”,虽然齐襄公有私通文姜之行为,但《春秋》仍对其为先祖报仇的举动予以褒扬。从上述观点的差异看,《公羊传》是主张复仇论的(但区分家仇与国仇)。《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多处与《左传》相异,[107]加上其成书时代较晚,[108]且以“义”胜,而非如《左传》以史实见长,[109]故不能据此认定春秋时期的复仇观念。
从《左传》的事例来看,对于复仇似乎有强调理由的正当性与否及区分公、私之目的。我们试以楚国伍子胥与郧公辛之事作为对比分析。伍子胥复仇之事是春秋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后世耳熟能详的著名掌故。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太子建师傅伍奢,其子伍尚对弟弟伍员(伍子胥)说了这样的话:
“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昭公二十年》)
这是认为报仇是孝道的体现。后伍员借助吴国之力攻打楚国,替父兄报了仇。此例中,伍奢无罪被杀,故伍员报父仇具有某种正当性。但是,吴攻入楚郢都,楚昭王出奔至郧,却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郧公辛之弟怀将弒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
陨公辛及其弟怀为楚平王令尹子旗(斗成然)之子。据《昭公十四年》载:“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与养氏比,而求无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使斗辛居郧,以无忘旧勋。”则令尹子旗乃是有罪被杀,且楚平王念及斗氏旧勋(斗榖於菟,即令尹子文),还让其子斗辛为陨公。故斗辛禁止其弟报父仇。可见,《左传》认为个人的复仇行为要具有正当性,否则是不赞成复仇的。郑国在处理大夫游眅被杀之事的态度上颇可说明问题。据《襄公二十二年》载:
郑游眅将归晋,未出竟,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杀之,以其妻行。子展废良而立大叔,曰:“国卿,君之贰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茍。请舍子明之类。求亡妻者,使复其所。使游氏勿怨。”曰:“无昭恶也。”
游眅为郑国公孙虿之子,[110]在去到晋国的路上,未出郑国边境,遇到亲迎之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夺他人新妇,其夫攻打并杀死游眅后带着妻子逃走。郑国执政大夫子展得知此事后,剥夺了游眅之子的宗子继承权,改立游眅弟大叔(游吉)为游氏宗主。另外,派人寻找攻杀游眅之人,令其回到原来居所,并下令禁止游氏之族对其复仇。这个例子说明,因为游眅的被杀是由于其自己的恶行导致,故复仇就失去了正当新理由。[111]同时也宣告用武力阻止(甚至是杀死)侵犯自己利益之人,在春秋时期被认为是一种“正当防卫”[112]的行为。同时,超出尺度的过分报仇亦被认为没有正当性。据《桓公十七年》载: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高渠弥因在郑昭公位太子时与其有仇,昭公复位后,高渠弥因害怕郑昭公杀己而先下手弑君。所谓“复恶已甚”,就是报仇之心太过分,[113]超出了当时的通常观念,故大夫公子达认为高渠弥以后将会被杀。果然,第二年高渠弥被齐襄公处以车裂之刑。(《桓公十八年》)
《左传》对于复仇的核心观念,是反对公报私仇的行为。据《文公六年》载:
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帑。夷之蒐,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捍之,送致诸竟。
贾季即狐射姑,原为晋执政中军帅,太傅阳处父将其中军帅之职更换为赵盾(宣子),狐射姑派续鞫居(续简伯)杀阳处父。此时赵盾又杀续简伯,故贾季出奔狄。赵盾念及与狐射姑的同僚之谊,派其属大夫臾骈[114]护送其妻、子及财产到狄。臾骈之前受到过贾季的凌辱(或处刑)[115],因此臾骈的从臣希望乘此机会将贾季之家人杀光,以报臾骈以前受到的耻辱。臾骈没有答应,其理由主要就是不能利用公权力来报私仇。这个例子除了说明春秋时期公与私已经有所区分之外,也说明了私人复仇具有了限制性的条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