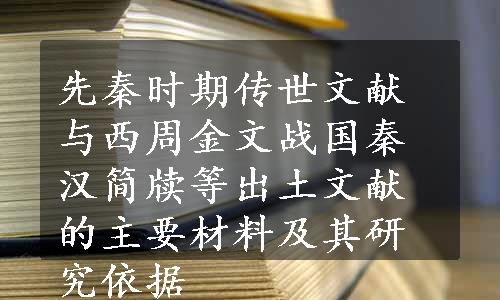
本书所用材料以先秦时期传世文献为主,兼及西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等出土文献。
1.传世文献。前辈学者曾经告诫:“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72]对于先秦史包括先秦法制史的研究,这种告诫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研究春秋时期的司法问题,史料的相对不足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要在各种有限的史料当中,辨别史料的应有价值。关于先秦时期各种传世文献对于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价值,史学界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本书对于传世文献的甄别取舍,以童书业先生所列次序为依据,[73]以《左传》为中心,参考《易经》、《尚书》、《诗经》、《国语》、《论语》、《墨子》、《周礼》、《礼记》、《公羊传》、《史记》等传世文献,并充分利用历代注疏成果进行校勘。下面,重点对《左传》、《国语》、《周礼》的史料价值稍作说明。
本书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左传》及其历代注疏的基础之上。原因在于,相对于其它史料,《左传》为研究春秋时期最可靠、最详细的史料。《左传》又名《春秋左氏传》,其记事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虽然对其作者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其成书时代也未有定论,[74]但对于其在研究春秋史上的史料价值,却早为学界所公认。比如,李学勤认为:“整本书有反复为出土文物遗存证明的,《左传》是一个佳例。《左传》所记人、地、事迹,多与考古发现的遗存和器物铭文相合,是这部要籍近来很少人再加怀疑的主要原因。”[75]事实上,司马迁的《史记》中春秋部分,除了依照《诗经》、《尚书》、《世本》外,主要的依据就是《左传》。考古学的发现也反复证实了《左传》记载的真实性。因此,《左传》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的基础。[76]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11月,由清华大学整理出版的战国简《系年》,共计138支简,分23章,编年记载了周初至战国初年的史事,第5章至第19章为春秋时期的史事,其内容基本上与《左传》所载相差无几,但其内容较之更为简略,更说明了《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真实性与详瞻性。[77]
《国语》亦为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典籍,其特点是以“语”(实际上多为当事人对某事的议论)的形式,分国别记录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之史事。与《左传》相比,《国语》所载的时间范围要长,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征犬戎,下迄周贞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但是,《国语》作为史料的整体感要比《左传》稍差,削弱了其史料的可信度。大概周语、晋语、郑语、楚语及鲁语上等篇风格比较统一,写作时代亦较早,但鲁语下、齐语、吴语、越语等所载明显带有战国以后的色彩,不能作为春秋时期的信史。[78]故而,本书的做法是以《左传》作为主证,而以《国语》作为旁证,两者的记载出现矛盾时,原则上以《左传》为主,参照先秦其它史料,结合春秋时期的总体特征进行述论。(www.zuozong.com)
《周礼》中大量的记载涉及到司法问题,特别是其《秋官》部分详细记载了司法官的名称、职能及其关系,以及诉讼制度的规定,对于我们研究先秦的司法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79]但《周礼》的成书时代,历代以来学者的看法相差太大,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年到西汉末年[80],故学界对于其史料价值是有分歧的。笔者同意这样的看法,《周礼》或许成书的时代要晚于春秋时期,但在对《周礼》的具体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后,是可以用来印证春秋时期司法的实际情况的。[81]
2.出土文献。本书的研究虽然以《左传》、《国语》、《尚书》、《论语》、《周礼》等先秦传世文献为基础,但同时也参考了相关的出土文献。比如,在论述春秋时期的司法职官、诉讼语词、诉讼程序时,就将传世文献的记载与西周金文、战国时期包山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进行比勘和印证,以加深对春秋时期司法的认识。当然,由于本书的研究中心是春秋时期的司法问题,故对西周、战国时期出土文献的运用还是辅助性质的。此外,虽然前面提到过刚整理出版的清华简《系年》对春秋时期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学界对其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且其对春秋时期的记载与《左传》雷同而内容简略,就笔者目力所及,基本不涉及司法问题,故本书暂不作征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