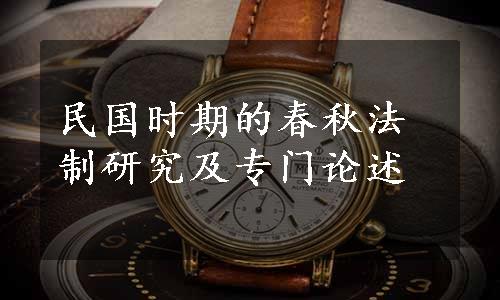
学界通常认为,用现代西方法学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是从梁启超和沈家本开始的。[13]春秋时期法制的研究也不例外。1904年,梁启超在《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一文中,以现代西方法理学方法分析了中国历代成文法编制沿革的内容及其特点,其中第二章为“战国以前之成文法”。该文列举了春秋时期的“齐之宪法”、“楚之仆区法”、“楚之茅门法”、“晋之被庐法”、“晋之刑书刑鼎”、“郑之刑书”、“郑之竹刑”七种“成文法”,并评论说:“刑鼎之制,与罗马之十二铜表,东西同揆矣。”[14]沈家本积数十年司法实践经验,撰有《历代刑法考》皇皇巨著,其中虽无研究春秋法制之专文,但散见于书中的论述亦不少。比如,该书《律令》中列有“晋常法”、“晋被庐之法”、“刑鼎”、“郑刑书”、“郑竹刑”、“楚仆区”等,沈氏多加以按语进行评论,特别是对于春秋后期“铸刑书”、“铸刑鼎”之事的评论颇有独到之处;在《行刑之制考》中,提到了春秋时期“涖杀”、“加木”、“刑于朝市”等独特的行刑方式,并与《周礼》进行了比较;在《历代刑官考》中,根据《左传》的记载列有“大士”、“尉氏”、“少司寇”、“司败”等司法官,并认为春秋时期各国官制与《周礼》所载不同;等等。[15]相对于梁启超浓厚的西方“法理学”研究风格,沈家本对传统法制的研究虽亦不乏“会通中西”的深意,[16]但其研究主要以资料梳理和考订见长。虽然沈、梁两人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且对春秋法制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很多问题皆论述不深,但其开创的研究思路和具体评价对后世法史学研究春秋时期法律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杨鸿烈的名著《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其上册“第四章”涉及春秋法制史方面的内容。作者一方面感慨这段历史的文献不足征:“在这百年里(引者按:指春秋后期晋楚争霸的百年),不知灭了多少国,破了多少家,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只可惜那时代的司法和社会的情形已无从详细查考了。”[17]但是,从《诗经》、《国语》、《左传》等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司法大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杨鸿烈对春秋法制史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一,作者以现代西方法学的编撰体例,按法典、法院编制、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民法、国际公法、法律思想等方面进行论述,这种编撰体例一直影响到了现在的法制史教科书;其二,杨鸿烈在书中提出了一些观点,对后世亦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在“法典”部分,作者除了将沈家本、梁启超所列的春秋各国“成文法”列入书中外,还补充了宋国的“刑器”、晋国的“戎索”、越国的婚姻禁令等[18],开拓了春秋时期“成文法典”研究的史料来源;杨氏援引英国学者梅因关于一切国家在未有成文法典之前皆经过一个“秘密法”时期的论断来评价当时的法制文明,得出了春秋时期“已由周代的习惯法时期进而成为成文法时期”、“子产是中国首先打破法律秘密主义的第一人”等看法,[19]对后世春秋法制史研究影响极其深远。在“法院编制”部分,杨鸿烈根据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20]一书,对春秋时期各国“最高的法官”情况进行了罗列,其中包括大司寇、司寇、小司寇、理、士、司败等,还注意到了“以行政官兼理司法事务”的大夫、宰等其他职官。该书还有某些看法也很有特色,如认为隐公四年(前719年)陈国使卫国大夫石碏“涖杀”卫国国君州吁的行为是一种“法庭互助”的性质;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元晅诉卫侯(卫成公)案中的士荣为“律师”性质、宁武子为辅即为“证人”;襄公十年(前562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一案中,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亦为“律师”性质,等等。[21]
徐朝阳著有《中国古代诉讼法》、《中国诉讼法溯源》两书,以现代诉讼法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法制,涉及周代诉讼制度时,所引材料多以《周礼》为据,具体内容涵盖传统中国社会的司法和诉讼制度,但也有涉及春秋时期司法和诉讼之事者。比如,对于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元晅诉卫侯案、襄公十年(前562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案,徐朝阳的评论是:“观其原、被告对质辩论,衡诸近代之所谓两造审理主义者,又何以异?”[22]认为春秋时期诉讼已采用西方近代普遍流行的原告、被告互相辩论的“两造审理主义”。又如,对于《吕氏春秋》、《史记》、《新序》所载楚昭王时“司法官”石奢不以父而废法的行为,认为反映了当时已经有了法官责任制:“至若法官之父,犯杀人罪,如为法官者,既不忍以父行法,又不肯阿有罪而废国法,法律私义二者之间,必偏于一,取弃甚难,若纵父而失法,惟有自承伏罪一途,别无其他救济方法。”[23]在《中国诉讼法溯源》一书中,徐氏还从史料中勾索出许多司法官的记载,包括鲁国的孔子、臧武仲,晋国的士景伯、叔鱼、李离,宋国的华御事、向为人,卫国的齐豹,齐国的庆佐等。[24]特别是对于卫元晅诉卫侯案的性质,该书列为专章进行论述,对于本案的性质,与杨鸿烈的观点不同,徐朝阳将其定为“诉讼代理和辅佐”性质。[25]徐朝阳的研究,比较系统地从诉讼法理论和方法上对传统诉讼法包括春秋时期的诉讼法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对于后世研究诉讼法史、司法制度史的学者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也给人以启发,但总体上看,作者用西方法学理论比附中国传统的色彩比较明显。(www.zuozong.com)
如果说上述学者对春秋法制史的论述,皆为片段、零散的,那么董康的《春秋刑制考》[26]一文则是民国时期仅见的专门论述春秋法制(包括司法)的论文。董康在这篇文章中,以唐律的编撰体例为坐标,利用现代刑法理论,从成文法典、法例、刑名、罪条、诉讼法五大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对春秋时期法制进行了阐述。作者在史料方面,广泛参考了《春秋》、《左传》、《公羊传》、《周礼》、《国语》、《尚书》、《墨子》等诸多先秦原始文献,征引史料之详瞻,为之前诸家所不及;而且,该文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如对九刑、铸刑书、铸刑鼎、妇人无刑、复仇等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五章中,作者专门列有“诉讼法”一章,首次对春秋时期的司法官和诉讼程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有些论述较上述学者理解得要真实和深入,比如关于春秋时期司法官制度、“坐狱”制度、盟誓制度,等等。董康的研究,为后来春秋法制的相关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从而为学术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底本”。[27]但是,董康对春秋法制的研究,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虽然论文名为《春秋刑制考》,但从时间上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春秋时期稍有不同,实际上指的是西周、春秋、战国在内的整个周代;其二,董康在编撰体例上以《唐律》为坐标,较之于以西方法学体例为准则的诸多法制史著作更符合中国的惯例和实际,但在某些方面仍旧采用现代西方法学的体例,典型者为第五章“诉讼法”部分,学者对此颇有微词。[28]第三,由于董康写作此文带有强烈的“求新知于故籍”的经世致用心态,故文中多有“以中化西”之处。[29]比如,将周代分封制比拟为西方的联邦制,将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的行为评价为具有“法治精神”,等等。
民国时期,还有一股研究思潮对春秋法制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即中国古代“国际公法”的研究,特别是“春秋国际公法”的研究。对“春秋国际公法”的研究,肇始于188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一文[30]。民国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国际法的论著主要有何炳松的《中国古代国际法》[31]、张心澂的《春秋国际公法》[32]、徐传保的《先秦国际法之遗迹》[33]、程树德的《中国古代之国际公法》[34]、陈顾远的《先秦国际法溯源》[35]、洪钧培的《春秋国际公法》[36],等等。上述有些论著的研究对象虽然囊括整个中国古代,但实际上重心皆为春秋时期。这些论著的共同特点是以现代国际公法理论来比附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如认为诸侯国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际法主体,盟会为国际组织,“行人”为外交人员,礼、信、敬、义或者自然法、国际道德、周旧制、习惯、条约、国内法为国际法的渊源;很多论著还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春秋时期的国际争议或国际纷争、战争与和平等国际关系问题。比如,在张心澂的《春秋国际公法》一书中,第六章为“国际争议之调和”,下设两节,第一节为“第三国之介入者”,分“周旋”、“居中调停”、“仲裁裁判”三种方式;第二节为“纷争国自行解决者”,包括“不用暴力的方法”、“用暴力之方法”两大类方式,后者又分为“报复”、“报仇”、“扣留君主或者使者”、“拒绝君主或者使者”四种方式。[37]徐传保的《先秦国际法之遗迹》,将当时的国际关系分为“和谐关系”、“不睦关系”、“战争关系”和“会同关系”四大类,其中解决“不睦关系”的方式有“交涉”、“成好”、“调解”、“干涉”、“裁判”五种。[38]陈顾远的《先秦国际法溯源》,总论部分第五章为“国际争议与国际公断”,其中将“国际争议之解决”分为“和平的息争手段”与“强硬的息争手段”两种方式,前者又分为“直接交涉”、“斡旋调停”、“国际公断”;后者则分为“反报”(或曰“报复”)、“复雠”(或曰“报仇”)、“封锁”。[39]洪钧培的《春秋国际公法》,第二编“平时法规”中第七章为“国际纷争之解决”,将解决方式分为“直接交涉”、“斡旋”、“调停”、“裁判”四种;另设第三编为“战时法规”。[40]虽然民国时期“春秋国际法”的研究并不一定符合春秋时期的实际,但是,他们的讨论对我们认识春秋时期的纠纷和争议是有帮助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