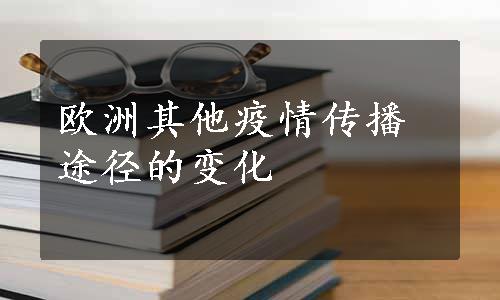
其他疫病方式的重大变化也出现于欧洲,或者作为1346年后鼠疫肆虐的结果,或者作为新疫病随着蒙古帝国的铁蹄在亚欧大陆向西蔓延。最突出的现象是麻风病发病率的减少,而这是黑死病时代之前中世纪欧洲的重要疾病。当然,那时的“麻风病”是一个集合名词,用来描述以显著而可怕的方式感染皮肤的多种传染病。今天该词所指的特定疾病,是挪威医务工作者阿穆尔·汉森(Armauer Hansen)于1873年第一次确认的细菌传染病。为把这种传染病区别于原被称为“麻风病”的其他疫病,有时也使用“汉森病”这一术语。
汉森病大约在6世纪已落脚于欧洲和地中海沿岸。[49]此后,与被视为麻风病的其他传染病一道,一直到14世纪仍然十分活跃。麻风病院在数以千计的中世纪城镇周围建立起来,到13世纪,据估计在所有基督教国家中达19000座之多。[50]
黑死病所导致的死亡肯定使许多麻风病院的病人减少,但认为该病随着所有患者的死去而消失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其实麻风病仍以相当的规模继续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规模较小;但麻风病人的数目已与1346年以前无法相比,麻风病院只能转做他用——或者改为医院,或者像在威尼斯那样,成为收容疑似鼠疫杆菌携带者的检疫所。
不容置疑,导致欧洲麻风病人急剧减少的生态环境已无法复原。最近的医学研究表明,可能与维生素C在食物中的含量有关,因为维生素能够抑制麻风病菌侵蚀人类肌体的某个化学过程。[51]但黑死病之后,欧洲饮食即使有变化,也似乎不足以解释麻风病发病率广泛但突然的降低。
另一个可能性更大的假说,是关于疾病竞争模式的变动。这个假说认为,欧洲麻风病可能因肺结核发病率的日渐增多而减少。其理由是:结核病菌引发的免疫反应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与麻风病引发的免疫反应有所重叠,以致宿主接触了一种传染病原,提高了对另一种传染病的抵抗力。在这种竞争态势下,结核有明显的优势,结核杆菌夹在感染者咳嗽和喷嚏的飞沫中进入空气,在宿主间传递,比其对手更富流动性。麻风病究竟是怎样在宿主间传播的,即便在今天仍无法确知;现在十分清楚的是,这是一种慢性接触性传染病,只有长期接触才会被传染。
不难想象,如果肺结核在1346年后确实更为流行的话,就有可能打断麻风病的传染链。办法很简单,只需先入为主,在欧洲人的肌体中激起更高水平的抵抗力,就能让慢了一步的麻风杆菌难以立足。[52]
然而这种假说马上又引起了新的问题:结核病是否在鼠疫暴发之后的欧洲更为流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是为什么?结核杆菌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分布最为广泛的病原体,结核感染早在初民时代就出现了,石器时代和埃及古王国时代的人类骨骸已被检验出有结核感染迹象。尽管肺结核的证据因其自身的原因还很稀少。[53]
在当代条件下,肺结核在城市环境下传播最快,那里互不相识的人们频繁往来,咳嗽和喷嚏即可以把结核杆菌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54]大约公元1000年后,城市就在西欧变得日益重要,但直到14世纪之后,城市人口在欧洲各地占总人口的比例仍不高。因此,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不足以解释麻风病的减少和肺结核的增多。
如果我们绕过这个问题而考虑另外一个变化,即于1346年后在清空(empty)欧洲麻风病院中可能起过作用的疫病变化,上述难题的合理解释也就浮出水面了。雅司疹(yaws,即莓疹)也被中世纪医生归为麻风病的一种,它源于某种热带莓疹螺旋体,而这种热带莓疹螺旋体与梅毒螺旋菌很难区分。通过与已感染的人直接接触进入皮肤以后,该病就以深而宽的疮口显示出来。雅司疹是否确实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如果存在,其流行程度又如何?凡此种种,都不得而知,因为它具有令人憎恶的症状而被列入麻风病的范畴。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欧洲人在哥伦布之前并非不熟悉热带莓疹螺旋体感染;一种专家观点认为,这种传染病就像结核病一样,属于人类最早认识的疾病,早在狩猎—采集者开始在地球上游历时就被带到世界各地。[55](www.zuozong.com)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念,即在1346年前雅司疹曾被欧洲人归入麻风病的话,则此后这种传染病显然衰退了。当梅毒在15世纪末暴发时,其毒性之烈与症状之触目,以及在患者体内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状况,在欧洲人看来都像是前所未有的新病。但产生雅司疹的热带莓疹螺旋体和产生梅毒的苍白螺旋体基本一样,其不同之处仅仅是宿主间转移的方式和在患者体内的传染途径。
在黑死病后的欧洲,这两种疾病可能都改变了传染途径,若果真如此,原因何在?显然,皮肤与皮肤接触的程度,首先取决于大部分人口尤其是穷人获得衣物和燃料的程度。在冬天缺少御寒衣物和取暖燃料的情况下,保持体温的最好办法就是人挨人地挤在一起,尤其在晚上。13世纪在西欧许多缺少木材的地方,这可能是农民度过严冬的唯一方式。然而,14世纪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得在同一个地方谋生的人比13世纪少了大约40%。显然,这意味着人们有可能得到更多的燃料和更多的衣物。另外,随着气候的恶化,14世纪的冬季比13世纪更为寒冷,这时若无法拥有足以御寒的衣物,仅靠挤在一起,已不再能够保持体温了。
众所周知,在14—17世纪,西欧羊毛织品的生产举世瞩目。根据现存史料,面向黎凡特(Levantine)和亚洲市场出口的高质量羊毛织物,比当地农民生产的粗质羊毛织物更多。倘若养羊业的日益发展(特别在英国和西班牙),以及更加寒冷的冬天,都没能促使欧洲人生产更多衣物的话,那就令人奇怪了。作为鼠疫所导致的劳动力短缺的结果,增薪使工薪阶层有条件购买更好的衣物;即便增薪不是一个普遍或持续的现象,降低了的人口与提高了的羊毛产量在西欧并存,这一基本事实也毋庸置疑。因此,即便是穷人,也有可能更加严实地遮盖自己的躯体。这样,欧洲人就有可能打破汉森病和雅司疹赖以通过皮肤接触感染的旧模式。于是,欧洲麻风病院的腾空也就易于理解了。
然而,羊毛纺织品越来越多的供应也会促进虱子和臭虫的繁殖,由此就方便了像斑疹伤寒这类疾病的传播。该病于1490年首先出现时,对欧洲的军队造成极大的损害。[56]另一个副产品是关于“体面”新标准的形成,它要求人们在大部分时间尽可能地遮盖身体。众所周知,十六、十七世纪,无论在新教还是在天主教国家里,都要求教徒隐藏性欲以及其他生理机能。这也从反面证明,即便穷人也能得到足够的衣物来遮盖身体。这种观念转变的日渐广泛,事实上间接而有力地证明了我的假说的正确性,即衣物在1346年以后的欧洲开始变得充足起来。
欧洲气候的寒冷和日益充足的毛织品供应,使麻风杆菌和热带螺旋体不得不直面生存危机,后者碰巧找到了一条生存通道,即通过性器官的黏膜在宿主间传递感染。该病的症状也随之改变了,欧洲医生在16世纪早期赋予它一个新名字——梅毒。[57]这不再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流行广泛的传染病,其症状也不再仅限于莓疹而一般不出现严重疮口(除非抵抗力减弱了)。现在的梅毒,大多只在成年人中传染,患者发病初期的症状也更为触目。一如人们熟悉的儿童病,譬如麻疹,表现在年轻人身上的症状要比在儿童身上的更为严重。[58]
然而,麻风杆菌却未能找到新的感染途径,只是维持在斯堪的纳维亚一地流行。那里的天气更加寒冷,衣物供应却没有增加,只好容许病菌维持其旧的传播方式。西欧其他地方与肺结核接触的增加,是否也对麻风病减少起到作用,尚无定论。但如果在中世纪条件下,结核接触赋予麻风病部分免疫的话,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上述这些假说的性质不言而喻。在当时情况下,其他因素的改变,如饮食的改变、气温的变化、公共沐浴方式的变化,都可能比衣服的增多更重要。尽管如此,确定无疑的事实毕竟是:鼠疫的反复发作、欧洲的人口衰减、羊毛制品的增加,还有麻风病院的清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