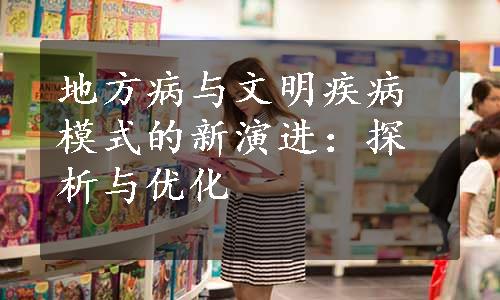
在这一进程展开之时,一些刚出现时对于欧洲来说相当致命的疫病,逐步演变成地方病——至少在那些人口稠密得可以无限维持传染链的地区。在人口不够稠密无法维持稳定的地方病模式的偏远地区,造成人口损失的传染病仍断续暴发。这类疫病从地方病的中心地区向外传播,沿着把分散的人口同城市中心连接起来的商业和流通渠道,深入农村和偏远地区,特别是海岛,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19世纪。[77]
然而,同传染病接触的增加却带来死亡人口的降低。传染病发作间歇期的缩短,意味着具有免疫力的人口比例的增加,这种免疫力是由早先疾病的侵袭激发的。假定某种疾病在时隔10年左右复发,只有那些从上一次传染幸存下来的人才会有孩子,这很快产生了有更高抵抗力的人,结果是相对迅速地进化到宿主与寄生物相对稳定的共存模式。
一种传染病让幸存者获得免疫力,又以5~10年的间隔复发,这样的传染病会自动成为儿童病。由于儿童,尤其是婴儿,相对容易补充,只感染他们的传染病对社会人口的影响较之不分老幼地袭击整个社会的疫病,自然要小得多。在所谓的“黑暗时代”,对传染病的适应过程在整个欧洲以这样有利的方式进行着,结果陌生疾病导致人口减损的后果在几个世纪中逐步消失了。
在西欧,对微型寄生关系渐趋增强的适应过程开始了很久,才建立起可行的对过度巨型寄生关系的限制。直到大约950年之后,一个由当地农村供养、装备和训练精良的骑士阶级才达到足够规模,并凭借战场上的勇敢无畏,把维京海盗从最富饶的西北欧驱逐出去。从那以后,尽管仍有不断的局部混乱和零星的掠夺,但这块土地上的人口还是开始了急剧增长的新时期。到这时,开始于2世纪的由文明的疾病圈相互渗透而导致的政治、心理和生物性后果已经被减弱了;在整个西欧最后跨入文明国家行列的动荡年代里,已经传遍拉丁基督教国家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才得以利用。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关于人们适应新疫病的详尽过程,我们还无从得悉。如果有通晓汉语的学者肯去爬梳中国文献以搜寻远东疾病的信息,相信也可钩沉出类似的模式:起初灾情严重,而后是与新疾病的适应。中国医学文献古老而丰富,在官方的正史和别的记载中经常提及疫病的异常暴发,但有关的诠释不力。关注古代中国和日本疾病史的学者在研究这一领域时,未能提出最具研究意义的上述问题。因此,在进行审慎的专业研究之前,可能仍难以发掘隐藏在浩瀚文献中的答案。
不过,有几点仍值得我们关注。在中国存在两部疫病史记载相对集中的史书:一是由宋代(960—1279年)的司马光所编[4],另一部作为帝国百科全书的一部分汇编于1726年[5]。这两部书均包含着抄写和日期转换不准确的地方;但可以把这两种文本相互参照,至少可以通过核对它们引用的资料更正部分错误。这样,我们把记录下来的中国疫病史做了重新编排,请见附录。[78]
通过按时间序列为这些疫病列表可见,在公元纪元早期出现了两大类疾病,并引发两次特别突出的大规模死亡:一次在161—162年,另一次在310—312年。根据列表,162年一场瘟疫暴发于当时正在西北边疆抵御游牧人的中国军队,夺去了十之三四的人的生命。310—312年,继蝗灾和饥馑之后,另一次重大的瘟疫在中国西北省份造成了百存一二的惨剧;十年以后即322年,又一场瘟疫接踵而至,在更大的地区造成十死二三的严重后果。
如果说第一类疾病只是可能性的标志,那么第二类则肯定标志着某种当时人们尚未接触过的新疫病在中国的降临,否则即便统计只是近似准确,这样的死亡率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类,可能牵涉一种伴生红疹和发烧症状的疾病,因为对这种病的最早描述来自一个名叫葛洪(281—361年)的医生所写的医学著作。书中记载:
最近有很多人在头、脸和身上都长了传染性脓疱,短期内扩散全身。其形如肿疱,内含白汁。旧疱刚去,新疱乃生。如不及时救治,病人通常死去。康复者因紫色疮疤而不堪示人,疮疤一年后乃去。[6][79]
这似乎是对天花(或麻疹)的准确描述,但尚有疑点,因其继续写道:
有人说,永徽四年(653年),这种病自西向东蔓延乃至入海。如果将可以食用的锦葵煮沸,混合以大蒜,然后食用,那么病症就会痊愈。如果初患此病就食用上述混合物,伴以少量米饭同服,也可治愈。因此病于建武年间(317年或25—55年)传入,其时中国军队正在南阳攻打蛮夷,故名“虏疮”。[7][80]
葛洪提到的这一事件系他死后300年才发生,这颇令人疑惑,不知这段有关天花的描述是在何时被写进去的。中国学者通常把自己的作品托于古人,因为古老使文献更令人尊重,有鉴于此,葛洪是否写了托于他名下的这个段落,或者天花是否在4世纪早期传到中国,都不能确定。不过,可能性仍然极大。[8]
即便依据这些零碎而不完整的材料,我们仍可断定,类似天花和麻疹这样的疾病在37—653年之间的某时来到中国。它们从西北跨越陆路而来,作为新的传染病侵入全新人口。其人口后果肯定与此时罗马世界正在经历的颇为相似。
至于鼠疫,中国对该病的最早描述始于610年,642年另一医家又提到它,并且观察到,这种鼠疫多发于广东(即广州所在的省份),而内地省份则较为少见,[81]这很有意义[9]。根据这些说法,我们可以推断,鼠疫系于7世纪早期由海路来到中国,距离该病于542年侵入地中海,仅隔两代人的时间。
在中国,正如在地中海,鼠疫的暴发肯定依赖于此前黑鼠及其跳蚤的扩散。黑鼠可能需要几世纪才能大量进入当地的生态系统,从而形成人类鼠疫大规模暴发的环境。无论如何,一系列的病变暴发于中国沿海省份,起自762年,当时“山东省死者过半”,然后断续流行,至806年又出现高潮,此时同样高的死亡率据称出现于浙江省。[82]
故而,根据这些不完整的史料,就新的致命的传染病可能从海陆两途来到中国而言,公元纪元早期的中国疾病史与地中海国家颇为相似。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人口在公元2年统计的大约5850万的基础上急剧下降。正如在地中海国家,人口的减少也伴随着行政的崩溃。残存的记载零碎而不可靠,但742年中国出现了另一份大致可靠的人口统计,记录的家庭数目大约是890万,而在公元2年登记的家庭总数则是1230万。此间,各种零碎的统计数字的复原显示了中国某些地区更剧烈的人口减少,尤其在南方,那里免受游牧民族袭击的相对安全性可能还抵不上从事中国式耕作的农民可能经受的更大的疫病风险,比如到5世纪中期,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南京周围地区统计出来的家庭数目只有公元140年时的1/5。北方的损失,尽管也很多,但在比例上尚不至于如此悬殊。[83]
在这些世纪里,中国和罗马之间,还存在着其他明显的相似点。220年随着汉王朝的结束,帝国统治在中国崩溃了。来自大草原的入侵和政治分裂相伴而至,到4世纪多达16个敌对国为控制中国北方而混战。极端的政治分裂,几乎正是与推测的天花和(或)麻疹同时来到中国的317年,而且,如果死亡率真的接近于司马光记载的严重程度(“百存一二”),原因倒容易理解了。相对于140年华北的490万户,370年同一地区的250万户比那些没有考虑到疾病因素的学者习惯认可的可能更可信。[84]
589年,中国再次完成了政治统一,而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重新建立地中海罗马帝国的努力却失败了。其中的差别在于,查士丁尼的帝国被542年以后反复暴发的鼠疫削弱了,而直到762年,同样严重的鼠疫并没有出现在中国,而且以后也只是影响沿海省份。尽管如此,755年的军事动乱[10]之后中国中央集权的崩溃,却与鼠疫的暴发时间相当接近。像鼠疫那样蹂躏易感人群的疾病很可能使帝国政府无法从沿海省份(未受动乱影响)征集资源来镇压起义,于是,皇帝请求游牧民族回鹘(今维吾尔族)军队的帮助,回鹘人自然待价而沽,结果迅速地把帝国财富转为己用。
宗教史为罗马与中国之间提供了另一个突出的可比之处。佛教在1世纪开始传入汉帝国,不久在社会上层赢得皈依者。它在宫廷的官方统治地位从3世纪延续到9世纪,明显地与同一时期基督教在罗马的成功传播相平行。像基督教一样,佛教也对苦难提出解释,而且也一如基督教在罗马的作为,佛教以其中国化了的形式为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和暴力与疾病的牺牲者提供安慰。佛教源自印度,与相对寒冷气候的文明相比,印度的发病率可能非常高;基督教形成于耶路撒冷、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城市环境,那里的传染病发病率也肯定高于较冷而人口稀疏的地方。因此从一开始,两种宗教都只得把突如其来的病故视为人生的当然事实,难怪两种宗教都劝导说,死亡是对痛苦的超脱,是进入跟被爱的人重新团圆的愉悦的来世生活的神赐通道,在那里世间的不公正和痛苦都将得到补偿。
还有,人口恢复的节奏提供了又一个东西方的相似处。到10世纪下半期,中国人口像西北欧那样,同此前困扰过他们先祖的疫病达成了生物意义上的成功调适,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到1200年,这个国家人口约为1亿。[85]要达到这种规模,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在微寄生层次上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达到相互适应,二是巨寄生关系得到规范,可以为中国农民留下足够产品,以在几代内维持极大的自然增长率。只有这样,成千上万的稻农才能充实华中和华南相对广大的区域。
达到在华南生存所必需的生物适应可能需要好长时间。直到8世纪,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人口真正稠密的迹象并不特别明显;只是到两宋时期,类似于黄河流域古来有之的人口密度,才出现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其他地区。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疟疾、血吸虫病和登革热可能对中国人南移起到过阻碍作用。人类对这些疾病先天抵抗力的差异、不同种类的蚊子之间的微妙平衡、各种温血动物的泛滥(毕竟人类只是蚊子的潜在供血者之一)以及传染体自身的毒性,毫无疑问决定着这些疾病的发作和严重性。但是有关中国农民如何在水田耕作方式所容许的密度下,学会在南方生存并日趋繁荣的细节,我们已不能奢望复原了,只需意识到,这种适应直到700年尚未完成,而完全占据南方则大约要到1100年才得以实现。
至于在巨型寄生关系的层面,随着960年宋朝的建立,相对有效的官僚制度扩展到中国的大部分(北方省份仍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相当合理的培训和选拔高级官员的方式[11]也定型了。官僚压迫并没有结束,但压迫的程度在宋代可能较以前有所减轻,对官僚阶层的制度性监督至少限制了明目张胆的腐败。人口向南方的大规模扩张表明,当存在足够多的新土地可供开垦以吸收过剩的子裔时,传统的租税依旧能让农民勤劳致富。
因此,对于我们关注的这段历史,中国的疾病经历明显接近于欧洲,但至少短期来看,则达到了比西方更成功的微型和巨型寄生关系之间的平衡。毕竟,在欧洲由勇敢的骑士们进行的地方自卫不能保证和平,因为骑士和他们的封建领主经常出现自相残杀,这也破坏了农民的生活及生产。从这点看,中国的帝国官僚统治显然更优越,只要它能够继续抵御来自北部和西部的好战的少数民族的进攻。还有,从微型寄生的层面,我们也可以公正地说,中国的成就更大,因为中国人在南下潮湿地区时是沿着疾病梯度往上攀登;而欧洲人口的北移是沿着疾病梯度向下滑行,进入的是感染机会较少的地区,因为那里气温较低,冰冻期也较长。
中国在适应微型和巨型寄生关系变化上的更大成功,反映在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文化史上。845年后,作为国教(a religion of state)的佛教被复兴且更加完善的儒教所取代。[12]这就像查里曼大帝(Charlemagne),在复活罗马皇帝头衔的同时,也复兴了多神教,将它作为宫廷宗教。当然,佛教继续在中国存在,主要吸引农民和其他无教养阶级。但胜利的儒教把最初吸引宫廷的佛教的形而上的理念吸收并融入自身,因此,融入官方儒教的佛教理念,与外来的疾病在中国人血液中引发并维持的抗体有相似的机理。因为,吸收到官方儒教中的新原则构成了道德和智力上的抗体,以抵御佛教的(或其他外来宗教的)拯救之路继续对卑微和无教养阶层所产生的诱惑。
日本的地理位置显然易于把它的群岛同外界的疾病隔离开来。然而,这是喜忧参半的事,因为隔绝有助于发展相对稠密的人口,而这又易于受到非常严重的传染病的打击——一旦某些新传染病成功地跨越海洋的阻隔,侵入到日本列岛。至少在日本的稻田耕作确立之前(这个过程到17世纪仍在进行),日本的农业人口与中国相比,仍很稀少;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日本城市也远比中国的小。这意味着,一些在中国已成为慢性病的重要传染病在日本直到约13世纪还没有扎下根。因此,在日本人口密度达到容许这些传染病成为地方病的临界点之前的600多年,日本列岛经受了一连串的疾病入侵。
第一次有记载的同大陆的接触发生在552年,那时来自朝鲜的佛教使团第一次登陆日本。外来者带来一种致命的新疾病——或许是天花。[86]同样严重的一次发病出现在一代人以后,即585年,到这时,由552年那次传染病产生的免疫力已经耗尽。一场时间更长的传染病开始于698年,在随后15年内波及列岛;该病于735—737年复发;又复发于763—764年;26年后,即790年,“所有30岁以下男女均被感染”。该病周期性复发的记载持续到13世纪,那时它已变成一种儿童病(首次记载于1243年),最后在日本列岛稳定下来。[87]
别的传染病引入日本并最终稳定的时间就不那么清楚了。808年出现了一种新疾病,“一半以上的人口死于该病”。联想到762—806年间中国沿海可能流行鼠疫的史实,极有可能这是一场侵入日本的鼠疫,尽管由于缺少临床描述,这一判断只具有猜测的性质。然而,在861—862年又一场新疾病——“暴咳”——袭击了列岛,并在872年、920—923年两次复发,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959年日本出现腮腺炎(它独特的肿胀症状即便在古代文献中也容易辨认),并复发于1029年。在994—995年的另一场瘟疫中,“死者过半”。如果这个统计有些许真实性成分的话,如此高的死亡率意味着一种陌生传染病的到来。有关麻疹的记载也令人感兴趣。麻疹的现代术语首次出现于756年,但以这一名称出现的严重而反复发作的传染病只始于11世纪(1025年、1077年、1093—1094年、1113年、1127年)。而它首先作为儿童病被提及是在1224年,仅仅19年以后,同样成为儿童病的“天花”亦接踵而至。
这些记录表明,13世纪日本列岛与中国(以及其他的文明世界)在疾病方式的进化上相当同步。然而,在此前600多年中,比起文明世界人口更多而间距更近的其他地方,日本遭受的传染病可能更严重。只要岛国人口不足以让天花和麻疹那样可怕的杀手转化为地方性的儿童病,这类每隔一代就要回返一次的流行性传染病,势必经常地和沉重地削弱日本人口规模,并以极端的方式阻碍列岛的经济、文化发展。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不列颠群岛。与法国、意大利或德国相比,中世纪英国的人口水平出奇的低,原因可能更多地归咎于岛民对传染病的敏感。然而不幸的是,即使穷毕生之研究,也不大可能把英国同欧洲大陆的流行病经历进行比较,因为大陆没有可与查理·克莱顿(Charles Creighton)的经典《不列颠疫病史》(A History of Epidemics in Britain)相提并论的著作,不过克莱顿能够为不列颠群岛收集那么多资料,这一事实本身或许就反映出,传染病在大不列颠比在欧洲大陆更为重要,即是说,后者地方病形成得可能更早,因为那里的人口更多,并且与城市(最初是地中海)的传染源有着几乎未曾中断的接触。(www.zuozong.com)
再者,当早期对传染病的敏感性消失时,无论在大不列颠还是在日本,关键性的门槛最终被跨过了。在日本这一转变发生于13世纪;在英国,因为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的灾难性侵扰,这一进程被推延了,以致长期的人口增长在1430年以后才开始。不过,一旦日本和英国跨越了关键性的疫病门槛,它们的人口状况都显现出比各自毗邻的大陆更有活力的发展。日本的结局是戏剧性的。对日本总人口的合理推测如下:[88]
至于大不列颠,可比的估计只限于英格兰:[89]
这里由于黑死病而导致的人口下降非常明显;日本从1080年到1333年的250多年间可能出现的人口倍增的情形,在英国却发生在1430年到1690年之间。
英国和日本出现的明显的与传染病渐进的适应,无疑与两个岛国的政治军事史有关。英格兰在不列颠群岛内侵入边地并镇压凯尔特人的历史众所周知;始于1337年进一步征服法国的努力,说明了更有野心地利用人口增长而加强军力的计划。当然,一旦黑死病暴发,军队即从这两类征服中退出。再度的扩张直到16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时代才恢复。从13世纪以后,日本在岛内(以牺牲虾夷人为代价)和海外(侵犯朝鲜和中国)的扩张步伐也明显变得更快更强。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大因素肯定是,当一度具有破坏性的外来传染病转变成较为平和的地方病时,日本社会内部就达到了一种新的疾病平衡。
不幸的是,现存的文献不容许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疾病史进行类似的重构。在公元元年到1200年间,欧洲人和远东人不得不适应的大部分新疫病,以前可能只活跃于印度和中东。无论如何,鼠疫似乎通过印度洋的航道东西扩散;光顾罗马和中国的红疹和热病由陆路而来,起点大约是中东国家——如果不是非要从终极意义来谈的话。
鼠疫来到罗马的同时,也可能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90]并且在这些地区也如同在地中海那样富于破坏性。由于运河的维修每年需要大量劳力,美索不达米亚人口的任何减少都可能由运河的荒废得到证明。据此,现代研究发现,在651年被阿拉伯征服之前,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口减少已持续几代,并且在被征服之后仍然如此。[91]没有理由认为新来的穆斯林对灌溉系统进行了任何重大的破坏,因为阿拉伯人已经熟悉灌溉,也无意于毁掉潜在的税源。似乎是别的东西打破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人口平衡。尽管土地盐化和其他技术难题妨碍了灌溉系统的稳定性,但经常遭受鼠疫感染,则为与7世纪阿拉伯征服相伴随的当地人口的急剧减少提供了合理解释。
至于印度,用于崇拜天花神的神庙的存在表明,这种(或极为相似的某种)疾病对于奉行印度教的印度在遥远的过去就极为重要。遗憾的是有限的记载让我们无法对1200年前印度的瘟疫史进行描述。
因为天花和麻疹在进攻新人口时,以及鼠疫在发作期间总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每当推测何种传染病导致某种大规模的暴亡时,这些疾病几乎垄断了文献所指。但人类交流方式的变化显然允许别的疫病也越出原来的流行界限而传播到新地区。这似乎是现代所谓“麻风病”的情形,对18000多具骨骸进行的专门研究表明,6世纪以前没有出现该病的症状,但此后却出现在埃及、法国和英国。[92]另外,归于《旧约》中所要驱逐的麻风病范畴的皮肤病则更为古老。为麻风病人建造的特殊疗养院,被证实早在4世纪就出现在欧洲,[93]但这不应作为出现新疾病的证据。毋宁说,这反映了罗马政府的基督教化,和对处理毁容性皮肤病的《圣经》训诫的严肃对待。
别的疫病在公元纪元早期肯定也占据了新的地理位置。某些疾病,比如结核病、白喉、流感,以及各种痢疾,可能都产生了与天花、麻疹和鼠疫相当的人口后果。而且以前可怕的地方病,在被迫与正在入侵的某些传染病竞争时可能消失了;正如下章所说,至少有理由相信,当新的剧烈的传染病把欧洲投入苦难时,这种情形的确发生过。
统一的传染方式并不存在,不过,尽管存在由气候和别的生态因素所决定的无数地域差异,似有理由推断,在旧大陆文明圈内,一个更接近统一的疾病圈,在公元1世纪作为经常性贸易往来的副产品正在形成。到10世纪,由传染方式的转变而引发的生物性适应得以在欧洲和中国确立,结果这些文明地区的人口再次开始增长。相应地,中国和欧洲对于中东和印度的相对重要性开始增加,尔后的世界史可以围绕着这一事实来书写。
此外,有理由相信有些周边民族曾跨越亚洲或扩张到东、西非,它们至少部分地进入以旧文明地区为中心的疾病圈。穆斯林和基督教的商人、传教使团深入亚欧大草原和北部森林地区,别的文明探险者深入非洲,在这些地方他们肯定带去了感染文明病的可能性,至少是间歇的、偶尔的、一代一遇或百年一遇的感染。
某些到那时还处于封闭中的社会肯定偶尔遭受过大量的死亡。然而在幸存者中,与新的传染方式的适应,在大草原民族一如西北欧那样进展快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土耳其和别的游牧人群深入文明地区,不管在亚洲还是在欧洲,他们都没有遭受非常可怕的疫病后果。如果他们的大草原老家对文明病毫无经历的话,这些游牧入侵者就会大量而迅速地死亡。
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在公元1000年前后,尤其在1000年后所进行的征服和入侵,如果没有这些民族对文明病的免疫力的话,就不可能发生,而且他们取得和维持的免疫力水平几乎等同于主要文明中心自身的水平。有关大草原的贸易方式和政治结构的所有已知事实都显示了这种可能性,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经常的长距离的迁移,偶尔大规模集结以进行掠夺或进行年度大狩猎(对蒙古人而言),提供了传染病在游牧群落之间交换和传播的充分机遇,甚至如中国史书所证实的,有时还与定居的文明人口交换传染病。
当一部分穆斯林商人和传教士游走于亚欧大草原时,另一些商人和传教士深入大部分非洲地区,其传染病的后果相似,尽管在非洲许多地方,该洲所特有的疾病构成了比其他大洲更可怕的对外来入侵的障碍。因此,文明的入侵有所局限,且非洲接触文明病的机会远不如亚洲大草原那么多。此外,当非洲奴隶在1500年以后来到新大陆时,他们没有因与欧洲疾病接触而大量死亡,这充分说明他们在非洲老家已接触到了一般的文明儿童病,时间如果不是在1200年前,就是在1200年之后不久。
相反,亚欧大陆在公元纪元第一个千年的传染病经历,在新大陆没有激起任何共鸣。当墨西哥和秘鲁的人口密集以至出现文明中心时,对旧大陆的传染病高度敏感的较大社会也就形成了。因此1200年后文明化了的美洲印第安人就像公元纪元之初的地中海人和远东人,人口已多到允许传染病肆虐的程度。但在讨论这种情况的可怕意义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探讨亚欧出现的第二次瘟疫动荡,其核心就是14世纪的黑死病。
【注释】
[1]即甲骨文
[2]西汉的起止年代应该为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受封为汉王。公元前202年,是刘邦打败项羽即皇帝位的年份;而221年,疑为作者的笔误。
[3]221年,应为220年
[4]即《资治通鉴》。
[5]即《古今图书集成》。
[6]该段文字的原文为:“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冶得差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
[7]该段文字的原文为:“世人云:永徽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煮葵菜以蒜齑啖之,即止。初患,急食之,少饭下菜,亦得。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
[8]上引《肘后备急方》中的文字确是问题多多,对此,范行准有较为详细的考证,范氏认为,水徽系为元徽之误,元徽为刘宋废帝的年号,元徽四年即公元476年。而历史上建武的年号有六,此当为南齐明帝之年号,即494—497年。这样的话,时间上虽仍不无问题,但大致可以接受。当然,这些都发生在葛洪去世之后(葛洪死于342年),据范氏的意见,这些文字系有陶弘景疏补《肘后备急方》时加入,陶的疏补完成时间约为500年,离上述时间较近,故曰“比岁”。(参阅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第106—109页。)
[9]作者这段关于鼠疫的论断主要依据了王吉民和伍连德的《中国医学史》中的描述,但遗憾的是,作者和王伍对此都存在一定的误会。首先需要说明,作者所说的610年和642年,其实是中国两部著名医书《诸病源候总论》和《备急千金要方》的成书时间。在注[81]中,作者列出了王伍对《诸病源候总论》中有关他们认为是描述鼠疫的文字的译文,还原成原文为:“恶核者,内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此风邪挟毒所成。其亦似射工毒,初得无常处,多测测痛,不即治毒入腹,烦闷恶寒,即杀人。”(见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三十一《恶核肿候》)然而这段描述明显源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该书中的原文是这样的:“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如梅李,小者如豆粒,皮中惨痛,左右走身中,壮热 恶寒是也。此病卒然如起有毒入腹杀人。南方多有此患,宜服五香连翘汤,以小豆傅之,立消。若余核,亦得傅丹参膏。”(见《肘后备急方》卷五《治痈疽妬乳诸毒肿方第三十六》)颇有意思的是,作者所说的642年的另一次论述,也明显是前面两段文字的继承与伸论,这里也转录如下:“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累如梅李,核小者如豆粒,皮肉瘆痛,壮热
恶寒是也。此病卒然如起有毒入腹杀人。南方多有此患,宜服五香连翘汤,以小豆傅之,立消。若余核,亦得傅丹参膏。”(见《肘后备急方》卷五《治痈疽妬乳诸毒肿方第三十六》)颇有意思的是,作者所说的642年的另一次论述,也明显是前面两段文字的继承与伸论,这里也转录如下:“恶核病者,肉中忽有核累累如梅李,核小者如豆粒,皮肉瘆痛,壮热 索恶寒是也。与诸疮根瘰疬结筋相似,其疮根瘰疬因疮而生,是缓无毒;恶核病卒然而起有毒,若不治,入腹烦闷杀人。皆由冬月受温风,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气结成此毒也。但服五香汤主之,又以小豆末傅之,亦煮汤渍时时洗之,消后,以丹参膏傅之,令余核尽消。凡恶核,初似被射公毒,无常定处,多恻恻然痛,或时不痛。人不痛者,便不忧,不忧,则救迟,救迟,即杀人。是以宜早防之,尤忌鱼鸡猪牛马驴等肉,其疾初如粟米,或似麻子在肉里,而坚似疱,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口即短气。取吴茱萸五合作末,水一升和之,绞取汁顿服,以滓傅上,须口服此汁,令毒散止,即不入腹也。入腹,则致祸矣,切慎之。”(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六十八《丁肿方·瘭疽第六》)该书确实也提到了这种疾病多发于岭南,中土较少,但不是仅指恶核病一种,而是说“恶核病瘭疽等,多起岭表,中土尠有”。而且事实上《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指出“多发于南方”,似乎算不上新的发明由此可见,暂且不论典籍中所说的恶核病究竟真的是否现代的鼠疫,就算属实,中国对此最早的描述也不是出现在610年,而应该是葛洪生活的3—4世纪,即使认为这一内容系由后来整理该书的陶弘景篡入,那也应该是500年,无论如何,都与作者这里所说的时间序列无法吻合。另外,将这种前后相续的有关某种疾病的论述理解为对该种疾病暴发的描述,也殊为不妥。还有,仅就其完全不提传染性这一点而言,恶核病是否为鼠疫就颇值得怀疑,若我们仔细研究以上三段文字,会发现其为鼠疫的可能性很小。
索恶寒是也。与诸疮根瘰疬结筋相似,其疮根瘰疬因疮而生,是缓无毒;恶核病卒然而起有毒,若不治,入腹烦闷杀人。皆由冬月受温风,至春夏有暴寒相搏,气结成此毒也。但服五香汤主之,又以小豆末傅之,亦煮汤渍时时洗之,消后,以丹参膏傅之,令余核尽消。凡恶核,初似被射公毒,无常定处,多恻恻然痛,或时不痛。人不痛者,便不忧,不忧,则救迟,救迟,即杀人。是以宜早防之,尤忌鱼鸡猪牛马驴等肉,其疾初如粟米,或似麻子在肉里,而坚似疱,长甚速,初得多恶寒,须口即短气。取吴茱萸五合作末,水一升和之,绞取汁顿服,以滓傅上,须口服此汁,令毒散止,即不入腹也。入腹,则致祸矣,切慎之。”(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六十八《丁肿方·瘭疽第六》)该书确实也提到了这种疾病多发于岭南,中土较少,但不是仅指恶核病一种,而是说“恶核病瘭疽等,多起岭表,中土尠有”。而且事实上《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指出“多发于南方”,似乎算不上新的发明由此可见,暂且不论典籍中所说的恶核病究竟真的是否现代的鼠疫,就算属实,中国对此最早的描述也不是出现在610年,而应该是葛洪生活的3—4世纪,即使认为这一内容系由后来整理该书的陶弘景篡入,那也应该是500年,无论如何,都与作者这里所说的时间序列无法吻合。另外,将这种前后相续的有关某种疾病的论述理解为对该种疾病暴发的描述,也殊为不妥。还有,仅就其完全不提传染性这一点而言,恶核病是否为鼠疫就颇值得怀疑,若我们仔细研究以上三段文字,会发现其为鼠疫的可能性很小。
[10]即安史之乱。
[11]即科举制。
[12]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北宋中期以前的相当长时间中,在中国社会有着非常深广的影响,甚至实际上有超越儒教之势,但将其视为国教,未免言过其实。事实上,中国社会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国教之说。作者这里以845年为界,显然是将会昌五年的唐武宗灭佛事件作为儒教取代佛教的分水岭,然而实际上,唐武宗灭佛,不过中国中古时期“三武灭佛”中的一环,佛教势力事后似乎很快得以恢复,而且儒学复兴,即理学兴起,乃是两个世纪以后——北宋后期以后的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