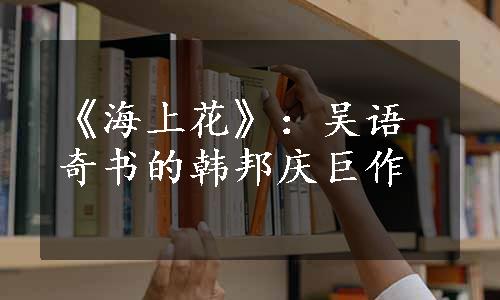
张爱玲(1920—1995)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具魅力的女作家,她一生创作涉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1969年后转研古典小说,曾对清末成书的《海上花列传》情有独钟。《海上花列传》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又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吸引传奇才女张爱玲为其倾力翻译并流传于世呢?
《海上花列传》是晚清时期以妓院及娼妓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一部小说,也因为如此,民国以来一直有人把这本书说成“专写才子优伶、妓院生活的‘狭邪小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从内容构思来看,《海上花列传》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二人从农村来到上海,为生活所迫、终至堕落的故事为主线,以上海妓院为中心,旁及官、商各界,为我们塑造了一批遭遇不同、性格各异的妓女、老鸨、嫖客、仆役形象。该书穿、插、藏、闪的艺术结构,平淡自然的白描写法,为当时小说所无;书中人物对话全用苏州方言,生动活泼,也开创了方言小说的先河。《海上花列传》的主线是赵氏兄妹在旧时上海这一“大染缸”的沉沦过程,中间重点描写五组主要人物。一是富家子弟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的感情纠葛;二是政府官员罗子富与黄翠凤、蒋月琴的关系;三是书香人家陶玉甫与李漱芳的生死离别;四是弱冠青年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最终无缘;五是风流子弟史天然对赵二宝的爽约。其间,又以洪善卿与赵朴斋甥舅两人为串线。
张爱玲译《海上花落》
韩邦庆著《海上花列传》
须知,以妓女生活入文,历来为正经文人所不齿,然《海上花列传》绝非以往专注艳情的低俗倡优小说之流,它取材现实,反思深刻,是一部难得的反映社会人生底层的力作。民国著名文学家胡适就曾极力推崇过《海上花列传》,并为之写序重刊。胡适赞之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又说:“苏州白话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了。希望他们(指说吴语的文人)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
正因如此,张爱玲也十分喜欢该书,她在给胡适的信中特别提到:“《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张爱玲爱此书,一则因为她乃上海人,能够深刻体会书中吴侬软语之妙;二则因为此书写法奇妙,立意深长,能够析透人性善恶,与张氏自身生活体验产生共鸣;三则因为此书确实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树一帜,使研究者不得不刮目相看。是以张爱玲花费大量精力,将此书翻译为英语和当时国语,并重新命名为《海上花》,又分为《海上花开》《海上花落》两部行世。
在依旧讲究封建道德、纲常伦理的晚清时代,这样的奇书,究竟是由怎样的奇人不惧世俗,不畏非诋,大胆地将它创作出来的呢?这个人就是出生于松江府娄县(今属松江区)的晚清才子韩邦庆。(www.zuozong.com)
电影《海上花》剧照
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写《海上花列传》时曾署名“云间花也怜侬”,他虽颇具才名,但英年早逝,死时年仅38岁。其父韩宗文是咸丰年间举人,素负文誉,官至刑部主事,故韩邦庆幼年随父寄居北京,曾经师从松江文人蔡蔼云习制举业,“资质极聪慧,读书别有神悟”,又兼文笔微妙清灵,深为世人称道。据传,韩邦庆考秀才时,写下《不可以作巫医》,通篇为游戏笔墨,有趣异常,考官欣赏其才华,又觉得文章不中程式,犹豫再三,还是定为一等,时年仅20岁。但这种不拘一格、笔走偏锋在当时带来的后果,却是此后屡试不举。无奈之下,韩邦庆旅居上海,与当时《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等沪上诸名士互以诗词唱酬,也曾短暂担任过《申报》主笔。
1890年,韩邦庆入彰德人(今河南省安阳市)谢星海之幕府。其实,早在1889年时,谢星海就曾寄书韩邦庆邀其入幕,但当时韩邦庆因家事所累而谢绝。不过阴差阳错间,谢星海并未收到韩邦庆回信,于是在次年又写信邀韩邦庆入幕,信中还明白催问行期,这使得韩邦庆左右为难。因为谢星海乃韩父之挚友,韩邦庆小时随父亲在京城,曾经住在谢星海家,是以谢氏非常赏识韩邦庆。最终,韩邦庆盛情难却,答应入幕。韩邦庆离开上海时,走得比较匆忙,来不及与诸友人一一道别,因此,他在为1890年6月2日《申报》所写《论宝清船主死节事》一文末又续道:“余将有彰河之行,与余友者千余人不及言别,书此敬谢,幸各自爱。”
侯孝贤根据张爱玲小说拍摄的电影《海上花》海报
但韩邦庆在位于河南的谢星海幕府为幕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为1890年夏至1891年秋之间。此后,他辞去幕僚之位,由河南彰德进京参加顺天乡试,但仍落第而归,遂与友人孙玉声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回到上海。回沪后,韩邦庆绝意仕途,潜心写作,并开始着手准备《海上奇书》杂志的创办工作。1892年2月,《海上奇书》第一期广告出现在该年新春的第一张《申报》上;不久后,第一期《海上奇书》正式发售。此后,韩邦庆不断在《海上奇书》上连载他所新写的《海上花列传》。1894年韩邦庆去世前,《海上花列传》连载完毕,其六十四回单行本也付梓出版。可惜的是,此书出版的同年,韩邦庆便病逝于上海。[1]
从《海上花列传》这部奇书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韩邦庆十分崇尚一种能脱离传统伦理束缚的自由生活,但由于所受教育和时代的局限,他很难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儒家教化的羁绊。因此,他的一生纵情与烦闷交织,充满了矛盾与彷徨。实际上,他的这种思想在清末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韩邦庆曾对友人说过:“夫阅世生人,阅人成世,万物逆旅,光阴过客。一切安富尊荣,智名勇功,曾不转瞬间泯然变灭而无所有。”作为一个由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松江、走向现代开放气息更加芬郁的上海的松江第一代转型知识分子,他所能感悟到的恐怕就是唯有把握现在才最真实,要及时行乐,保持平静心态,一切顺其自然,不必强求等凡此之类的人生哲理而已。境界虽不见得多少高超,但毕竟代表了当时松江人应对时代巨变的一种思想变化趋势。
[1] 白雪梅:《清末文人韩邦庆生平思想考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