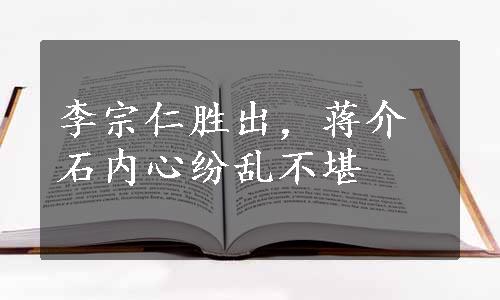
日军攻陷枣阳后,数路并进,快速穿插,中国军队的阵脚已被打乱。
5月9日,日军骑兵第4旅团超越16师团,在张家集附近渡过滚河,次日拂晓渡过白河,当天下午攻占新野。
同日,第13师团一部向枣阳东北突进,攻占湖阳镇。
5月10日,第3师团留在信阳的铃木支队一个半大队的兵力向西攻占桐柏。
连战10日,日军虽遭到激烈抵抗,但并未捕捉到国军主力。因而,冈村宁次判定国军主力仍在随州、枣阳之间的桐柏山区。
冈村宁次此战目的就是要聚歼中国军队主力,只要对手还在,就不能罢战休兵。汲取以往的教训,冈村令第3师团由唐县镇向西北吴山、三合店方向追击,第13师团由枣阳、湖阳镇北向双河方面突进,第16师团沿唐河岸向东北行动,阻止中国军队向湖阳镇以西撤退。
至此,日军的意图已完全暴露,即缩小包围圈,将第五战区左集团军主力压缩于桐柏至枣阳间的狭小区域内,围而歼之。
千算万算,冈村宁次还是低估了他的对手。
连日来,日军舍弃近在咫尺的第五战区总部襄阳、樊城不打,反而东、西两路全力向随、枣一带压迫,国军将领看在眼里,知道其中大有文章。
为了避免被日军合围,5月6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左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将军遂致电李宗仁,要求马上转移,跳出日军的包围圈:
(一)令八十四军立即脱离战斗,经随阳店向唐河转进。第十三军仍退入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区,相机以攻势行动攻击西进之敌,并切断敌后方联络线。三十九军仍留驻大洪山一带,牵制西进之敌,相机向敌后采取攻势。
(二)总司令部即撤离枣阳,向随阳店移动,与八十四军会合后向唐河撤退。
(三)建议长官部移驻老河口,及建议尔后左地区与长官部之联络改为南阳、唐河一线。
稍后,李品仙就携总司令部紧急撤向唐河。
经两昼夜急行军,左集团军总司令部于9日拂晓前到达唐河。夜间,途闻左方不断有枪炮声传来,李品仙等人知道日军随时有可能出现。到了唐河,接获南阳方面的报告才知道日军1000多名骑兵已于夜间占领了新野。
得到这个消息,李品仙真似劫后余生一般。遥望新野方向,只见天边一片红光,在夜暗中显得十分耀眼,那是日军在纵火烧房。李品仙久久伫立,心中感慨万千。
随后,84军也于9日到达唐河附近,转危为安。
至于汤恩伯的13军,就更不是省油的灯。李品仙令13军“退入桐柏山防守桐柏地区”,汤恩伯哪里肯听,命令一下,他就在桐柏山留下少量部队虚应故事,自己则带领主力向泌阳奔逃。途中,遭遇日军前锋的袭击,部队一度被截成数段,直到10日才退至外线的泌阳,而31集团军总部则退得更远更快,一直退到豫中的舞阳才作罢。
第五战区所有参战部队,就数汤恩伯的部队逃得最远。还真难为他,逃跑的速度竟如此之快,别说是友军,事后就连日军也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从战役目的来讲,也不能完全否定汤恩伯的作为。他若不逃的话,有被日军围歼的可能。只是汤恩伯如此消极避战,跑得如此之快,实在有失大将风度。
日后有人以此攻讦汤恩伯,汤除竭力替自己辩解外,甚至找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31集团军可以在河南打游击战,这也是响应南岳军事会议的战略精神。
南岳会议期间,国民党军开始重视游击战,在衡山办起了游击干部训练班,邀请中共将领讲授游击战术。起初担任游干班副主任的是中共名将叶剑英,而主任则是铁杆反共的汤恩伯,两个冤家聚在一起,在旁人看来,事儿肯定是少不了。
不料,没过几天,汤恩伯竟乖乖地当起学生来了。
当时,叶剑英在讲课中提出“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著名论断,在学员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汤恩伯也凑过来问道:“我们为什么打不过你们?”
这个问题显然已经困扰了汤恩伯多年,语气中透出几分诚意。
叶剑英看他问得如此诚恳,便很风趣地答道:“你们只有在沙漠地带能同我们打,在有群众的地方你们就不能与我们打。”
汤恩伯听后,深有感触,在一次全体大会上,他指着身旁的叶剑英,以十分敬佩的口吻说:“过去我们打你们,却老是打不过你们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们同民众的关系是鱼水的关系。”
从此,游击战这个概念就在汤恩伯的头脑之中生根发芽了,他也总想着把在南岳游干班学到的东西在战场上用用。但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汤恩伯只看到游击战保存实力的好处,却全然忘了主动进攻的精神。再说,游击战首先要处理好与民众的关系,而汤却在河南声名狼藉,被河南人民痛斥为“水、旱、蝗、汤”四大害之一。
借口总是借口,明眼人都清楚。李宗仁曾形象地描绘汤恩伯,“形势有利时就趁势猛打,形势不利时就卷甲远遁”,说得真是入骨三分。
就在我84军、13军远遁南阳的时候,日军仍旧做着合围第五战区主力的梦。他们哪里想到,中国军队主力早已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正在谋划对日军的反攻。
此时的冈村宁次已被南昌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他对鄂北会战的判断,中国军队行动迟缓,将领贪生怕死,而且情报显然也出了问题。所以,他不相信中国军队已逃出了他的大网,便命令部队继续合围,缩小包围圈。
日军第11军各部一味冒进,整个后方已渐渐空虚,暴露在我军面前,李宗仁苦苦等待的反攻时机终于到来。
第五战区南路,刘和鼎的39军还在大洪山一带坚守,襄东第33集团军虽被打散,但正在集合收拢兵力,伺机反攻。尤其是这两路的指挥官张自忠、刘和鼎两将军,虽出身旧军阀,但久历战阵,屡经艰险,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战时往往身先士卒,激励士气,具有强烈的主动进攻精神。此时,面对日军的猖狂北进,两军将士重整旗鼓,积极反击,日夜不停地攻击日军侧背。
不仅如此,日军的正面除了有我第31集团军与84军外,孙连仲第2集团军这支强援也及时杀到。(www.zuozong.com)
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除平汉线一侧外,日军已处于中国军队的三面包围之中。第五战区长官部有鉴于此,决定全线反击。
5月13日,五战区以第2、31两集团军向南阳、唐河西南攻击,以33集团军在枣阳附近发起攻击。3个集团军协同攻击,对日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同时,刘汝明68军自桐柏山南麓截击由信阳西进之敌,外线的江防军也发起攻击。
在这次随枣会战中,有一支抗日力量不能不提,那就是地方民团。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南阳别廷芳的民团武装。
别廷芳,南阳地方军阀,河南内乡人,1883年出生。此人残忍嗜杀,纤芥不容,在南阳人的记忆中,他的发迹史不堪回首,充满阴暗和血腥。
1914年,他半夜偷袭自己的好友曹会成,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曹的 13条枪。遭到伏击后,别氏怕被人认出,又枪杀了受伤不能行走的侄子,并毁尸灭迹。1918年,为了夺取亲家王谦禄的10余条枪,别氏故技重演,夜扮土匪,偷袭王家,打死王家6口人,抢走了所有枪支。1919年,别氏闻听老友袁江陵购有步枪五六支,又夜袭袁家,将其满门杀绝。
为了扩充实力,别廷芳丧失人伦,凶狠毒辣,无所不用。终于在1925年成为坐拥人枪达2000之众的内乡一霸。
之后,他又恃强凌弱,不择手段,五六年间,就控制了南阳全境。
乱世枭雄!别氏统治全凭个人好恶,一时性起,就能提枪杀人。
南阳人回忆说:“在他的统治区内,广大民众和那些敢据理说几句话的人,他们的生死荣辱,全凭别廷芳的喜怒好恶。
“1934年春,在县城有两个买卖铁锅的人在讨价还价,偶然从背后来一人说,卖锅人卖的锅是偷来的。为此,争吵不休。恰遇别廷芳路过,闻听后只摆一下头,就将卖锅人杀掉。
“别廷芳最讨厌民众打官司,他的信条是爱打官司的,都不是好家伙,对爱架秆打官司的‘衙骨’,他不分你有理没理,一律除掉。对给人写状词的人,别廷芳也认为此类人不是‘好百姓’,必予除之。城关镇皮袄巷有个姓李的,因给街头一家人写状词,别廷芳得知后,即派卫兵将其处死。”
别廷芳专横酷虐,但乱世强权,却也造就了南阳一时的稳定局面。
抗战军兴,别廷芳已控制人枪10余万众,国民政府自然注意到了这支力量。与其驱之为敌,不如为我所用,于是便不再纠结他的过去,任命他为豫南13县联防司令,授予少将衔。
别廷芳虽有着不光彩的过去,但在民族大义面前却不含糊。而且精明的他看到南阳正好处在第一、第五战区的后方接合部,国民党军重兵环伺,与其野战部队相比,他的民团不过是个卒子而已,对于上面的命令,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日军一到,他就毫不迟疑地率部协助第2集团军投入反击。
他一面命令沦陷区内的唐河、泌阳、桐柏、新野4县民团投入战斗,一面又从南阳、内乡、镇平、淅川调集精锐民团7000人,配合第2集团军,强袭日军。民团虽非正规部队,但熟悉地形又为保家而战,士气高昂,竟先克新野,再克唐河,随后投入总反攻之中,大破日军,毙伤日军甚众,缴获颇多,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明令嘉奖。
战场形势在向着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转变。此时的日军,苦战两周,虽攻城略地,突进至中国军队纵深,但战线过长,补给困难,而且各部受到我军和民团的不断袭扰和攻击,日军左支右绌,渐成强弩之末。
5月13、14日,在各路中国军队的奋力反击下,日军终于支持不住,全线溃退。
但是,撤退历来不那么容易!
一路上,日军除了被33集团军不停追杀之外,大洪山的39军也早已布下铜墙铁壁,严阵以待。
15日至19日,我39军在大洪山北侧的长岗店一线占领有利阵地,苦战5天,截击向应山、安陆撤退的日军第3师团、第13师团各一部。
其中,公秉藩的34师表现得尤为壮烈。15日,从枣阳溃退的日军3000多人与34师遭遇,一开始,双方都未轻举妄动,只是在大洪山鸡鸣寺一带对峙。次日,日军又退来步骑兵5000多人,即以其一部偷袭毛茨坂高地,进而占领鸡鸣寺,遂使34师腹背受敌,陷入孤军奋战之中。日军以炮火掩护步兵攻击,34师退据鞍山,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抗击,苦战5昼夜,以伤亡100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数百,击伤无数。直到19日,日军才摆脱中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仓皇逃去。
在武汉、南京的日军,无论是第11军还是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都为鄂北日军能否安全撤退悬着心。
22日,我军先后收复唐河、桐柏、枣阳,逼近随县。此时,日军除随县县城之外,其余均退回原占领区。我军各部虽歼敌甚众,但苦战已久,各部伤亡过大,无力追击,也渐次转入休整。
鄂北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随枣会战日军“将中国军主力包围击灭”的计划彻底破产。此时的冈村宁次,自然是十分懊恼。损兵折将不说,本来占据优势的11军,却平白地易主动为被动,战略目的不仅没有达到,还留给国军以击败日军的口实,这在士气和宣传上对日军都是极其不利的。
冈村宁次思来想去,还是无法排遣心中的郁闷。为了遮丑,他致电军部,将作战失利归罪于左翼兵团(第13、16师团与骑兵第4旅团)的迂回不力,以及右翼兵团(第3师团)攻击动作的迟缓,请求撤换第3、13师团的指挥官。
本来,11军下达给第3师团的训令中就明言,对中国军队的攻击不可操之过急,甚至连战车队、气球队的使用都做了限制。现在作战失利,却归罪于人,实在算不上光明磊落。
不过,话说回来,冈村宁次快速突进的战术还是可圈可点的。7天之内,日军最左翼的骑兵第4旅团前进了将近300公里,16师团突进约270公里,靠近中央的13师团前进约200公里,这样的进攻速度在日军战史上还是绝少见到的。与其在武汉会战的指挥相比,显然大有改观,尤其能避实击虚,大开大合,确实展现了冈村不俗的指挥能力 。
可惜,这不过是一场华丽的表演而已。经过此战,他一直不愿面对的恐惧和忧虑才真正到来。他深知,解决“中国事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打垮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摧毁蒋介石的抵抗意志。可如今,苦战半个多月,在指挥、作战并无重大失误的情况下,非但不能伤及中国军队的元气,竟然还让中国军队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损兵折将,今后日军还有多大的机会达成战略目的?
可以说直至此次会战前他还充满信心,以为结束战争不过是时间问题。现在看来,局面远非他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国军队已经具备了持久抵抗的能力,日军解决“中国问题”的前途开始变得黯淡起来。
“支那(中国)战争泥沼,看来真正陷进去了!”
武汉,生性强傲的冈村宁次咀嚼着失败的苦涩。
一家欢喜一家愁。
重庆,蒋介石翻阅着军委会送来的战报,心情渐好,反攻南昌失利的阴霾也荡去不少。南昌、鄂北,与冈村宁次这个强硬对手的较量一胜一负,结局尚可。更重要的是,第五战区收复失地,掐断了日军控制的平汉铁路,战略上中国军队仍对武汉形成威胁。只要保持现在的态势,日军就不敢放开手脚再发动攻势,战略相持的局面就能维持下去,他就能赢得时间调整部署、整训部队。
“李德邻到底是老行伍,还是能打仗的!”
蒋介石心生感慨,再想想他的黄埔嫡系,内心五味杂陈,不是个滋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