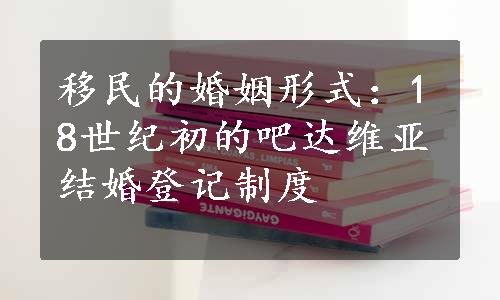
明清时期,国人成婚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正统,即使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也要由男方请一个媒人上女方家正式提亲,方为正式。经媒人介绍后,双方宗亲认为生辰八字相合即可成婚。这种婚姻形式我们称为传统式婚姻。而正式登记注册成婚,即男女双方在婚前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报备,领取结婚证书,这在中国古代则甚为少见。但是,据吧城华人公馆档案资料记载,荷兰殖民者统治下的吧达维亚(今印尼的雅加达),早在18世纪初就有登记注册成婚的形式。
根据吧达维亚的唐人公馆档案,18世纪末吧城唐人婚姻形式可分为正式登记注册结婚和非正式登记结婚(或称为传统式结婚)两种形式。
(一)正式登记注册成婚
吧城唐人采用结婚登记制度始于1717年,是海外中国人最早采用登记形式的。其程序大概是:首先当事人通过结婚申报书,报上男女双方姓名、年龄及双方家长姓名,经审查许可后,发给结婚证书。结婚证书及《成婚注册存案》簿上有新郎、新娘的签字,有男女双方主婚人的签字,有媒人的画押,有公馆甲必丹、雷珍兰等审查者的署名签字。荷兰殖民政府为什么要求唐人结婚登记注册呢?是否仅是为了收取唐人的结婚税呢?而实际上,早在1717年之前,荷兰殖民者就规定唐人成婚者须缴纳结婚税。1706年12月7日,吧城荷兰东印度公司政府公告,荷兰政府告诉纳税的武直迷(Boedelmeester,财产管理官,理救济院及遗产事宜),无钱的唐人不必付结婚费,其他唐人要向市政府交5文(1文等于2.5盾)结婚费,还要交一二文给中华医院。[3]那么,规定登记注册结婚又是为何?是否想通过这些手续,使结婚者得到社会的确认,而且也得到政府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尤其是使唐人死后其妻室子女对其财产的处理有法律依据呢?由于材料不足,对这个问题只能进行推论。
根据现存最早的吧城唐人公馆档案,即从1772—1791年档案的记载,唐人正式登记注册结婚的对象分为四类,[4]即:
1.与唐女结婚
这里所说的“唐女”是指中国女子。但根据史料分析,在荷属东印度和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槟城,甚至是后来的新加坡,真正从中国南来的女子,是很少见的。据《开吧历代史记》记载,吧城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只移入一位中国妇女。据说,这件事情在当时几乎达到轰动整个吧城的程度:“康熙卅八年,己卯,即和1699年正月,唐船来吧,有王界夫妇,潜搭此船来吧,登岸时唐番俱见,此信播扬通吧,直至大王耳边。王界妻郑氏,伴态生成,仪范端庄,衣服与吧人迥异,大王询之备细,切意欲观中华妇女,即令人来请,王界夫妇,齐到王府内相见。”[5]
也许,上述史料所言有些夸张,但大多数史学界的专家学者认为,在明清时期,从闽粤沿海乃至整个中国沿海渡海南来荷属东印度和海峡殖民地的妇女确实少见。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在轮船发明使用之前,由于航海技术较为落后,一般从事海上贸易的帆船安全系数不高,船上的空间也不大,携眷外出不方便,因此南来的华侨一般不带女性家眷同行。其次,当时的中国政府政策规定,出洋远行不能带家眷同行,而且华侨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一人在海外奋斗打拼之时,家眷得在老家照顾父母老小,以尽孝道,且祖宗香火也需有人照料。再者,早期移居南洋的华侨,由于大部分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即使在老家已经成家,也不会带家眷到南洋。出于上述诸原因,早期南来的华人女性很是稀罕。那么,公馆档案中所指的唐女,应该是指华人男性和与华侨宗教信仰没有什么冲突的当地女性——巴厘女、武讫女等结合所生下的“峇峇”(Pananagan)——土生华人。
与土生华人女性结婚,在17中叶至19世纪荷属东印度和马六甲及较后期的槟城华侨中是常见的事。但这种通婚,通常发生在较富有的华侨之间,或者较富有的华侨之女在地位比较低的伙计中选贤婿时才出现。下面列举吧城公馆档案中的数例说明:
1778年5月6日,住在吧城监光(唐人街)猫汝的毛成公与朱政娘结婚的《成婚注册存案》簿中记载到:[6]
遵奉王制,为婚姻事,今据男家毛成公,年16岁,住监光猫汝,女家朱政娘,年14岁,媒妁林宣娘,合和琴瑟,结缔朱陈,禀明甲必丹雷珍兰列位大人台前察夺,成婚注册存案,给照准此。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十日,即和(“和”指荷兰,荷兰使用公元纪年)1778年5月6日给。
甲必丹黄(衍观),雷珍兰杨(款官),雷珍兰唐(偏舍),雷珍兰蔡(敦官),雷珍兰吴(泮水),雷珍兰王(珠生),雷珍兰高(根观)。
男家主婚,宗叔毛扶官(拈笔画押),女家主婚,胞叔朱尊官(拈笔画押)。媒妁林宣娘(拈笔画押)。
第22号,钱59文1钹1方半。
又如,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三日,即和1783年11月26日《成婚注册存案》簿记载:圣墓港许孙官(17岁)与蔡甘娘(15岁)结婚,媒妁颜宴官,男家主婚父亲许钟官,女家主婚族兄蔡杭官,第118号,钱6文。其余所载,与毛成公、朱政娘成婚注册存案相同。[7]
从现存的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中华人《成婚注册存案》记载的新郎和新娘的年龄来看,成婚对象都很年轻,年龄在14岁至17岁左右,属早婚,可见,只有当地出生的唐人子女(但估计大多数为唐人与当地妇女,如巴厘女子结婚所生的土生华人子女),靠父辈的经济支持才能少年成家。结婚还要交纳一定的结婚费,供中华医院之用。
再如,雍正《朱批谕旨》第55册记载:漳州陈魏,1714年到吧城,1716年娶杨氏,福建人,生三个女儿,1733年其妻去世,因无子买蕃妾二人。同安人杨营,1728年到吧城,娶郭氏,唐人,生子两个、女儿一个。哥哥杨课在吧城娶妻生子两个,1732年哥哥去世。1733年6月带妻子及嫂子、侄儿回厦门。
2.与唐人养女结婚
所谓与唐人养女结婚,是指吧城华侨娶当地的华侨养女为妻,而唐人养女一般是指在当地出生,且过继给当地华侨的侨生女——“峇峇”,或是当地土著女子。在《成婚注册存案》簿中有不少这样的记载。
如乾隆四十二年一月十九日即和1777年2月26日《成婚注册存案》簿记载:打铁街后黄章兴(28岁)与陈益娘(25岁)结婚,媒妁马喜娘,男家主婚是黄章兴自己,女家主婚是新娘宗兄陈傅公(时泰),旁注明“新娘雅朗官养女”。这里记载的雅朗官即朗官太太,陈益娘为其养女。1777年2月26日《成婚注册存案》同样记载有,暗涧陈顺官(40岁)与戴文独(17岁)(旁注:雅戴甲养女)结婚,媒妁林七娘,男家主婚为房叔陈秀官,女家主婚为宗叔戴换官。
唐人养女,有当地女子,也有侨生女,而以前者为多。
3.与已出身[8]入唐籍的女婢结婚
吧城唐人与已出身女婢结婚者不少。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三月十五日即和1790年4月28日拜三公案,王海称与武讫人结为夫妻20余年,其妻亦系人之女婢出身,此为一例。也有许多唐人是与未出身女婢私合生子后,才付其出身,使之成为妻妾的。
被卖为奴婢的当地女子,卖价为100文左右,而奴婢要赎身为自由人,也同样要付钱。如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月十三日,即和1787年11月22日拜四公案中提到雷珍兰高根观(厦门人)遗嘱“付女婢5名出身”“一做出身之女婢春梅,吗年,当寅,每名钱100文”可以为证。出身后的女婢,经拜唐人为义父后,改用唐人姓名加入唐籍,以做字立约为准,方能与唐人登记结婚。其手续过程,从蔡捷明与新尧立吉女婢劳吉申请婚字书(结婚证书)的经过可窥一斑。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七月十二日即和1788年8月13日拜三公案,甲必丹蔡敦官回复荷官实奎炳有关婚姻事云:
1788年6月25日,蔡捷明与荷人新尧吉立女婢劳吉申请结婚,持荷兰字一张,称是荷人缎厘戎之字,并称女婢生于吧地,已拜游六郎为契父,改为唐人姓名陈贤娘,恳求甲必丹蔡敦官给婚字书,未许。后新尧吉立来议此事,甲必丹蔡回答此事曰善,然此婢已入唐籍,并无凭据,是以责蔡捷明作事糊涂,何不先到敝处斟酌得宜,方可到公堂给字。列位雷珍兰会议曰:自古以来,未尝有提起异色出身女婢亦准给字,况数年前土库(办公处)内上人有出示,不许番唐结婚。历代未有此例,故未敢擅专,以干国法。后公堂召问游六郎有否作义父,游六郎答作义父之事不知,是昨晚蔡邀来办交婚字。列位雷珍兰会议:此事糊涂,况兼是荷兰女婢,是以未敢给付婚字。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八月四日即和1788年9月3日公案,实奎炳倒案(定案)准给结婚云:
1788年9月1日,蔡捷明与劳吉齐到实奎炳台前申请结婚,呈上唐字二张,一为游六郎愿认劳吉为义女,命名荫娘,一为劳吉拜游六郎为义父。上台召问游六郎果有此事否,游六郎认可,因是案夺批准,仰唐人甲必丹给发婚字,成其配偶。1788年9月12日甲必丹给出婚字书。是日,蔡捷明与荫娘齐到朱葛礁(书记)处,花押在交寅簿上,二人正式成为夫妻。
4.入赘结婚
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家的家族成员谓之入赘。有些学者称之为“母居婚姻”。[9]根据傅利曼博士的观点:男人入赘即男人婚后和女方娘家人同住的情形可分为几类。最极端的一种是招赘。被招赘的男子,其作用和已婚女性相同,即为妻家提供子嗣。被招赘者在闽南语里被称为“卖大叮”或“给人吊大叮”,表示他放弃自己在自家姓氏叮下的地位,而“嫁”出去为岳父家生儿育女。他并非岳父母的儿子,而且是一名男性的媳妇。但是如果他娶的不是这家的女儿,而是这家的童养媳,则他的地位和妻子相比,可能会高一些。另外还有一种类似的安排:这名男子和妻子所生儿子中,可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可承袭父姓。譬如在结婚时就已约定,只有长子随母姓,其余子女则随父姓。[10]还有一类入赘在闽南语里被称为“进做”,就是一个男人在婚后与妻子家人同住,但不丧失任何为父的权利。这种做法在荷属东印度或海峡殖民地的华侨社会中是比较常见的。而且早期移民社会喜欢这种安排,因为还没有着落的“新客”可在妻子家人那边找个避风港。当然,处于“进做”地位的丈夫,其地位并不低,不仅如此,他可能还被视为享有某些特权。下面列举一吧城华侨社会男人入赘的事例。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廿二日即和1777年5月28日,《成婚注册存案》记载,吧城21岁的吴莽娘,“因前夫刘察身故存下子女,无依无奈,招巫亚票为夫,议养子女,二人两相情愿。”巫亚票前住王部,即蔗糖厂的甘蔗种植园内,年纪36岁,经媒妁人沈总观介绍,公馆甲必丹黄衍观,雷珍兰高根观、吴泮水、王珠生、郑隆观、蔡敦观、唐偏舍审批发给结婚证书,编为31号,二人在婚字簿名字下面拈笔画押(画圆圈为记)存案,并交结婚费8文1钹1方半。
(二)非正式登记注册结婚
非正式登记注册结婚,也称为传统式结婚,即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经媒人介绍后,双方宗亲认为生辰八字相合即可成婚。这是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人采用的一种传统结婚方式。随着闽粤居民移居海外,家乡的传统结婚方式也被带到华侨社会中。这种婚姻方式在荷属东印度和海峡殖民地的华侨社会中均较为普遍,只是在荷属东印度,尤其是由荷兰人直接管辖的商贸据点,如吧城,由于荷兰殖民政府要求华侨执行登记注册结婚制度,因此一些华侨的传统式结婚形式为正式登记注册结婚的形式所取代,当然,也有不少华侨的结婚方式是两种兼而有之。
18—19世纪的吧城华侨结婚,除了遵照荷兰殖民政府的规定,实行登记注册结婚外,也有一部分华侨,尤其是居住在吧城以外乡下的华侨,采取非正式登记注册的结婚方式。这些未经登记注册的结婚者根据有关专家的看法,也可以分成四种类型。[11]
1.与唐女非正式登记结婚(www.zuozong.com)
比如,据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一月廿八日即和1790年1月13日拜三公案中,在旧把杀(指旧市场或旧集市)卖鲁肉(卤肉)生理曾随申诉,其妻余成娘被大姨余近娘引诱与人私通。列台问:交寅(马来语或闽南语,结婚的意思)几年,有结婚字否?曾随答曰:无结婚字。余成娘申诉,曾随拐骗年方16岁舍妹成娘私奔,岂有交寅之理。及成配之日,日用饮食,分毫不理。[12]此记载表明两人系私合,后经判决分离。
1790年1月27日公案,杨远娘申诉:其夫李天河要与氏分离,且要将小女带走。列台问:有结婚字否?答曰:无。李天河谓其无计可养妻小,以此欲泊割。列台劝和好。
1790年8月11日拜三公案,黄沧供谓其妻杨桂娘被外父杨兴带回,不许再来。刘台问黄沧娶妻有给交寅字及行婚书仪礼之帖否?黄沧禀云:给交寅字及诸礼帖皆无,唯两家甘愿,随便成婚而已。杨兴云小女为夫殴辱,衣食难堪。刘台责黄沧殴妻大不该,黄沧服罪,劝双方和好未成,判离婚。后离而复合,9月1日齐到公堂补给交寅字。
以上三例没有登记结婚的公案均在一年之内发生。
又如和(荷兰)1826年9月22日,拜五,唐丙戌(道光六年)八月廿一日,公堂嘧碴唠(意为诉讼、审案、商议),值月公勃低(“公勃低”是荷语、马来语gecomnitteerde的音译,意为代理人,在这里指每月在公堂理事的两位雷珍兰)郑甲解官不到、叶甲选官。其中一案例为王守、黄合、胡报夫妻申请补发结婚证书案:
公勃低婚字雷珍兰戴明基官申详公馆,为前日给婚字期,黄合、王守、胡报供称,伊三人要给婚字,因先婚后给,卑职未敢擅便,备由申闻,以凭甲必丹大(高长宗)暨诸雷珍兰案夺施行。
大清道光六年丙戌七月廿二日,吧1826年8月25日
雷珍兰戴鸣歧具
王守同伊妻张愿娘:
据愿娘供称:伊夫陈艳照为夫妻六年三个月,生下二女:名陈银娘,年二岁;陈簸娘,年一岁。艳不幸,有七年之久,至和(荷兰)1812年,再嫁王守为夫妻,至今一十五年,生下一女,名王劳智娘,年六岁;又一男,名王文显,年十四岁。未给婚字。
守恳公堂恩恤。
男:王守,年三十七岁。女:张愿娘,年四十三岁,住在丹林望(Tanah Abang)。
胡报同伊妻林谦娘:
据报供称:现住大南门外直街前,完婚之时在井里汶(Cirebon)。已未三月初一日和(荷兰)1797年,彼时井里汶完娶成婚,无给婚字之例。
报禀知,伊生下一女,名胡金娘,年二十六岁。报恳公堂恩恤。
男:胡报,年五十八岁。女:林谦娘,年五十四岁。[13]
从上述几例华侨采取传统的、中国式结婚方式的事例可以看出,这些华侨都是经济上不很富裕的下层移民,他们不想花这份钱,或无力缴纳结婚税。但还是有不少华侨愿意采取正式登记注册结婚方式的,上述例子中有两例就是主动向公馆申请补办结婚证书的。
2.与赊税女婢结合
早期吧城的华人也有租借女婢作为妾室及家役之用的现象。如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十月五日即和1787年11月14日拜三公案记载,林听回唐(指唐山,即中国)时,将自己的婢妾及其所生的一个才4个月的女婴赊租给黄倦,租金为50文钱,并其幼女亦托为饲养。双方立下私契,规定此婢不得转卖他人,付其出身则可。这是一个吧城华人回唐山老家前将自己的小妾赊租给他人,到回吧时再取回的典型案例。[14]
又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三月廿二日即和1790年5月5日拜三公案记载:唐人游政经剃头司黎师介绍:向唐人姚东买一囝仔(指未出身的女婢),价钱是100文。囝仔说她原是赵准师的女婢,生有一女。准师在世时,将婢典卖给雅林甲,到了准师去世后,此女婢被转卖好几回,当她被卖给姚东时,姚东又将女婢出租给黎师,初时每月税银为2文2钹,后来姚东想提高女婢的税钱,黎师不敢再租,姚东欲婢攒钱赎身,婢以此敢出行四处攒钱,后来幸遇游政,欲为婢赎身,才向姚东议价承买。
从上述华侨租借当地女婢苟合的情况说明,当年吧城的部分华侨由于贫穷或其他原因,无力结婚成家,只好采用租借苟合的方式。吧城唐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可能已在家乡成婚,他们到吧城来只是为了赚钱回去养家,并无定居的打算,而他们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在吧城通过明媒正娶的途径娶得妻室,所以只好采取税租的方式聊慰寂寞。上述情形反映出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属贫穷阶层,在吧城生活维艰。
3.与未出身女婢结婚
早期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侨富有者,家中多有奴婢供家里使唤,或作为小妾,而在吧城的华侨也不例外。当时由于吧达维亚华民社会男女比例失调,华侨与女婢结合者为数不少,有的不经媒妁人而私合,有的则经媒人介绍两相结合。如: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十二月十二日和(荷兰)1789年1月7日拜三公案,郑兼与陈求翁婿间的经济纠纷案中,公堂劝郑兼曰:尔岳翁年老且贫,可拨多少钱付他济急如何?郑兼对曰:自顾不暇,焉有钱付我外父取去。列台又劝曰:不然可拨一女婢交他使唤如何?郑兼答曰:现有二婢,一颠一娠,有何可与?
上述表明郑兼与女婢私下苟合,且女婢已怀孕。当然,这不仅在早期的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有之,就是在男权社会的古代中国也常见到。又如: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三月廿九日即和1790年5月12日拜三公案,吴文标禀诉:前有一个妇人愿与文标结为夫妻,原议定,妻弃夫当备钱还夫,夫若弃妻亦当备钱还妻。及后与妻一起乘船往北加浪时,闻知拙妻乃是人之女婢,尚未出身。
由此可知这男女双方是自愿结合的。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三月廿二日即和1790年5月5日公案记载,刘器申诉,他托卢盒为媒,求雅韩厚(即与韩厚结合的当地女婢)之女结亲。蒙其许诺,手指(金戒指)办亦已送来为凭,及行订盟礼仪,却不纳反悔。雅韩厚说是小女诸亲戚不愿结亲。韩台说,韩厚弃世后其女由韩院(掌亚森新圩赌场)抚养,韩院不允刘器求亲,及韩院弃世,刘器又向女母求女结亲,其母私许允并无通知院嫂及诸亲戚,况女母尚是囝仔身,未有出身,焉得主意。而刘器乃有路无厝之人(即刘器乃属赤贫之辈,连房屋都没有,是以为韩家诸亲戚所嫌弃,不允结婚)。列台曰,女母尚未出身,虽有许亲,其言不足为凭,事可以已。又谕雅韩厚赠刘器大烛台一对,以坐赔不是。
从上述诸案例中我们可以得知早期吧城唐人与未出身的奴婢结合的一些情况。
4.与当地女子非正式登记结婚及入赘
据顾森《甲喇吧》一文记载,18世纪上半叶之前,吧城贸易市场上皆为妇人,荷兰殖民者以妇人计丁取赋,赋税很重。但是,如果女子嫁给唐人,则可免赋。因此,每当唐船到来时,常有老姐携幼女,艳妆求售者,所费甚廉,只是不许携眷归唐。华人娶了当地女子后,这些女子不仅勤于料理家务,而且还精于交易,赴市交易等事,俱能任理。这里记载了唐人与当地人通婚,但并没有详细记述女子来自哪里、为何种族,仅一般指为当地人。
而陈乃玉在《噶喇吧赋》一文中写道:此时吧城,十有七家,招夫赘婿,千而万鼎,酿蔗成糖。按此记载则有70%的唐人入赘女家,30%的女子入男家成婚,即大多数唐人是采取入赘方式结婚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就吧城郊区甘蔗种植园及市内一般劳工而言。南来的新客,多作苦力,收入不高,因而大多数只能因贫入赘女家。与吧城城内华侨多数都采用登记注册结婚形式的情况相反,吧城郊区的华侨则多数是没有登记结婚的。[15]
如上所述,早在18世纪初期,荷兰殖民政府就要求华侨采取正式登记注册结婚的方式。其目的之一是收取华侨的结婚税,且根据华侨结婚仪式的豪华程度的不同,规定出数目不等的收费细目。这种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华侨婚姻稳定的作用,使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尤其是在“一夫多妻”的婚姻形式下,在处置男方的身后遗产方面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18世纪初,荷兰殖民政府在吧城华侨中实行的“正式登记注册结婚制”,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