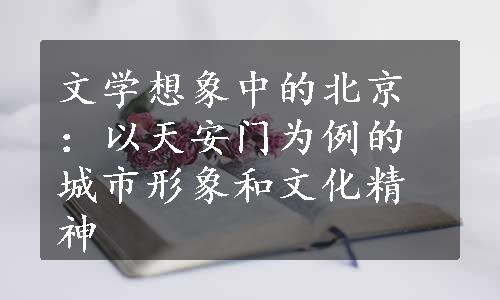
现代作家在体味北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经验并以文学的手段将之表现出来时,文学想象在这一将经验转化为文本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辞海》中“想象”一词的含义为:“对原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而形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人不仅能回忆起过去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即表象),而且还能想象出当前和过去从未感知过的事物的形象。但想象的内容总是来源于客观现实。一般可分为创造想象和再造想象两种,它们对人进行创造性活动和掌握新的知识经验起重要作用。”经由文学想象,北京的各种物理空间(建筑名胜、公园景区)和文化习俗(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在现代作家笔下不仅是其直接描写的对象,而且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塑造人物性格、表达作者复杂的情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现代作家描写的北京城市空间和文化习俗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21]从老北京的建筑名胜、四合院的格局意义等在文学中的描写,到情趣天然的具有乡土气息的城市风光,再到从口腹之欲上升到文化享乐的饮食习俗……老北京的风采神貌,早已跃然纸上,鲜活生动。故本文不再就此做重复的勾勒与描绘。此地笔者以被众多作家书写的天安门为例,探讨现代作家是如何将这些描写对象放进文学文本并塑造出新的城市形象和文化精神的。
明清两代,天安门及其宫廷广场外有一个封闭的“T”字形宫廷广场,又称“天街”,外设宫墙,属皇家禁地,是不许普通老百姓入内的。这个“T”字形广场两侧建有长廊供六部大臣公干。对于整个宫廷广场在建筑上的效果及其意识形态功用,侯仁之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整个宫廷广场,都保持着严格的轴线对称,周围绕以色彩浓郁的红墙,层层封闭。正中央是一条狭长而又笔直的石板大道,一直伸向天安门前。大道东西两边,傍红墙内侧,是联檐通脊的千步廊,一间一间地排列下去,显得有些矮小单调。但是对比之下,矗立在大道尽头横街对面的天安门,就显得格外雄伟、格外壮丽。其目的也是要通过建筑物的低小与高大、简单与豪华在形象上的对比,以及利用中心大道的纵长深远和大道尽头一带横街的平阔开展这种空间上的突然变化,来显示帝王之居的尊严华贵以及皇权统治的绝对权威。”[22]民国政府成立后,天安门广场逐步对外开放。普通百姓可以自由穿越长安街,或者自前门入中华门,沿着曾经的御道一直向前,一睹天安门的真面目。从那时候起天安门在现代作家笔下开始不断出现,石评梅、郑振铎、姚克、陈学昭、老舍等人在不同作品中都书写了天安门。[23]1937年北平陷落后,新民会为了向日本人邀功,胁迫中学生和小学生参加庆祝保定陷落的大游行,游行的路线基本上是从各个学校到天安门广场,然后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当时身处异地并未亲历此事件的老舍,后来在《四世同堂》这部巨著中通过文学想象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了别样的叙述,赋予了天安门新的文化精神。
游行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广场,老舍让作为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的物化形式的天安门见证了这场“严肃的、悲哀的、含泪的大游行”。此时的“北平,那刚刚一降生似乎就已衰老,而在灭亡的时候反倒显着更漂亮的北平”,在这样的日子也显示出它的与众不同。老舍借为谋私利屈膝日本侵略者的瑞丰的想象与视角描写了当时天安门的场景:
他预料着,会场周围必定象开庙会一样的热闹,一群群卖糖食和水果的小贩,一群群的红男绿女,必定沿着四面的红墙,里三层外三层的呼喊,拥挤,来回的乱动;在稍远的地方甚至有照西湖景和变戏法的,敲打着简单而有吸引力的锣鼓。……可是眼前的实在景物与他所期望看到的简直完全不同。天安门的,太庙的,与社稷坛的红墙,红墙前的玉石栏杆,红墙后的墨绿的老松,都是那么雄美庄严,仿佛来到此处的晴美的阳光都没法不收敛起一些光芒,好使整个的画面显出肃静。这里不允许吵闹与轻佻……瑞丰看不到热闹,而只感到由城墙,红墙,和玉石出来一股子什么沉重的空气,压在他的小细脖颈;他只好低下头去。……
慢慢的,从东,西,南,三面都来了些学生。没有军鼓军号,没有任何声响,一对对的就那么默默的,无可如何的,走来,立住。……学生越来越多了。人虽多,可是仍旧填不满天安门前的广场。人越多,那深红的墙与高大的城楼仿佛也越红越高,镇压下去人的声势。人,旗帜,仿佛不过是一些毫无分量的毛羽。而天安门是一座庄严美丽的山。[24]
显然此时作为民族尊严和民族精神象征的天安门,被作者放大了它特有的庄严尊傲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感染着游行的人,使他们羞愧、沉默,并以沉默来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侮辱。老舍先生把这场游行描写成一场“滑稽剧”——天安门的高大反衬着侵略者及其帮凶的渺小,天安门的庄重肃穆使他们显得愚顽可笑。日本军官的宣讲“好像一个猴向峨眉山示威”,“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25]。傲然不屈、沉默不语的天安门此时已着上了这个民族高贵不屈的气质,它使“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26]。不屈的天安门使异族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一次精神侮辱变成了一场闹剧,在老舍笔下它提供了一种强大的为这个民族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在《四世同堂》第八十三章,老舍通过祁瑞全的目光和思索道出了北京城(以天安门为缩影)的精神内涵对人的影响。(www.zuozong.com)
一看见天安门雄伟的门楼,两旁的朱壁,与前面的玉石栏杆和华表,瑞全的心忽然跳得快了。伟大的建筑是历史、地理、社会与艺术综合起来的纪念碑。它没有声音,没有文字,而使人受感动,感动得要落泪。况且,这历史,这地理,这社会与艺术,是属于天安门,也属于他的。他似乎看见自己的胞衣就在那城楼下埋着呢。这是历史地理等等的综合的建筑,也是他的母亲,活了几百年,而且或者永远不会死的母亲。
北京既是养育这方子女的母亲,也是培养传承民族精神气质的母亲,这是老舍的发现,也是现代作家们共同的精神思索。
北京在现实生活中独特的城市风貌,不仅在文学中重新彰显或被赋予某种新的精神气质,在文学叙事中也为故事情节的展开提供了相宜的舞台。
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主要讲述了民国总理之子金燕西与平民之女冷清秋之间的爱恨纠葛。作者把二人情感发展的每一关键情节都放在了各处公园里展开。去颐和园的途中两人初遇,金燕西为冷清秋的素雅之美倾倒,随即开始了追求。香山之行,两人感情渐渐深厚,情定于此。后去西山,因时日耽搁留宿山中,成夫妻之实,清秋有孕后两人成婚。后来两人情感不和分手,金燕西在西山路上错过了骑驴而过的冷清秋,从此二人再无缘相见。最后只剩金燕西的妹妹梅丽与情郎谢玉树同游颐和园时追忆燕西和清秋的情感故事。张恨水对颐和园、香山、西山的风景描写恰合了当时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是既写景又写情的妙笔。与张恨水类似,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也有这样的构思。《京华烟云》第十三章,姚木兰一家至西山别墅郊游。姚木兰巧遇了在白云观时就曾关注过的孔立夫。同样寄情山林风光与废墟之美的趣味使两人相知相熟。后来的什刹海看洪水,同游泰山以及圆明园的废墟之约,都为木兰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即使两人的感情并未结出果实,但木兰“深深体会到,只要和立夫在一起,她就会永远幸福,永远满足”[27],即使这种幸福只能通过同游山水的方式来实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语堂是残忍的,他想象书写的人物命运里木兰没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但他同时也是慈悲的,他让那些美好的园林山水成为姚木兰一生的幸福回忆。
老北京有着纷繁复杂但又极具人情之美的繁复礼仪和日常生活习俗,在现代作家的文学想象中,对习俗、礼仪的描写在丰富着人物形象的同时也表达着作者的情感体验。《四世同堂》中,祁老人的七十五和八十寿日,尽管处于战争的阴影下,还是如期度过。因为“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这两次寿日过得异常艰辛,既是生活条件的艰苦,也是祁家人心理挣扎的痛苦。瑞宣为在亡国时期做这样的庆祝而内心深处充满悲苦,但是由于长孙的地位又不能不如此。从对七十五岁寿日的心存渴望到八十寿辰的寒苦悲愤,祁老太爷从冥顽不灵的固守中走出,体验到了国毁家亡的痛苦。而韵梅则为了一家人生活的和睦,为顾及礼仪伦理的要求,尽量维持着无米之炊,体现了她善良、勤劳、耐苦的女性品质。祁老人的生日是八月十三,与中国传统佳节中秋紧邻。《四世同堂》第十四章,老舍用抒情意味极其浓厚的笔调,追忆往年中秋前后最美的北平:飘香四溢的水果摊,裹着细沙与糖蜜的肥大炒栗子,做工精细、粉面彩身的兔儿爷,来自丰台花样繁多的秋菊……同时老舍以上街排遣内心烦闷的祁老人为视角,描写了日寇占领下北平中秋前的状况:没有瓜果香,街道冷清,月饼稀少,只有孤立的兔儿爷摊子……节日在饥寒交迫而将走上死亡之路的人们心中已不占重要地位。祁老人的眼睛流出眼泪,“现在他看明白,日本已经不许他过节过生日!”[28]祁老人一家以富善先生赠送的白面做寿桃,过了祁老人的生日和中秋。此时祁老人似乎已经觉醒,他知道所有的灾难“全是他们闹的!日本人就是人间的祸害星!”在节日礼仪润饰下的日常生活被破坏时,祁老人也渐渐开始认清现实并由中庸保守逐渐走向抗议和激烈。
“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象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29]老北京的城与人在这种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习俗与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的确具有中庸、保守、怯懦等缺点,但是当它自身受到压迫面临死亡时,它的城与表现它精神的人,就会形成对抗的力量以求自身的生存和出路。以老舍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借文学想象的方式,在对老北京独特的城市风貌和繁复驳杂的风俗礼仪的书写中表达了上述思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