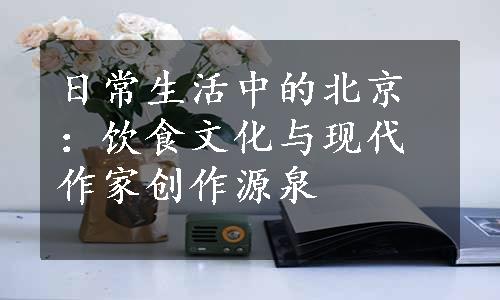
在对北京进行精神观照时,日常生活经验毫无疑问为现代作家想象并书写北京提供了创作源泉。“民以食为天”,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多种多样的饮食及其所包含的饮食文化,为现代作家所津津乐道,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作品。追忆北京菜的发展渊源,记忆老北京美味可口、花样繁多的风味小吃,并借此书写饮食文化中所包含的文化享乐精神和审美情趣,是大多数现代作家的共同追求。本节以现代作家笔下老北京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及其文化为中心,探讨日常经验在现代作家书写“文学中的北京”时的影响和作用。
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北京多少世纪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八方人士荟萃之地。深厚的历史背景,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百年来山东菜、宫廷菜、川菜等不同菜系在北京的流行,使北京菜包括其特色小吃逐渐形成[9],并产生了一大批名扬京城的老字号,如东兴楼、泰丰楼、同和居、致美斋、丰泽园、砂锅居、东来顺、烤肉宛、烤肉季、全聚德等。这些老字号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丰富着北京人的饮食生活,在文学作品中也常常作为素材被现代作家使用。《老张的哲学》中,老张、孙八、南飞生、龙树古等人在九和居做“立于健全的胃口之上”的美满交际。老舍凭借对九和居的夸张描写以及对“宴饮五关”的调侃,刻画了老张等人的丑陋群像。同样在《赵子曰》中,金来凤回回馆、致美楼、东安楼等老字号名店成为赵子曰等人聚众宴饮的场所,口腹之欲的满足尽显了他们的无聊与浅薄。当然老舍文化批判的意图很明显,故此金来凤、东安楼、致美斋、九和居等在老舍笔下没能得到正面的描写,以尽显它们的风采。
事实上,这些老字号无论在食品的制造,还是自身文化精神的铸造与传承上确有过人之处,例如全聚德。全聚德如今已是驰名中外的北京美食的代表,而它的复杂菜式则由最初的“挂炉烤鸭”而来。同治三年(1864年),杨寿山由“便宜坊”的“焖炉烤鸭”得到启发,开始了“挂炉烤鸭”的实验。“挂炉烤鸭”成功后,全聚德逐渐扩大门面,增加了白案、红案、主食、炒菜等,1910年正式升级为饭店。然而全聚德不满足现状,反复研究探索,后来创设出了“鸭全席”,拥有了自己的菜系,成为“地道的北京菜”。不断革新的传统是其最终获得成功的强大动力。[10]全聚德的成功显示着北京“荟萃八方”“吐故纳新”的文化精神[11],“但要真正了解北京饮食文化的历史和基本精神,还得从体现北京饮食文化主要特征的北京小吃说起”[12]。
徐霞村在《北平的巷头小吃》中认为:“北平为三百年来满洲旗人聚居之地,当日一般养尊处优的小贵族整日游手好闲,除了犬马声色之外,惟有靠吃零食来消磨他们的时光,因此北平各胡同里售卖零食的小贩之多,也为国内任何城市所难望其项背。”[13]接下来,徐霞村详述了豆汁、灌肠、切糕、扒糕、凉粉、炸豆腐、烤白薯、大米粥、糖葫芦、豌豆黄、艾窝窝、凉糕、酪、酸梅汤、硬面饽饽等小吃。无独有偶,梁实秋也曾做《北平的零食小贩》一文,追忆他生活在北平时见识到的各种小吃以及零食小贩的叫卖声,生动地描摹了“北京人馋”的特征。[14](www.zuozong.com)
然而北京人的饮食文化并不在于吃食的丰富与精美,而是在吃的韵味。周作人曾在《北京的茶食》一文中,因北京没有好的茶食而心存遗憾。他说:“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这与“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一样,“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15]。周作人将茶食与看夕阳、听雨并置一处,显然是把这一日常生活经验审美化了。吃——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只是生理所需,而是透着以“玩乐”为基本内涵的怡人心性的心理行为。所以老舍《正红旗下》里的姑母即便在家道衰落后仍不忘讲究吃喝;张恨水《夜深沉》中生活贫苦的丁二和与杨月容能在烤白薯、烙韭菜盒子里找到生活的乐趣。易中天认为:“北京平民的生活大多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简陋,但却决不会因为贫穷而失去了身份,丢了体面。即使不过一碗老豆腐,二两烧刀子,也会慢慢地喝,细细地品,一点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气度,那派头,有如面对一桌满汉全席……要之,他们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饮酒喝茶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16]与平民的生活相似,豪门贵胄、富裕之家的饮食生活也透着浓浓的生活情趣。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里,吃食和宴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十六章,姚木兰与孔立夫以及父亲等人去什刹海看水、品茗、吃鲜嫩的莲子,木兰和立夫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并有了之后的“圆明园之约”;紧接着的中秋螃蟹宴上,吃着美味的螃蟹,探讨孔夫子是否爱吃螃蟹的“典故”,讲与螃蟹有关的笑话和绕口令,为节日增加了欢乐的气氛,给整个宴饮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17]
从为北京菜正名的各种老字号,到街头巷尾零食小贩供应的各种小吃,再到高门巨富大宅门里的各种家庭宴饮,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已变成一种悠然自得、怡人心性的文化精神的载体。无论是追求“食有名品”的老字号,还是喜爱遍及街巷的风味小吃,“选择独具文化感的食物便是选择更为精致的生活情趣与更高的精神文化境界”[18]。在北京,无论平民百姓还是豪门贵族莫不如此,这一现象背后承载的是北京文化的贵族气派[19],是对生活情趣与文化精神的追逐。现代作家在选择描写对象时,本身也透露出自身的喜好与趣味,他们笔下的文字与人物的趣味就是最好的证明。
以饮食文化为中心,现代作家书写着北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平民精神和贵族趣味,既生动地描摹展示了日常经验中的老北京生活,又透露出在这种日常经验中形成的作家本身的经验和趣味。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城与人的双向互动——“他们创造了‘艺术的北京’,自身又或多或少是北京的创造物;在以其精神产品贡献于北京文化的同时,他们本人也成为了这文化的一部分”[2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常经验中的北京对现代作家书写并想象文学中的北京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