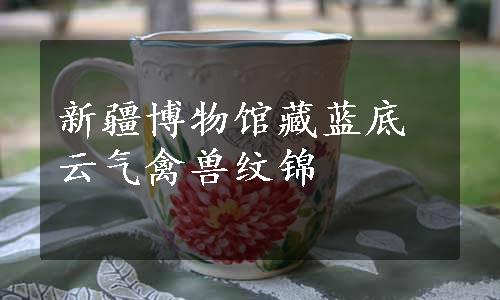
陈新勇[1]
摘 要:蓝底云气禽兽纹锦,织锦上的动物禽鸟与《山海经》中所载瑞兽神物惊人相似:八个神兽和一个跪拜妇人两两穿插在变体云气山峦纹之间,分别向四周重复地连续和延伸扩展而形成的纹样。
关键词:新疆博物馆;蓝底云气禽兽纹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一件汉代鸟兽纹锦鸡鸣枕,也称蓝地动物纹锦枕,1984年山普拉出土。展开后通长67厘米,织锦长25厘米,宽25厘米,翼宽8.2厘米[2]。国家二级文物(图1)。
图1 汉代鸟兽纹锦鸡鸣枕展开图
笔者对这件汉代织锦仔细观察分析,发现这件织锦上的动物禽鸟与《山海经》中所载瑞兽神物惊人相似,蓝底云气禽兽纹锦(图2)采用二方连续构图形式,因左侧留有副边,顾自左至右分析,图案自左至右有四个云气山峦作为分割,每个山峦云气间穿插两个瑞兽,1单元由于紧靠幅边只有一个瑞兽单分为一组、2-3单元为一组、4-5单元为一组、6-7单元为一组、8单元为人物、9单元为瑞兽。
图2 蓝底云气禽兽纹锦局布纹锦
1单元组:此形象靠近幅边,自上而下成“S”形蛇状,蛇状“S”形右上角有一小块“工”形纹样,在其他单元不见,因右侧紧靠云气山峦,故1单元仅此一神兽。上古时期似蛇的神兽经过对比后,蝮虫与之较为相似。虫为虺的本字,腹虫即蝮蛇,出自《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南山经〉),第三篇《猿翼之山》“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猿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多白玉,多蝮虫,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3]
2-3单元组:
2单元:观其形象似鸡,大圆眼,长喙,矮小站立状,双足各分出两趾,其尾巴雄壮向下弯曲拖地,向右朝向。
形象与上古神兽重明鸟描述极为相似。重明鸟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形似鸡,但是叫声像凤凰一样,据说它能够驱除猛兽和妖物。新年时家家户户将鸡贴在门窗上,也是取了重明鸟驱除妖邪的寓意。在《拾遗记》中说:“尧在位七十年,有积支之国,献明鸟,一双明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解落毛羽,用肉翅而飞。能抟逐兽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或一年来数次,或数年都不来。国人都全洒扫门户,以留重明。如重明鸟未到的时候,国人或刻木,或造铜像,为此鸟的形象,放在明户之间,则魑魅之类,自然退伏。”所以到了现在,都刻木像、造铜像或画图像,或画鸡于门上。
3单元:观其形象似虎,身体健壮匀称,身体上有表示斑点的四个同心圆。四足作奔跑状,双目圆睁,嘴巴大张,头顶有一向后弯曲的犄角。
形象与上古神兽獬豸描述极为相似。獬豸也称解廌或解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上古神兽,古代神判与神裁思想下产生的著名神兽,据说獬豸能够听懂人言,能够分辨是非,所以也被为勇敢、公正的象征,又被称为“法兽”。根据《论衡》和《淮南子·修务篇》的说法,它身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长相与麒麟相似,额上有一个角,酷似如今的“独角兽”形象,据传角断者即死,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发,双目明亮有神。
4-5单元组:
4单元:观其形象较为短小成匍匐蠕动状,似仅有一足爪,且足爪上有三个锋利无比的指甲向后弯曲。足爪与身体头部连为一体,头大,双目圆睁,高鼻梁、嘴巴做呲牙状,头顶与脊背皆有向上的鬃毛。身体朝向右方。
形象与上古神兽狸力描述极为相似。狸力,《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南山经〉:“柜山,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4]是柜山上的瑞兽,狸力出现的地方,正在大兴土木。见到它的地方,地面多起伏,所以猜测狸力善于挖土。
5单元:观其形象似虎豹,身体上有五个表示斑纹的同心圆,四足成奔跑状,豹头短耳,双目圆睁,嘴做吼叫状,头顶有向上的鬃毛,短尾拱起,末端向下分散似牛尾。
形象与上古神兽彘描述极为相似。彘,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
6单元:似站立的人形兽,猴头,长臂双举起,身上有下垂的长毛,双腿成半蹲状,身体朝向右方。
形象与上古神兽狌描述极为相似。狌,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食之善走。狌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异兽,记载于《山海经》,形似猿猴。《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海内南经〉)[5]:“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狌”狌是神奇的野兽,形状像长毛猿,长有一对白耳,既能匍匐,也能直立行走,传说它通晓过去的事情,但是却无法知道未来的事情。据说吃了狌的肉,有健步的作用。《荀子·非相》:“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无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肉。”
7单元:观其形似鸡状、形体大方,双足站立,头顶部有冠羽,大尾羽毛上扬向后飘逸,有一表示斑纹的同心圆。
形象与上古神兽凤凰描述极为相似。凤凰共有五种,即五凤,《小学绀珠》卷十:“凤象者五,五色而赤者凤;黄者鹓鶵;青者鸾;紫者鸑鷟,白者鸿鹄”,《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6]《渊鉴类函》引徐整《正律》中有一条极可注意的记载:“黄帝时代以凤为鸡。”此一记载有一定的可信性,可能正是在此时,鸡成为凤凰的主要替身之一。汉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形成时期,凤文化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较大发展。在汉代各种工艺品和建筑装饰上,自然界的鸟几乎都用作图案题材,如鹤、孔雀、锦鸡、喜鹊、鹭、鹳,等等。但是,最鲜明而富有时代特征的是凤凰一类神化的瑞鸟纹样。这些传说中能给人们带来祥瑞和兆庆的神鸟,在装饰物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凤鸟形体大方,挺胸展翅,高视阔步,气宇轩昂。汉代的凤鸟图案,充分流露出形象的动态与气势,处处表现出整体的容量感、线形的速度,以及变化的力量。
8单元:观其形是一跪坐的妇人,着汉服,最典型的是“交领右衽”,就是衣领直接与衣襟相连,衣襟在胸前相交叉,左侧的衣襟压住右侧的衣襟,在外观上表现为“y”字形,褒衣广袖,袖宽且长,发髻高耸,成双手抱于胸前成跪拜状,似在向9单元神兽跪拜求饶。在汉代女子对于发饰的装扮是力求多样的,因为汉王朝的政治进步、经济繁荣,再加上与外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流,社会风尚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宫廷贵族的发式妆饰则更是奢侈、华丽。汉朝女子大多是让额头前的发饰隆起,露出额头来,然后平分成髻,梳于脑后。最为特色的是,她们的发髻都高耸于脑门之上,有的头发不够长,就用假发来接,高髻只是少数贵族女子使用的一种发式。
9单元:观其形仅残存多半纹样,大头大耳圆眼阔鼻、血盆大口满嘴獠牙,头上有三角形一排犄角,脊背上长满鬃毛,头与身体连接一体,卷曲的足爪,足爪分出三趾长甲向下后抓。蜷曲的身体上有表示斑纹的五个同心圆。
形象与上古神兽饕餮描述极为相似。饕餮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秘怪兽。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相传为上古四大凶兽之一,《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吕氏春秋·恃君》:“雁门之北,鹰隼、所鷙、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
《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北山经〉)[7]介绍其特点是:羊身,眼睛在腋下,虎齿人爪,有一个大头和一张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就吃什么,由于吃得太多,最后被撑死。后来形容贪婪之人叫“饕餮”。
新疆考古发现的织有兽头纹的锦、绮实物数量不少。兽头纹在绮和锦上常与其他纹样一起出现,有时也是云气动物纹中一种特殊的动物纹。兽头纹样作为丝绸图案题材,早在殷商时期的刺绣品上就已出现了,它和同时期青铜礼器上流行的饕餮纹有密切的关系。(www.zuozong.com)
1995年尉犁县营盘墓地YYM15∶5一件白色菱格动物兽面纹绮现藏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白色,组织结构为典型的汉式组织,平纹地上以3∶1隔经显花。图案为菱形框架内依次排列兽面、对兽、对鸟、对兽、菱格几何纹等。菱格动物兽面纹绮图案复原,最右边大头鬃毛竖立,大嘴獠牙者应是饕餮(图3)。
图3 菱格动物兽面纹绮图案复原
菱格动物纹绮,斯坦因楼兰墓葬出土,其兽头形象及排列已接近魏晋风格,王磊义先生编绘的《汉代图案选》中称之为豹首纹锦[8](图4)。
尉犁县营盘墓地M39号墓出土一件汉文和佉卢文双语禽兽纹锦,日本学者释读佉卢文为“悉”,汉文为“王”。动物的图案是狮子,这样纹样文字织锦的设计、生产,受时在京质子、胡商胡人使团等的影响,织出“王”字,昭示其某种地位和身份,因此,这类文字织锦应是在京朝贡的西域绿洲城邦国家王族或在京西域子侄们请求织室或服官役吏,按照他们的审美、功利等意愿,设计生产。”这件织锦上的动物应该是饕餮。(图5)
图4 斯坦因楼兰发现对菱格动物纹绮
图5 尉犁县营盘墓地M39号墓出土一件汉文和佉卢文双语禽兽纹锦
楼兰墓出土对禽、对兽兽头纹绮的兽头也是填充在杯形骨架中。斯坦因在楼兰发现两件兽头纹锦:一件锦上兽头和连枝灯、虎、龙等纹样横向并列贯通幅;另一件锦上的兽头居中,两旁各有体态较小的豹纹(图6)。
图6 楼兰出土对禽、对兽纹绮
值得提到的是魏晋南北朝初期,在新疆地区生产的平纹纬锦上也见有兽头纹,它虽然是模仿汉锦兽头纹样,也伸出双爪,但面目更接近人的面貌。1972年阿斯塔那古墓TAM170∶60红地人面鸟兽纹锦(图7),这件织锦里面的“人面”形象,估计描述有误,其实也是饕餮形象,构图延续了汉代织锦中饕餮的形象,头部鬃毛竖立,圆眼,双爪两侧,只是趋于装饰意味,不是血盆大口、瞠目獠牙那般凶猛。
图7 红地人面鸟兽纹锦(王乐复原提供)
汉代的图画是汉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画像砖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可以分为神仙世界、墓主人生活和驱鬼镇墓三大系统,被大量运用在丝绸、彩陶、漆器、建筑及墓壁上,反映瑞兽、瑞禽形象的不少,饕餮形象千变万化,流传延续时间较长,风格迥异(图8)。
小结:此件蓝底云气禽兽纹锦(图9),纹样设计巧妙,神兽神态逼真,八个神兽和一个跪拜妇人两两穿插在变体云气山峦纹之间,分别向四周重复地连续和延伸扩展而形成的纹样。左边有幅边应该是起点,右侧到饕餮处仅存饕餮一半纹样。综上所述几处出土织物及画像砖饕餮形象,推理如图像完整,应右侧还有一爪,应该还有其他神兽组合。古人将妇人和诸多神兽组合排列,肯定有其用意,《山海经》中兽描述,上古华夏神州,万物皆有灵性,在广瀚的三界之中,出没着一些极富灵性的神兽。它们长有各种奇异的外形,并且有着不为人知的神奇力量。
图8 汉代画像砖上的饕餮纹饰 西晋时期画像砖上的饕餮纹饰
图9 蓝底云气禽兽纹锦复原图
从上述新疆出土的一些类似神兽纹锦大致可以看出:越早织锦越复杂精细,汉代时神兽纹样不但表现得动态、神态相当具象,就连各自的性格是凶是温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晋唐时期,神兽图案趋于简化概括和抽象,构图几何化,用色也活泼跳跃。
中国古代神话风起于周,拓展完成在汉,汉虽有前后两分,但一脉相承,其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情怀,经过政治纲纪,达到完善。汉代的神话证明:在古代神话不仅仅是表象的历史神话化或神话历史化的产物,传说的积累扩展或者对自然力的想象,更深层的是建元开国、治国理政的战略实践和具有宗教精神的资源力量的适用。
【注释】
[1]作者单位:新疆博物馆,乌鲁木齐830091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新疆山普拉——古代于阗文明的揭示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3]王学典:《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南山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4]王学典:《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南山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5]王学典:《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海内南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页。
[6]王学典:《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南山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7]王学典:《山海经全鉴赏》(注译卷一〈北山经〉),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8]王磊义:《汉代图案选》,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