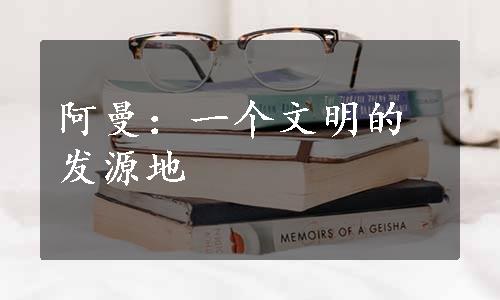
春末,我在阿曼湾旁,与友人苏莱曼·康嘉里一同在苏哈尔堡(Sohar Fort)附近散步。我走向堡垒苍白的灰泥墙。高耸的墙面几乎与一旁的枣椰树一样高,几个世纪以来,不断以灰泥涂涂抹抹。那天艳阳高照,天气炎热,海面与雪白墙面的强烈反光让我差点睁不开眼。
苏莱曼肯定发现我眼睛眯起,遂呼唤我过去。我走下卵石阶梯,准备到他所在的城墙阴影下。墙面爬满深绿色的九重葛藤蔓,点缀鲜红的花朵。我跟他躲进阴影,发现前方有一圈低矮的石墙,石墙围绕着地面洞穴。我眼睛适应暗处之后,旋即睁大眼,环顾四下。
有群人围着一名阿拉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正比画手脚,指着那处围起的坑洞,向学生解释这是过去考古挖掘之处。“过去听听看吧,”苏莱曼轻轻对我说,“我会尽量把他讲的话翻译给你听。”我靠过去,庆幸能躲在阴影中。
“阿曼湾是古代航海的摇篮,苏哈尔是航海家最早起航的港口之一……港口以石墙包围,距离城堡还有200码[1],可惜已被风暴摧毁。到了10世纪,穆斯林地理学家伊斯泰赫里(al-Istakhri)称这里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海港’。这是阿拉伯半岛东岸上,最大、最富有的交易枢纽。我们现在所在之处是由13或14世纪初的霍尔木兹人建造,目的是安置军人,保护如今已被摧毁的港口。但更早之前的纳卜汉尼王朝,这个港口是用来交易铜与香料的,以换取造船的木头。”
“纳卜汉尼王朝?”我问。
“12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你的祖先纳卜汉尼家族控制了这座港口,成为区域统治者。当然,在他们称霸之前,这个地方已有贸易活动了,甚至在兴建第一座堡垒之前就有了,大约是1世纪。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早在公元前3000年,这一带可能就有航海人出没,他们最初只让船只在海岸附近停留。关于这处海岸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阿比辛国王(King Abi Sin,公元前2029到前2026年在位)的时代。根据记载,来自马干(阿曼)的铜与熏香,人们会用来换取美索不达米亚的木材及印度的香料。后来,海上贸易拓展,跨越海湾、大海与大洋。堡垒持续兴建,在我们正下方的最底层曾发现中国瓷器,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几个世纪以来,用这座港口的不只有阿拉伯商人,还有犹太商人。事实上,我们认为穆斯林的名字最初可能是犹太人的,后来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之后才稍微改变。
“不过那时的阿曼人和现在一样,不安于现状。”
苏莱曼微笑着,显然翻译到一半,他就开始提出自己的见解:“我的家族源自于东非,好几千年来,阿曼人曾到东非与桑给巴尔人买卖香料。其他人例如你的纳卜汉尼祖先则居住在肯尼亚外海的拉穆群岛。阿曼人过去曾在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建立殖民地,或许还包括马达加斯加岛。没错,许多人都是香料商人。”
“乳香交易是在阿曼北边的港口,还是在南边佐法尔省的巴里?”
图8:古阿曼交易中心的废墟,位于绿山高原下的沙漠,令人感叹几个世纪以来的贸易之路多么变化多端。(图片来源:作者)
如果查古地图,会发现有几条内陆的交易之路从乳香产地一直延伸到现在的阿曼北部。大家都以为乳香之路是从也门的萨那(Sanaa)与马格里布,往北经过麦加与雅什里布,抵达佩特拉,之后再通往耶路撒冷或亚历山大。不过,商队还有许多其他路线可走,有些还穿越鲁卜哈利的荒凉区域。眼前的这条路是稍微偏半岛东岸的路线,从佐法尔延伸到马斯喀特与尼兹瓦(我不太确定究竟通到哪里),之后又通往伊卜里(Ibri)与雅布林(Yabrin),再到巴士拉与巴格达。
“但我不认为这条路会一直沿着海岸前进,否则商人会被海盗盯上。我反而认为这条路会隐藏在内陆,这样才能把货物藏在有防护的绿洲,例如巴赫拉。之后,等他们准备好把货物送到海上时,无论是铜、皮革或霍杰利乳香,皆以商队送到苏哈尔等港口。”
我闭上眼睛,设法理解这一切。航海的亲戚、内陆的隐秘通道、非洲外海的祖先。我对自己的血脉认识这么少,着实难为情。
虽然阿曼的马干王国有土生土长的闪族部落,有些还信仰早期的犹太教,不过这里还住着其他闪族部落,多半是来自也门的移民。这些也门闪族中,有些是3世纪下半叶阿德汉纳谷的马格里布水坝溃堤后而北迁的人。
或许我的纳卜汉尼祖先也曾颠沛流离,先逃到绿山高地,远离容易泛滥的地面,那是阿拉伯人能抵达的最远之处。若认为他们是自愿离开也门,恐怕太过天真,毕竟游牧的畜牧者与香料采集者、商人与绿洲农夫之间的平衡,突然间颠覆且无法挽回,迫使许多部落必须同时逃离。每当自然或政治局势出现变化,游牧的采集者与畜牧者,与定居的务农部落之间松散的共生关系会受到压力,而在人口组成发生巨变时,创新与不平常的事物也会跟着出现。
马格里布水坝在3世纪时坍塌,导致许多阿拉伯原住民部落前往中东其他地区,甚至寻找新的职业。难民包括游牧畜牧者及偏向定居的哈德尔族,后者曾在较广大的灌溉绿洲中从事农耕,例如马格里布阿德汉纳谷一带出现的农业中心。灌溉农业会在中东及更广的世界普及,多多少少是因为这些出走的哈德尔族。他们在过去的4000年中,持续提升用运河灌溉农作物的技巧。
这些人永远离开也门老家之后,显然持续迁移,且不局限于在陆地上活动。他们精通航海之道后,便踏入更辽阔的世界,鲜少回到祖国。阿曼的港口俨然是他们的跳板,香料运输成为他们最常见的职业。
腓尼基人在红海与地中海地区学习到了卓越的航海技巧,之后才往更远的地方发展,而阿拉伯航海者则从巴士拉港离开阿曼与波斯,最初多在波斯湾与印度洋活动,之后又前往好望角。当然,古吉拉特、印度与锡兰水手早已在这一带水域航行,他们开展贸易已有好几个世纪,而阿拉伯人也以那些民族的航海经验为基础,发明新的航海技术,包括观察48颗星星移动的方式、在海岸边安置成千上万的地标,并利用季节风向的转换来跨越海洋,或沿着岸边航行。他们在非洲与亚洲建立起常设休息站与香料仓库,功能像以前阿拉伯沙漠的商队旅馆。
阿拉伯水手在沿岸港口见识到某些香料后,发现这些香料远比沙漠的野生种类要丰富珍贵。虽然在阿拉伯半岛沙漠生长的香料品种效果无疑很强,但和印度、斯里兰卡、摩鹿加群岛、中国、桑给巴尔或马达加斯加岛的一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这些烹饪原料逐渐改变游牧民族较为简单的菜肴,使之演变成今天众所周知的中东菜肴,例如:羊肉串(laham mishwi)是把加了香料的羊肉或山羊肉,以签子穿起后在柴火上烤;枣子酱(hays)则是把枣子、凝乳与印度酥油混合而成;塔里德(tharīd)是把无酵面包放进简单美味的炖肉;肉汤(khazira)则是加了麸皮与香草的清肉汤;麦粥(sariq)是用大麦、小麦或二粒小麦煮成的粥。
多亏亚洲与非洲的进口货物,这些菜色在烹调时能加入新的香草与香料,用蜂蜜与蔗糖赋予甜味,并淋上酸柑与泰式青柠的酸果汁。此外,来自其他国度的丰富食物被认为是奢侈的异国品,和阿曼做生意的人莫不目眩神迷。这些食物在希腊、罗马、美索不达米亚与托勒密帝国政治经济中心都要价不菲。雅典、罗马、亚历山大、利格斯(Lygos,即后来的拜占庭)与巴比伦的权贵,根本难以抵抗强烈的香气与滋味诱惑,他们用这些时髦的进口货来炫富,以提升地位。如今我们很难想象,游牧者的临时帐篷或农民的小村庄如何能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满足城市国家对奢侈品与新奇玩意的需求。
由于定居生活形态的人总有难以满足的欲望,这让阿曼航海家获得了继续往外探险的动力,他们学习外国语言,设法直接与香料生产者交涉,并把航海与备粮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么一来,阿曼水手即可在海上度过好几个月,不怕坏血病或台风袭击。到了公元前100年(或许更早得多),他们已常通过在马拉巴尔海岸、马来西亚或摩鹿加群岛的中介,收购中国商品,甚至亲自跟中国人买。中国人在北部湾(Gulf of Tonkin)附近初次碰到他们时,分不出是波斯还是阿拉伯船只,一律称他们为“商胡”,意思是“外国商人”。黑胡椒与白胡椒、中国肉桂与锡兰肉桂、肉豆蔻仁与肉豆蔻皮(mace)、八角与丁香都到了他们手中,他们再收藏起来。他们取得香料的地理范围扩张到已知世界的最远之处。
当然,到了这时候,各种熏香已不是“当红”产品线,更无法左右商路的确切路线。亚洲的丝、麝香与药草等产品变得无比珍贵。这些东西循着陆路,从中亚由骆驼运送到印度南方或西方港口。
阿曼的阿拉伯人甚至腓尼基人,过去曾靠着骆驼商队深入偏荒,取得香料产品,但从物流与成本等因素来看,货物以海运送到更远之处则便利多了。船只越造越大、越稳固、速度越快,但商队根本无法光靠着增加每头驮兽的载重量,或用更多驴子、骡子、马匹、骆驼甚至大象与船队匹敌。然而,驮兽并未遭到淘汰。时至今天,市面上仍有称为“骆驼茶包”的沱茶。沱茶长时间放在骆驼背上穿越沙漠,这也赋予茶叶独特的气味。
有些人可能好奇,在历史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最初究竟是循着陆路还是海路抵达中国?这个问题看来没有太大意义。许多早期(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前)的阿曼商人,在一趟旅程中可能兼采海陆两种方式,亚洲人也是如此。这些贸易工作者可能包括信仰犹太教雏形的阿拉伯人,有些人仍信仰多种神祇,或通过萨满巫师来接触精灵。
在那时,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这两个词并非互斥的两个类别,因为不同的闪族群体(包括迦南人),显然都成了摩西的追随者(各语言中可能称为“Moses”“Moshe”或“Musa”)。这位先知率领众人离开埃及,前往西奈,在西奈获得神的指示。犹太水手与商人仍与阿拉伯群体融合了好几个世纪。在伊斯兰教发展之后,他们与早期的基督教徒与萨比教徒变成“齐米”(dhimmi)或是“有经者”[2]。齐米人必须缴税给穆斯林主人,才能换取居住权与保护,可实行某些穆斯林社群禁止的仪式。“齐米”的特殊地位,让双方在共同的历史中彼此支持包容,直到17世纪时世俗主义兴起才出现变化。
我在阿曼时,曾造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一处博物馆,主题是乳香的贸易史。我惊喜地发现一份古代手稿的副本,那是阿曼香料商来到东方的最早文字记录之一。他当然不是第一个和中国交易的阿拉伯商人,因为双方早在他出生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已有往来。但这个人在公元750年到了中国,并把经验写下来,足足比马可·波罗的精彩口述早了500年,何况马可·波罗不识字,是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帮他写下的。
这位相当于也门马可·波罗的英雄,叫欧贝达·宾·阿布杜拉·宾·卡希姆(Obeida bin Abdulla bin al-Qasim),在阿拉伯世界从来都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西方世界更是默默无闻。阿拉伯人并非不好意思纪念他们的英雄与先驱,而是阿拉伯学者知道,比欧洲人更早抵达中国的商人成千上万,欧贝达只是其中一个。博物馆特别将他列出,是因为他用阿拉伯文对早期中国的记录保存得很完整。不过,这份记录中所描述的亚洲贸易,远不如几个世纪后博学多闻的伊本·巴图塔描述的精彩,因此在阿曼之外,欧贝达的知名度不高。我看着收藏这份珍贵手稿的防护玻璃箱,明白来参观博物馆的阿拉伯人也不觉得这份文件有什么了不起。许多人认为这份手稿平凡无奇,毕竟阿拉伯航海史学者能列出许多这样的记录。
虽然阿曼商人进入中国最早的日期仍没有答案,但在诸多第二三人称的文件中,已确认阿曼与也门的阿拉伯航海者在公元500年已常造访现在的马来西亚甚至中国,比欧贝达记下的丰富经历早了250年。在早期阿拉伯航海者更简短随性的报告中,中国是“中央王国”,北方则有蒙古。阿曼航海者(包括犹太商人)在信仰伊斯兰教,且伊斯兰教尚未扩张之前,即从苏哈尔或马斯喀特出发,短暂停留在阿拉伯湾尖端的巴士拉,之后往南到希拉夫(Siraf,在今天的伊朗)或到更南边、位于波斯湾的盖斯(Qays),再前往马拉巴尔海岸。到了这个年代,在陆上贸易之外,还通过波斯湾与印度洋来运送货物的,不只有阿曼阿拉伯人。
腓尼基人与波斯人(或安息人)早已来到此处,迦勒底(Chaldeans)与古吉拉特人也是。海湾两边的诸多港口多元文化并存,只差希腊与罗马文化。港口居民的语言有闪语、波斯语、印度语。港口边的商队旅馆[3]除了安置骆驼,也要安置大象;除了骆驼夫投宿,也有水手落脚。珍珠和紫色颜料一样常见,而中亚麝香和也门乳香需求都很高。香菜、孜然、茴香与芝麻来自四面八方。
在公元前140年以前,中国人已前往印度与迦勒底港,直接与聚集在此的叙利亚、阿曼与也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通商。在汉朝,中国人称迦勒底为条支,从陆路与海路皆可前往,循海路约100天可抵达。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已熟知佩特拉,称之为“犂靬”。但在唐代时,中国人感叹:“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他们宁愿让闪族人航海与商人前来。
这短短的评论透露出的是,虽然其他文化(例如中国)很早就和闪族一样,有很强的航海能力,却比阿曼、纳巴泰与腓尼基人更急于返乡,回到文化与宗教根据地。相对地,在闪族人的观念中,似乎更愿意让商人建立起“卫星通信”,连接圣地与神庙,避免思乡病,即使以其他语言当作通用语,也不会出现强烈的文化或身份失落感。他们似乎能适应任何环境,确保能做成生意,日后才有精彩的冒险故事可以说。
香料商人就是在以波斯湾和印度洋为中心的贸易网络中出现了大跃进。公元50年到60年写成的《厄立特利亚海航行记》,记载了希腊人懂得运用季节风向直接穿越印度洋往返。只是欧洲人不知道,其他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或许在更早之前或在不久后即达成这项成就,离开浅浅的大陆架,前往更深远危险的水域。从物理与心理方面来看,这些航海的香料商人终于摆脱束缚,在看不见陆地的大海上航行好几天,船舵下没有任何浅滩。他们的成就相当于摆脱地球引力,航向月球或其他星球。
后来,不到40天,商人就能从阿拉伯半岛穿越整个印度洋。此时的他们迟早会经过锡兰(今斯里兰卡),穿过狭窄的马六甲海峡,找到炙手可热的丁香、肉豆蔻仁与肉豆蔻皮。从索科特拉岛或也门的亚丁港,他们会很快绕过好望角,而一到好望角南部又马上面对辽阔的海域。不久,阿曼航海王朝就会殖民肯尼亚附近的拉穆群岛,以及桑给巴尔香料海岸外的岛屿。一旦阿拉伯航海者抵达桑给巴尔,取得陌生的异国植物产品,他们就像登陆了外星。那边的生活条件与尼亚德大不相同,毕竟故乡鲜少降雨,大地上没有“泥土”之地。
一时间,他们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取得新奇的自然资源,卖到遥远的市场。就像童话中的苏斯博士,帮商人创造出奇特的外衣,让商人从一个大陆或岛屿带到下一处。[4]旧大陆终于成为广大的购物中心,里面有大量的“畅货中心”,贩卖数不清的动植物化学品,让人嗅闻、品尝与摄取。
不过,香料商人面对的挑战依然严峻:如何把天南地北的货物来源整合起来,成为连贯的交易系统,还要建立共同的货币、估价与税务系统,让这套体系能从马达加斯加延伸到马格里布与中国。
图9:香料靠着远海运输,让区域性的珍馐进入全球市场。丁香原本只在香料群岛生产,后来进入印度、中国与罗马。19世纪,桑给巴尔成为全球丁香产量最高的地区,图中是人们把丁香铺开晒干的情景。(图片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
煎鱼椰香饭
想从食物中了解印度洋的跨洋交易,最适合的就是香料鱼、米饭、椰浆、扁豆、泰国青柠与嫩姜。刚来到阿曼海岸的人,往往不知道别人端上桌的是传统的阿曼阿拉伯菜还是近年在阿曼苏丹国餐饮界工作的印巴移民工人引进的菜色。从历史观点来看,阿拉伯半岛与印度次大陆交易主粮食谷类、豆类、水果、鱼干、蔬菜与香料的时间相当悠久,因此要区别哪些是哪边的传统、特有或正宗菜肴,答案也都模棱两可。
在也门的阿拉伯语中,“Maqlay samak”简单来说就是“煎鱼”。鱼会先用加了许多香料的柠檬腌过再煎,之后放在以椰浆煮过的饭上。可以使用任何在近海捕捞的白身鱼(例如欧鳊、乌鱼或海鲈鱼)。
以橄榄油腌过的烤茄子或茄子沾酱,是很适合搭配这道菜肴的简单配菜。以下食谱为4人份。
材料
绿扁豆/半杯
新鲜柠檬汁/3/4小匙(www.zuozong.com)
印度香米/一杯半
橄榄油(炒饭用)
小豆蔻荚/四根,切开
印度酥油(油炸用)
去皮鲜姜末/一大匙
椰浆/三杯
水/一杯
海盐
新鲜研磨孜然粉/半小匙
新鲜研磨小豆蔻粉/一小匙
新鲜肉桂粉/一小匙
姜黄粉/半小匙
泰国青柠/两个榨汁
鱼(半斤)/一条,去除内脏
做法
扁豆放进碗中,加水淹过,并加入柠檬汁搅拌,在室温下泡7小时,沥干、洗净后静置。
把米放入碗中,多加点水淹过,以手指淘洗米,洗米水会变混浊。之后把水倒掉,重新在碗中加水盖过米,再淘米、沥干,重复至洗米水变清澈,之后把米沥干。用煎锅或大平底锅以小火加热一匙左右的橄榄油,加入米炒几分钟,之后离火静置。这一步骤能确保煮饭时米不会黏在一起。
用干的平底锅烤肉豆蔻荚,烤香后取出。同一个锅中加入半小匙印度酥油,以中大火加热。加入姜炒香,之后加入扁豆与米,拌匀。加入椰浆、水、小豆蔻荚煮。以盐调味,将火关小,加盖,直到水分被吸收、米与扁豆变软(约30~45分钟)。离火,端上桌前用汤匙把小豆蔻荚捞起。
开始煮米和扁豆前的大约10分钟,可准备煎鱼。在装得下鱼的浅碗中,把孜然、小豆蔻粉、肉桂粉、姜黄粉、泰国青柠汁与一点盐拌匀。静置至少 10分钟,让混合物变稠。把鱼洗净、擦干,与混合香料一起放入碗中,让鱼两面蘸匀,在室温中腌30分钟。
以中大火加热煎锅或炒菜锅,锅内刷一层印度酥油,直到酥油发出滋滋声。之后将鱼从腌酱中拿出,放入锅中煎,记得翻面,避免烧焦,直到两面棕黄(约10~12分钟)。刀尖插入鱼肉时能轻松掀起代表鱼已熟。时间依照鱼肉的厚度而有所不同。
把饭盛入盘中,鱼摆在饭上即可享用。
芝麻
芝麻(Sesamum indicum)种子无论是新鲜的或烘烤过的,都有一股浓郁的坚果香,很适合当香料或烹饪油。事实上,芝麻种子60%的重量是油,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种栽培来榨油的种子。早在欧亚与非洲文明有文字记录之前,印度次大陆就已经驯化芝麻。芝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有可爱的钟形花朵,小小的水滴形种子有白色、米色、浅红色、棕色与黑色。
多数野生芝麻的亲戚生长在非洲,但有种特别的野生芝麻祖先(S.orientale var.malabaricum)只在印度次大陆生长。考古学上找到的最古老的芝麻种子是在印度哈拉帕(Harappa)的印度河谷地(Indus Valley,现位于巴基斯坦),时间可追溯至4000到4600年前。这项发现似乎指出,芝麻在印度次大陆驯化的历史超过4500年,可能在500年后传到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2000年)。巴比伦人只用芝麻榨的油,而麻油在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到了公元前200年,芝麻已在中国种植许久,成为常见作物。有趣的是,许多中国的品种通过丝路往西传到中亚。日本与美国各式各样的寿司上都会撒黑芝麻。
我的老友多罗西亚·贝蒂吉恩(Dorothea Bedigian)是种族植物学家,她称芝麻为“漫游词”(wanderwort),因为芝麻的名称繁多,又通过早期贸易广为传播,因此要追溯语言发源地很不容易。有趣的是,芝麻似乎在青铜器时代早期从马拉巴尔海岸传到美索不达米亚,称为“taila”或“tila”,这个词是源自于印度北部的古梵语,泛指任何有油的种子。无独有偶,阿卡德语的“šamaššammu”,意思也是“油”或“含油种子”。后者与亚述的“shaman shammi”有关,且影响到阿拉米语的“shumshema”(也写成šumšèm)、古阿拉伯语的“as-samn”与现代阿拉伯语的“as-simsim”。希伯来文中的“sumsum”也很类似。这些词都有含油种子的意义。
今天现代波斯语的“konjed”,是衍生于中世纪波斯语的“kunjid”,可能是源自于古亚美尼亚的“kûncût”或突厥语的“kûnji”。同为印欧语系的印度语则称芝麻为“gingi”,可能是描述种子在干燥果荚中的声音。这个字可能也和阿拉伯语中“回音”这个词“jaljala”有关,西班牙语的芝麻“ajonjoli”与马耳他语“gulglien”皆衍生于此。
芝麻往东传入到中国后称为“胡麻”,意思是“外来的麻”,与“油麻”都是使用很久的词。非洲的许多方言与语言称芝麻为“benne”“benniseed”等类似的字,而在美国南方,“benne”仍用来指当作覆土作物或供野生动物觅食的芝麻。
芝麻的种子有点类似饼干的坚果味,经过烘烤味道会更浓。味道浓郁的麻油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未烘焙的芝麻榨出来的油颜色浅,但很清香,加上发烟点高,适合烘焙、炒菜与其他高温烹饪。烤过的芝麻所榨出的油为琥珀色,有扎实的香气,很适合淋在沙拉上或加入已煮好的菜肴中,但发烟点低,鲜少用来油炸。第三种芝麻做成的“油”则是黏稠的麻酱,阿拉伯文称之为“as-simsim bi tahini”,其他语言则称为“tahini”。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曾见过来自黎巴嫩的祖父小心将芝麻酱与柠檬汁混合起来,涂抹到煎鱼上。祖父过世之后,这任务就交给我父亲,由他以同样的认真态度处理。他们都常给我带来酥酥脆脆的美味糖果,那是从纽约布鲁克林的萨赫蒂(Sahadi)家买的,是将芝麻和焦糖化的糖混合而成。我爱极了这种糖果,因此我和人合伙在亚利桑那州亚马多(Amado)开设10亩农场,种植复古品种的谷类与豆类之余,也不忘种植芝麻。
芝麻压碎、加糖后,可用来制作另一种酱,干燥变硬后就是知名的哈瓦酥糖(halvah),从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东部到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与巴勒斯坦都很常见。不过,这个词在埃及到摩洛哥这么广大的范围中是用来指各式各样的甜点,但未必包含芝麻。
整个伊斯兰与犹太世界,居民会把芝麻撒在以麦麸制作的环形圆面包上(包括发酵的与无酵的),称为赛米塔面包(semit,多拼作“simit”),或西班牙文的“pan de semita”。这种面包从土耳其、黎凡特到北非都很普遍。西班牙宗教审判期间禁止食用这种面包,因为它对西班牙的犹太教徒与穆斯林都有很重要的文化意义,在西班牙的拉丁美洲殖民地也是如此。于是芝麻面包师傅与芝麻面包走入地下,只在遥远的地方再度出现,例如德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墨西哥索诺拉州的玛格达莱纳(Magdalena)、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以及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伊格纳西奥(San Ignacio)。
虽然犹太历史学家声称,墨西哥与美国西南部有芝麻点缀的面包圈,代表这一带有地下犹太教徒。不过,这种面包也可能来自人口多元的安达卢西亚,由地下穆斯林与天主教徒引进,并成为传统食物。我们大可以说,无论闪族人与其他人迁徙到哪里,他们都会带着芝麻。或许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明。这些年,我在自己的园子种了些芝麻之后,2011年,也在亚利桑那州南部农场的一小块田种芝麻(正如前述)。芝麻收成后,我就送给我第二故乡的手工面包师傅。
丁香
丁香(Eugenia caryophyllus)尚未绽放的芳香花蕾干燥后就像红棕色的木钉,因此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被称为“clove”,意思是“钉子”。它的香气刺激却甜美,据说“足以烫伤味蕾”,但许多人认为丁香是很好的口腔麻醉剂与催情剂。
摩鹿加群岛的丁香和胡椒、肉豆蔻仁与肉豆蔻皮一样,在世界贸易史上举足轻重。中国最早关于丁香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国人显然是从其他文化的中间商那里得到丁香,包括今天菲律宾人公认的祖先努桑陶(Nusantao,意为“南岛人”)航海人。丁香在2世纪来到印度,梵语称之为“kalika-phala”,传入阿拉伯语系国度之后,被称为“karanful”。
丁香在1世纪时进入希腊与埃及市场,接下来的两个世纪,腓尼基商人把丁香卖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后来,拉特纳犹太商人(Radhanite)把丁香传遍整个欧洲。
公元1300年左右,马可·波罗出版游记之后,欧洲人才开始了解丁香的来源。书中描述这位威尼斯人在返回欧洲的途中,在东海的回族与汉族港口学到关于丁香的知识。到了1421年,回族的航海指挥官郑和与摩鹿加香料商人建立起合作关系。摩鹿加商人早已改信伊斯兰教,重新与穆斯林商人联结起来,由后者把丁香通过各商路贩卖出去。葡萄牙人是香料交易的后进者,但是到16世纪初已垄断昂贵的丁香交易,且长达1个世纪。在葡萄牙人之后,丁香贸易由荷兰中间商掌控,直到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禁止英国人买丁香,除非直接向生产者购买。
【注释】
[1] 英美制长度单位,通常换算方式为1码=0.9144米,实际1码=0.91440183米。
[2] People of the Book,伊斯兰教词,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拜星教徒,有时也包括拜火教徒。过去在穆斯林国家,有经者属于受保护的次等公民。
[3] 例如迦勒底的吉拉港(Gerrha)。
[4] 发现异国植物的经验也会在后来的历史重演,即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与穆斯林来到加勒比海群岛与美洲大陆,挖掘先前从未见过的植物产品,促成“哥伦布大交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