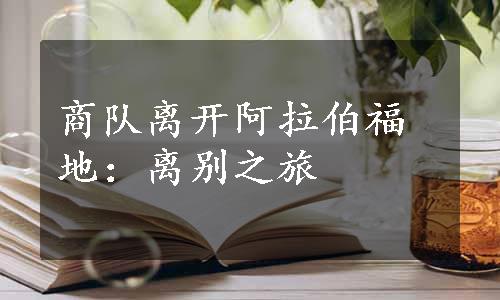
我顺着乳香之泪与没药的袅袅熏烟离开阿拉伯半岛,越过好望角(Horn of Africa),最后在青尼罗河峡谷(Blue Nile Gorge)的火山边缘双脚落地,四周是火山岩大地。在有近700年历史的德布雷利巴诺斯(Debre Libanos)修道院附近,我闻到多种香料共同散发出的气味,那些香料都在大树下的古老市集中。在这树下,能望见青尼罗河的支流阿贝河(Abay River)。眼前的迷人色彩与耳边的陌生话语迎接我进入晨间的香料市集。聚集在此的商人有些住在附近,也有人远道而来,共襄盛举。
我闻到一股夹杂泥土与芥末的气味,直觉那是姜黄(Curcuma longa),一种和姜类似的根茎。世界各地都有人使用姜黄,它可以帮助身体疲惫者与年迈者减少感染。孩童生病时服用姜黄也可刺激免疫系统发挥功效。
为了寻找这强烈气味的来源,我在临时市集的拥挤走道上穿梭。这里像是一群人在开跳蚤市场或野餐,反倒不像真正的市集。我瞥见一名年轻黑人女性朝我打招呼──这来到市集的外地人,惹得她吃吃笑。
我看着她,以及她卖的东西。她席地而坐,身穿蓝灰色长袍,上头以新月和六角星装饰。她头上披着一块长长的紫色布料,眼神窥视我,示意我停下脚步,品尝堆在她面前的毛巾上类似金粉的东西。我弯下腰,捏了一小撮,并舔舔食指。我真喜欢那带点土味、胡椒、微苦却美妙的滋味。这正是我在寻找的姜黄。
突然间,我仿佛感受到比我诞生前还要久远得多的贸易传统。在这一带,香料、熏香、药用茶与芳香植物的采收与买卖,历史长达上万年。这些产物跨文化的交易经过时间考验,重要性不言自明,遂延续至今。姜与姜黄源自于遥远的地方,后来进入了家家户户的院子菜园。如今,本地人以为这些香料本来就生长在他们的土地上,仿佛祖先能唾手可得这些芬芳植物的根部。
这个每周一次的香料市集,是由说阿姆哈拉语(Amharic)的埃塞俄比亚人举行的,他们成群居住在阿贝河上方的斜坡上。外地人知道,峡谷底下的这条河是青尼罗河支流。香料商人聚集在这坚硬的大地上,峡谷边缘颤巍而立的巨大无花果树为他们遮荫。妇女来自步行可及的德布雷利巴诺斯(意思是“黎巴嫩兄弟”),也就是科普特修道院(Coptic monastery)。她们用披肩装满刚采收的农作物,每周爬上山,再来大树下一次,把货物摊开在手工织成的布料或织篮中,并放在大腿前。
我踮着脚,在贩卖五花八门商品的小摊子间行走。我的前后左右尽是成堆的辣椒、姜黄粉、姜、没药与葫芦巴(fenugreek),实在没什么空间让我落脚。我嗅到附近烤葫芦巴种子飘来的淡淡焦糖苦味。我遇到的埃塞俄比亚人都喜欢把烤过的葫芦子(abesh)磨成粉,再加入到许多食物中,例如类似可丽饼的因杰拉(injera),它是一种用发酵苔麸(teff)粉做成的饼。
我环顾四周,这棵无花果树下人潮汹涌。我总觉得,早在人类开始用瓦罐煮野菜时,这处露天广场就存在了。那时人类会围着营火彼此诉说故事、交换食物。这棵为商人遮荫的伞状古老大树,说不定就是传说中那棵“人类诞生的树木”。
如此古老的市集,为什么仍这般朝气蓬勃,不只向我这临时造访的人招手,也引来许多当地人?人类是不是藏着某种基因,致使我们想品尝有异国风味、味道强烈的芬芳之物?这样堆满香料、熏香、绿色咖啡豆、谷类、豆类、膏药与茶的市集,似乎是让各路人马从附近山谷、河谷与山上前来,齐聚一处的原始方式。
图2:巴里遗迹。这是印度洋跨大陆交易最早的海港之一。(图片来源:作者)
3500年前,附近香料交易出现新变化,虽然那种崭新的发展,是在4800年前就从诸多各自独立的经济体中慢慢发生,进而积累而成。这一变化最早可能发生在非洲东部,或阿拉伯半岛南岸。我不知道最初发生的地点或是从哪个民族浮现,但这一现象传播后,就改变了世界经济与生态的轨道。
我在阿曼南部时,曾有机会造访半岛上最古老的香料交易中心之一。先前提到的转变应该早在史前时代就发生了,并使市集的性质成为我们今天熟知的模样。这处香料交易中心比阿拉伯海略高,周围有火山露头包围的小河湾。有人独具慧眼,知道这河湾既美观又实用,是极佳的天然屏障。
我是在那地方开始有人居住后的数千年才抵达,发现船只不再进入这个港口。河湾已成了苍鹭、白鹭与 的避风港。禽鸟来到此地的原因,或许和最早的人类居民一样。一条鬣狗从河口边往火山上跑,最后消失在洞穴中。港口有丰富的鱼贝,适宜居住,既容易从海上进入,又有屏障。野生单峰骆驼来到岸边的水潭寻找淡水。这一位置绝佳的地点曾是扎法尔港,位于史前的海港小镇巴里(alBalid)。佐法尔省的名称正是来源于古代的扎法尔,如今是阿曼最南边的贸易枢纽。我曾在几英里外买到霍杰伊乳香。
傍晚,夕阳的余晖在海面洒下柠檬色与玫瑰色的光。我在巴里镇附近游走,以前骆驼商队就在此处与海上的阿拉伯帆船相遇。知名的旅行作家伊本·巴图塔[1]在14世纪曾见识过这样的景象。之后阿拉伯帆船会载着乳香与其他芳香植物离开山区原生地,穿越海湾,前往遥远的其他的大陆。
“巴里”这个名字,是早期阿拉伯文中“永久城镇”的意思,和过去季节性的营地截然不同。没有什么意外,考古学家已确定这160亩的遗址,确实是4000年前的重要人口中心。那时的阿曼称为“马干”(Land of Magan),外地人也知道这里的人会把铜送到北边的繁荣城邦迪尔门(Dilmun)。迪尔门是古代贸易中心,位于肥沃的农业谷地,离岛国巴林的巴林堡(Qalat al-Bahrain)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已解读出在巴里发现的部分古代楔形文字,确认了早在公元前2800年,人们就会长途运送数以吨计的粮食来交易。同时期的苏美与阿卡德(Akkadian)碑文也显示,当时的人会进行海上贸易,路线从美索不达米亚往北到迪尔门岛,往南到阿拉伯半岛的马干,往东则到梅路克哈(Melukhkha)水域──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香料岛,也就是今天的摩鹿加群岛。
苏美与阿卡德的部分碑文可能是最早关于全球长行程贸易的文字记录。这些记录显示,闪族中的马干人会用铜(或许还有熏香药品或香料)换取数百吨的大麦。数量如此庞大的谷类会沿着波斯湾海岸往南运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沿着阿拉伯海的海岸远达扎法尔港。
人也会跟着思考。商人可能开始动脑筋,思考某地生产的阿魏说不定与故乡的优质莪术一样有价值;于是他们巨细靡遗地比较出不同的物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思索如何利用。
简言之,来自世界上最干旱土地的闪族,已学会如何用手中的少量贵重金属、宝石与有功效的植物产品(树脂、种子、类似肉桂的树皮、花朵的缤纷柱头、苞片或花苞),交换世界上其他水源较丰沛之处所盛产的粮食。
姑且让我推测“学会如何交易”的重要性。香料商人学会基本营销技巧后,就知道该运用心理策略,说服农夫买个铜铃铛送给妻子当项链;买个抗发炎的东西来治疗背部很重要,就像他需要足够的苔麸或小米来维持家人温饱,以免在接下来的歉收季节挨饿。人们会不会以为,来自世界另一个角落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和他在自家土地上采收或生产的最优质产品,一样有功效、值得渴望与拥有?或许香料商人当初就是靠着这种方式找到他们无法轻易种植的粮食,例如高粱、大麦、小麦与苔麸,以及蚕豆、鹰嘴豆与扁豆。他们在沙漠之海中,在如岛屿般的灌溉土地上发现这些谷类与豆类。住在绿洲的居民表达出他们想要香料的欲望,为日复一日的枯燥粮食带来变化,为吃腻的餐食增添不同滋味。
椰枣配羊肉、羊肉配小米、小米与椰枣,高粱与羊肉、羔羊肉与高粱,碎麦与鹌鹑肉、鹌鹑蛋与鹰嘴豆炖煮。若某种香料(shadhan)有令人难忘的浓重滋味,能不能为千篇一律的粮食增加些许乐趣?该用什么东西打破饮食的单调乏味,以免让每天处理、烹调食材与吃东西沦为苦差事?
可以想象,若心中总是挂念着些问题,会出现何种情况。这问题可能使人更不满意眼前境况、更渴望难以得到的东西。闪族人(至少有一部分)似乎臣服于某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渴望──沙漠另一边的草总是比较绿。这一渴望是无法满足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无论到了哪里,都会创造出某种心灵沙漠,因而永远到不了“草地”,得不到幸福。
因此,商人和游牧民族一样,也有走向天涯海角的动机,原因不光是帮自家的食物储藏室增添食物,更要让这些食物能有香料搭配。经济历史学家近年确认,闪族商人确实运用奇妙的方式来适应阿拉伯半岛的农业与野生资源零星分布的情况。他们游走在环境迥异的零星田地间,成为有效率的商人,重新分配多样性与财富。他们不仅得采用某种移动方式,更须具备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居民鲜少具备的心态,这样才能做成生意。
我离开佐法尔,远离乳香的生长区,造访阿曼北部的露天市集时,才明白这些早期商人多么重要。那时我与妻子萝莉(Laurie)和优秀的农业科学家苏莱曼·康嘉里(Sulaiman Al-Khanjari)一同旅行。他与许多阿曼人一样,家族来自桑给巴尔。我们一到海岸大都会马斯喀特,苏莱曼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再去一趟香料市集:“你们看到的东西会和在塞拉莱看到的差不多,但我希望你们见见今天可能会在市集出现的某个人。”我隐约觉得,苏莱曼说这段话时眼睛闪闪发光。
我们到了露天市集之后,在狭窄的走道上寸步难行,成群的阿拉伯年轻人想要买衣服、珠宝、电子用品、手表、鞋子,当然还有香料。萝莉和我想跟上苏莱曼的脚步,无奈总是被阿曼拥挤的人潮冲散,因而落后朋友兼导游几米。好不容易赶上之后,苏莱曼把我们拉到一旁,解释下一步的行动。“我先去和一个朋友见面,他的店面在那边的小阶梯上……看见了吗?对,就是那间。如果他在上面的话,我会跟他聊一下。等我招手示意,你们再过来。”
我看见苏莱曼向一名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色小圆帽、脚上穿类似拖鞋的男子招手。他们两个人穿着一样的服装,彼此拥抱后,便悄悄聊了一会儿。终于,苏莱曼朝我们挥手,示意我们过去。
“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纳卜汉博士,来见见你失散多年的堂兄吧──阿曼马斯喀特的乳香商人纳卜汉先生。”苏莱曼咧嘴一笑。之后,他把方才的英文翻译成海湾阿拉伯语给身旁的中年男子听。这名男子比我矮,有一头黑发,眼袋和我的近亲不无类似。他的皮肤和我父亲一样是橄榄色的。
“Al-hamdu lilah!”(赞美神!)这名香料与熏香商人对我微笑,之后握起我的手。他请萝莉一起来照个相,还送我们乳香当礼物。我们开始问彼此问题,苏莱曼慷慨地当起翻译,并自行增加一些背景说明。
“阿曼是不是有很多纳卜汉尼家族的人?”我问。
这位商人点点头。“对,他认为如此,”苏莱曼解释。商人继续说阿拉伯语,苏莱曼听完,再翻译给我听。“你们这个姓氏的人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或许有1400年,甚至2000年。所以,住在这儿的纳卜汉尼家族人数众多……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苏莱曼之后加上几句显然是他自己的说法:“他们就像是你们国家姓史密斯或琼斯的人!他们说,纳卜汉尼家族是和其他哈德尔族(al-Hadr)的人一起从也门来的,但我不知道是多久以前。”
这位可能是我远房堂兄的乳香商人滔滔不绝地解释,苏莱曼试着翻译得更精确些:“是很古老的部族……你们怎么说的?开枝散叶吧!有许多谢赫(sheikh,这是阿拉伯语常见的尊称,是部落首领的头衔)呢。”乳香商人之后问,在我们国家是不是有许多纳卜汉尼家的人?如果有,他们是从哪里过去的?
苏莱曼把我的回答翻译成海湾阿拉伯语:“我的祖父母和姑姑是在黎巴嫩靠近叙利亚边界的地方出生。他们在一百年前搭船从贝鲁特出发前往马赛,之后到美国纽约。还有人去了墨西哥或巴西。”
苏莱曼翻译完我的回答之后,便与纳卜汉先生你来我往聊了几分钟。终于,苏莱曼回过头,对萝莉与我咧嘴一笑:“他想知道你们在美国的商店里卖些什么东西。”
我在想如何回答阿曼商人纳卜汉先生时,也想起最早抵达纽约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的家族成员,他们曾挨家挨户兜售香料、包装香料,或在布鲁克林的亚特兰大大道(Atlantic Avenue)的街角杂货店贩卖香料。
我小时候为了赚零用钱,曾挖掘番红花的根,并在墨西哥的索诺拉州(Sonora)与原住民朋友一同采收野生的奇特品辣椒(chiltepin)与墨西哥奥勒冈,然后当中介人,卖给零售商店。现在我在亚利桑那州沙漠高地的小农场上还种了20多种椒类、薄荷与奥勒冈。
我抬起头,看见纳卜汉先生与康嘉里博士还在等我回答。我知道自己无法以阿拉伯人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遂简单回答:“对,我的家人曾在美国买卖香料,不过我自己是老师……与农夫。”我请苏莱曼向那位先生解释,“一开始,我祖父与叔叔伯伯们卖过香料。我在美国采收过辣椒(fulful)与香草(za'atar),装满一卡车后,再卖到其他国家。”
纳卜汉先生是从未离开过故乡的乳香商人,他会心一笑,好像总算确信我是他的远房堂兄弟。
我在也门数据馆找不到任何阿拉伯系谱,因此无法轻易得知我们的亲缘到底有多近,或者到底几代以前的纳卜汉尼家部落祖先就进入了传统香料这一行(其实是种偏好)。我们只知道,数千年前出现的崭新发展,影响了闪族人在熏香、药草、麝香、染料与香料集结处的行为。
商人最初是靠着半驯化的骆驼与小帆船把这些货物送到离产地十分遥远之处。他们横跨大陆,来到相异的文化环境,那里的人说的语言是他们从未听过的。起初,商人们只能骑骆驼旅行,因为骆驼一天能在平地上走22英里路。后来,商人终于找到办法搬移较重的香料、熏香与药草等货物,且搬运得更远,超出驮兽的负担范围。
商人开始打造小型阿拉伯帆船,开启自己在阿拉伯海与印度洋的远海航行。他们的目标是,在顺风的情况下,每天要比最强健的骆驼走得更远。当然,在这个时期,许多文化中的商人已经想出如何在海岸的浅滩与附近礁岛后方的潟湖航行。他们的小船是靠着动物皮囊浮起,而且是由缝制兽皮、芦苇束、挖空的棕榈或树干做成。
但我认为,来自阿拉伯南边与东边的水手更有企图心。他们架起船桅,并在船桅上挂起可操控的大船帆,使水手们能顺着风向改变船帆方向。他们穿越海洋,靠着季节风向让小帆船往返。不久之后,在半岛的海湾或浅滩航行已不能满足他们,于是他们开始用遥远的地标与星斗在更辽阔的水域辨识方向。
图3:肯尼亚拉穆群岛海域附近的独桅帆船。这是早期香料商人重要的航海工具。[图片来源:卡尔·雷格纳·吉尔森(Karl Ragnar Gjertsen)]
半个多世纪以前,历史学家乔治·法德洛·胡朗尼[2]开始思考,为何阿拉伯人最早通晓航海探险之道。胡朗尼在文笔优美的经典之作《古代与中世纪早期印度洋的阿拉伯航海人》(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中,大胆提出主张:
阿拉伯海岸的地理条件有利于航海的发展。阿拉伯半岛三面环海,海岸线甚长,从苏伊士湾(Gulf of Suez)开始延伸,绕至波斯湾(Persian Gulf)。海岸线附近是阿拉伯最富饶的地方:也门(alYaman)、哈德拉毛与阿曼(Umān)。从海上往返这几处,并不比跨越这几个地方间的沙漠与翻山越岭危险。许多阿拉伯人想和邻国做生意,只要穿越红海与波斯湾所包围的水域,就能联系两个古代财富与文明的中心──埃及与伊朗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是,红海与波斯湾有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注入,成了进入地中海盆地与东亚的最佳通道。于是,阿拉伯人能涉足世界两大贸易路线。
有些阿拉伯半岛南方与东方的闪族显然不再满足现状,因为他们更经常通过长途贸易与其他文化中的人接触。这或许只是一种臆测,但他们的信仰体系似乎与当时众多泛神信仰及多神信仰分道扬镳。
这些不安定的灵魂或许是放眼世界,但同时情感与道德也较为“居无定所”。人类生态学先驱保罗·雪帕德(Paul Shepard, 1925—1996)曾指出,中东沙漠的独特闪族心理代表人类史上的转折点。“这些旧约圣经中的先祖们是史上最有企图心的人,懂得善用居无定所的情况……闪族人的暴风雨神是会四处游历的神衹,能在任何地方出现,不局限于某个地点。”
有趣的是,他们无论旅行至何处,甚至定居他乡之时,都不会遗忘他们的神。因此,闪族的各族群不会因为远离故乡便失去文化认同。换言之,他们的身份认同似乎与实际生活地点无关,即使心中多多少少眷恋着祖先的老家。
犹太神学家亚伯拉罕·乔舒亚·赫舍尔[3]虽然不像生态学家雪帕德那样,提出居无定所那么尖锐的观点,但赫舍尔承认,闪族的核心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和其他近东文化大不相同。赫舍尔指出,在他们心中,有些闪族否认这个观念:“神居住在空间,例如在山脉、森林、树木或岩石等特定的神圣地点;神局限在某个特定地点。”
相对地,赫舍尔推测,多数闪族宗教渐渐接受的概念是“空间(或者圣地)和神的性质是不同的”。如果神在任何时空都会出现,而不局限在特定地方,那么经济机会也是。
阿曼的闪族航海人似乎打算落实这一可能性,遂展开六七十天的长途跋涉,前往异乡,而异乡居民总渴望购买他们的新奇货物。一两千英里长的旅程突然变得稀松平常。从32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记录来看,阿曼与也门的乳香已更频繁地出现,而且数量也不少。
为了迎接商队与商船的长途运输,以及跨文化交流等诸多新挑战,因此,能说多种语言的独特商人阶级兴起。这些商人设法克服了商队或海上运输的困难,还能灵活学习不同的语言,能以吸引人的方式向其他人诉说产品有何神奇妙用,以及运送过程中曾有过哪些冒险。他们也开始谈买卖,且不只是一次性的买卖,而是大量买卖。
有些人天生就是语言天才,各文化中也不乏有说故事天分的人。不过闪族的香料商人会培养年轻人的这两种能力,这样常驻遥远异乡的成员便能以外国语言诉说商人经历的神秘层面。顶尖的香料商人太了解,他们不只是贩卖热量、药品或香气,更是贩卖这些商品附带的故事,因此要以故事来强化每种品项的价值。
如今能叫出名字的最早的商人文化,是来自庞特(Punt)国的迈因人。部分欧洲人以“庞特国”称呼古阿拉伯南边的熏香王国,包括今天也门与阿曼南方的佐法尔区。庞特也是圣经学者认为的传说中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居住地,虽然这个熏香王国的正确名称是“萨巴”(Saba),而非“示巴”。最好的乳香来自哈德拉毛与佐法尔高地,不过这些地区西边、迈因国(Ma'in)的迈因人,是最早把乳香卖到更广区域的商人。他们最初可能在靠近季节性扎营之处,用乳香换取绿洲上生产的粮食作物。后来他们在更广大的区域用乳香换取其他产品。
当然,长久以来,他们与其他人交易的当地物产包括野生茴香籽、肉桂类树皮、靛青染料甚至没药。位于北边的迈因国营地只要几天的时间就能取得这些商品,之后再用这些野外的产品换取南边萨巴、提姆纳(Timna)与夏布瓦(Shabwa)国度中,水源较丰富的绿洲村落所生产的谷类、豆类、椰枣与药草。皮制品与金属也从不同的贸易路线送来,不光是一条乳香之路。多数迈因人住在偏远的内陆,位于阿拉伯福地与阿拉伯沙漠(Arabia Deserta)交界处。
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迈因人控制了最后几处以石墙包围的小型绿洲,也就是定居的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雅什里布[ Yathrib,后来改称为“先知之城”(Madinat Rasul Allah)或是麦地那(Medina)]与盖尔诺(Qarnaw)。这时,迈因人的商队还没开始前往游牧民族漫游的鲁卜哈利沙漠之海,也尚未到尼亚德边缘的乳香或没药树林收集乳胶。
不久之后,迈因人经常往返两个极为不同的世界:一是在沙漠野地采集香草、熏香与有用药物的游牧民族,另一则是栽种小米、椰枣、芝麻与亚麻,以及用番红花与槐蓝为生活增色的定居部落。
善于说故事的迈因人想出无数方式让定居的农民觉得游牧文化相当神秘,反正这些定居者忙着灌溉,根本无暇探索外界。同样地,迈因吟游诗人也设法让游牧民族羡慕农民在永久的农庄与村落所积累的财富。迈因人游走于这两个世界,学会了如何轻轻松松地将两者玩弄于股掌间。
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650年,这群担任中介的迈因人逐渐牢牢掌握早期半岛南边的香料交易。虽然他们的势力从未扩张到整个半岛,却替未来的跨区交易铺好了道路。历史学家卡罗琳·辛格(Caroline Singer)指出,迈因人在热闹的交界社群中扮演枢纽角色,包括夏布瓦绿洲哈德拉毛人与马格里布绿洲的萨巴族群,以及航海时期运送香料的主要港口坎纳(Qana):
商人本身或许并非夏布瓦的本地人,而且没有证据显示,哈德拉毛人或萨巴人曾当过香料商人。显然,有个非常特定的南方阿拉伯人群体扮演着长途商人的角色——他们来自迈因国。根据老普林尼记载,迈因人是罗马世界最知名的南方阿拉伯人。他们会带着熏香商品到叙利亚、埃及与亚述,还会到希腊与罗马。他们还建立起活跃的商人网络,商路上的各个关键点都有行政长官监督。在卡塔班首都提姆纳、哈德拉毛的夏布瓦、偏远的底但(Dedan)绿洲,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等诸多城市,都有迈因商人的聚落。(www.zuozong.com)
值得玩味的是,整个阿拉伯半岛的熏香与香料商人(例如迈因人)常把最珍贵的香料藏在远离港口的小城。好港口固然很难得,却也难以防守,容易被不怀好意的外来者入侵。比方说,行踪不定的纳巴泰人就住在佩特拉这座隐秘的城市。多数香料商人都会造访这处内陆绿洲,毕竟掠夺者若想前来此地,得先穿越环境严酷、毫无变化的沙漠,之后又得进入堡垒,最后才能找到最珍贵的货物。如今的阿曼与也门,过去都有这样隐秘的香料储藏处。
萝莉和我在阿曼时,曾造访巴赫拉要塞(Bahla Fort),那是过去香料商人使用过的堡垒中最具代表性、最完整的一座;我的纳卜汉尼家族祖先也曾来到这里。这座神秘的堡垒城市深居内陆,距离我祖先曾掌控交易的几处港口相当遥远。我们往内陆前进,先穿过荒凉的海岸平原,来到布满碎石的干涸河床,又在低矮的石灰岩小山群上上下下,才看见如今仍令人震撼的巴赫拉要塞。它位于陡峭的石灰岩高原“绿山”(Jabal al-Akhdar)旁。当年我的亲族曾掌控肥沃的河谷,失去霸权之后也曾避居在此。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浓密高大的枣椰树林,之后才看见其他耸立在地平面上的轮廓,乍一看,宛如炙人骄阳下的海市蜃楼。高耸的石墙绵延10英里,城堡般的堡垒在原野与树林中拔地而起。
以前,人们把香料、熏香、椰枣与贵重金属都藏在这儿,之后才由骆驼商队趁夜晚凉爽时送到海边。肉桂与小豆蔻、黑胡椒与白胡椒、番红花与檀香也都囤积在这里──这些货物是向冒险犯难、远道而来的水手购买的,他们来自索科特拉岛(Socotra)、印度马拉巴尔海岸、斯里兰卡或印度尼西亚。
我们那天在灌溉沟渠间逛了很久,附近有蚕豆田、玫瑰丛、椰枣园,还有柑橘、石榴与无花果园。这些地方是靠“阿夫拉贾”灌溉体系(falaj)滋养,这个灌溉体系从荒芜的石灰岩山坡收集雨水,储存起来供城墙内的绿洲使用。我们造访过铺着石头的祈祷池、浴池,还有蜿蜒的运河穿过荫凉苍翠的世界。这里和城墙外被烈日烧灼的沙漠有着天壤之别。
后来,我们来到尼兹瓦(Nizwa)附近一处贩卖蔬果的市场,当地居民阿里·马苏德·苏比(Ali Masoud al-Subhi)加入我们的行列。阿里告诉我们,他有个特别的东西要让我们瞧瞧。他带领我们来到一处果菜摊,顾摊子的老人在打瞌睡,脸被白袍(jalabiyah)遮着,仿佛正午暑气使他没力气招呼顾客。他前面的白色台面上放着两尺长的棕榈穗状花序,上头结着刚采收的椰枣。“吃吃看,”阿里悄声告诉我,“别担心,我们不是在行窃。我会把钱留给老人家,他醒来就会看见。”
后来我从棕榈花序上掐下几个成熟的枣子,一个给苏莱曼,一个给萝莉,第三个给自己。我的牙齿咬破深巧克力色的皮,焦糖色的果肉真是甜美无比。
图4:巴赫拉要塞是个内陆枢纽,货物会经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与印度洋卖到世界各地,如今已列为世界遗产。(图片来源:作者)
我抬起头,看见阿里已经在柜台上放了几个铜板,又摘了个椰枣。他用拇指和食指捏起,好像把椰枣当成了科学标本。“朋友,这叫作‘纳卜汉尼椰枣‘,只在这里生长,其他绿洲可能都找不到。或许是很久以前,为你的家族命名的。”
在阿拉伯半岛上,所有有灌溉水源的枣椰绿洲,对阿拉伯民族历史而言,重要性都不言而喻。尼兹瓦、巴赫拉,以及也门中北部阿德汉纳谷(Wadi Adhanah)的马格里布都是例子。一般认为,这些地方最早出现采用水利系统的文明。这些水利系统是在4000年前兴建的,是当时最浩大的灌溉工程,为超过4000亩的食物与纤维作物供水。
历史学家声称,世界各地许多靠灌溉而发展农业的传统文明,皆发源于马格里布。灌溉系统先传到阿曼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后跨越地中海传入西方,往东传至中国,最后传到美洲。西班牙语系广泛使用的“acequia”一词(意指灌溉沟渠),仍源于古也门的阿拉伯语“al-sāqiya”,指任何一种引水道。
不过,迈因文化能蓬勃发展,是因为和依赖灌溉农业、趋于定居的哈德尔族,以及偏向游牧的贝都因与贾巴里族建立起共生关系。哈德尔族投入灌溉农业,而贝都因与贾巴里族则是从事畜牧业或交易香料。虽然住在绿洲的农民能为整个阿拉伯福地与众多阿拉伯沙漠的族群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但骆驼夫、熏香采集者与香料商人却带来财富与物欲。
事实上,马格里布水坝是经过多个阶段、耗时数千年才完成,为面积超过9500亩的年收作物、果园与枣椰园提供灌溉水源。这个水坝后来横跨阿德汉纳谷(Wadi Adhanah),在巴拉克山丘(Balaq Hills)堵住600码(约550米)的间隙。公元前715年,统治者苏姆胡·阿雷·亚努夫(Sheikh Sumhu' Alay Yanuf)父子完成了水坝的最后阶段,那时紧密堆放的石头与砖石砌成的墙,比阿德汉纳谷的原始河床高出50尺(约15米)。水坝另一头的巴拉克山岩床下有处水库,泄水闸会沿着25尺(约7米)厚的洪水蓄水库把水送下来。从这里开始,绵延数里的“母运河”会把储存的洪水送到次级与三级运河,进而让水流进萨巴人种植谷类的田野与果园。农民之后将农作物卖给迈因人。迈因人可以用乳香、茴香、没药与野生药草,换到六七种谷类、四种豆类与十多种水果,还有藤蔓类瓜果、西瓜与小黄瓜。
多数蔬果是趁新鲜生吃,剩下的则晒干,供日后食用。谷类甚至豆类会烘烤磨成粉,之后做成哈利拉蔬菜汤,这道菜里通常有小麦、鹰嘴豆、扁豆,也可能加入香料、洋葱与野生青蔬。居民也会用柴窑烤无酵大饼,蘸抹谷类、羔羊肉或山羊肉煮成的汤,当成前菜,之后再吃塔里德炖肉(tharīd,会搭配面包食用,通常有肉,但有时则为素食)与抓饭(maqluba,用煮熟的谷类、肉与蔬菜炖煮而成)。新鲜椰枣或压制成厚饼的椰枣随时都有。这些沙漠农民的食物虽然朴素,却最美味。
迈因人也用萨巴人染的骆驼皮、山羊皮与绵羊皮换到棉麻来纺织。在长达2800年的时间长河中,荒野沙漠区与生活在此的游牧民族找到某种方式,与马格里布绿洲较为温和的世界相辅相成,让区域经济为双方带来繁荣。
图5:图中为哈德尔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发明的水车(sakieh),是了不起的创新之举。这种水车通常由牛推动,在中东与埃及进行灌溉。(图片来源:纽约公共图书馆图片与印刷品部)
但是在苏姆胡·阿雷·亚努夫与工人设法掌控沙漠自然环境后的千年,马格里布水坝溃堤,洪水淹没大地。一夕之间,萨巴人目睹四十个世代赖以为生的水库干涸。无论是萨巴人或是相邻的迈因香料商人,在世界上的角色顿时风云突变,再也无法复原。
虽然闪语系的部落早已迁出阿拉伯福地,前往半岛上的其他地区,但是到了3世纪,马格里布遭逢洪灾的难民也跟着加入流离行列,规模之大前所未见。知名阿拉伯历史学家艾伯特·胡朗尼(Albert Hourani)指出,这期间来自也门的原始阿拉伯人(proto-Arabic)中,闪族宗族大幅移出,是阿拉伯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许多宗族永远离开南方的故乡,分散到整个半岛,并慢慢转变成重要的阿拉伯族群,日后演变为主宰整个中东区域的主要阿拉伯部落。有些人往北前进,走上最早的商队携带乳香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与埃及的道路。他们的许多后代后来也开始做起香料买卖。
然而,就像某些离开了应许之地的犹太族群一样,这些原始阿拉伯人离开也门南部灌溉良好的绿洲之后,脚步再也停不下来。除了神秘的老家之外,他们不属于任何地方。当然,他们够聪明、适应力够强,体力与经济都足以让他们在任何地方建造新的家园,只是与祖国相系的心灵脐带切断了。他们能在许多气候带建立房屋、王朝与经济体,却无法回到家园。
许多人成为冷漠的流浪人──这大概是香料商人不可避免的个性特色。
在鲁卜哈利的沙漠之海中,他们标示出离开也门的古代路径,留下和人一样高的石坊(trilith)。正如石坊的名称,这方尖碑似的石堆数量不一,有的是三个,有的则成群出现,且高度够高,即使碰上沙漠风暴也不会被积累的沙子淹没。这些石坊标示出的道路指示着人们从阿拉伯福地走向辽阔世界。
纵使经过几个世纪沙漠风暴的侵蚀,如今依然看得到这些石坊在原地屹立,只是在风吹日晒之下,线条变得逐渐柔和。这些石坊是史上最大规模迁徙的现存证据──迈因人、阿拉伯人、犹太人、腓尼基人与亚拉姆人等闪族人离开阿拉伯福地。水坝溃堤,他们离开半岛故乡,积极寻找最浓烈的香料与熏香,使这些物品在任何地方都买得到。
香味飘到哪,我就要跟到哪。
地图2:撒哈拉的香料之路
椰枣蝗虫香料饼
阿拉伯沙漠的游牧民族在寻找食物时常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盼着能碰到意外之财或是意外的大丰收,让他们能采收、干燥,并将食物储存起来,在日后必会发生的歉收月份食用。这样的食物必须精巧,不会腐坏,毕竟得在骆驼鞍袋中放几个月。游牧民族会用这些食物和迈因人等绿洲居民交换谷类粮食。
接下来这道菜肴,参考了伊本·萨亚尔·沃拉克(Ibn Sayyār al-Warrāq)的蝗虫食谱。作家莉莉亚·扎亚利(Lilia Zaouali)认为,沃拉克的著作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阿拉伯烹饪书之一。这道食谱是把蝗虫揉进枣椰糊中,而我加入阿拉伯半岛上找到的香料,或数千年来与印度贸易时取得的香料(尤其是茴香与阿魏)。厨师阿娜·索顿(Ana Sortun)认为,加入茴香籽可为蔬果增加温润、类似薄荷的甜味。世界香料商场(World Spice Merchants)香料公司的东尼·希尔(Tony Hill)说,阿魏(和洋香菜同科)磨成粉之后,会散发出强烈的硫黄臭味,但加热后能转化为可口的洋葱香与蒜香。在这个食谱中,以前人们通常使用野生椰枣,但使用较常见的大椰枣(Medjool)或其他容易买到的栽培品种亦可。尽量别用较珍稀的种类,例如黑斯芬尼克枣(Black Sphinx)。如果找不到(或不敢抓)大量蝗虫,可改用加盐的烤蚱蜢(部分墨裔香料行可买到从墨西哥城进口的蚱蜢)。
搭配热薄荷茶或冰芙蓉茶。6人到8人份。
材料
活蝗虫/四杯
水/四杯
海盐/1/4杯
芫荽籽/两大匙
茴香籽/两大匙
阿魏粉/两大匙
卤水
水/五夸特(565毫升)又一杯
玫瑰水/三杯
盐/六大匙
椰枣(去皮切碎)/八杯
做法
抓一群飞行很久后休息的蝗虫,放进加盖的篮子。在椰枣树荫下,小心地将死蝗虫挑出来丢掉。把活的蝗虫放进大碗中,加入水与盐淹过蝗虫,之后把水倒掉,把蝗虫放回篮子。
在石研磨钵中,将芫荽籽和茴香籽混合,磨成略细微的粉末。加入阿魏粉搅拌。
制作卤水时,将水、玫瑰水与盐放到700毫升的容器中,并加入盐搅拌,让盐融化。在瓷盘或陶盘中,平铺蝗虫,1厘米厚。舀出4杯卤水,淋到蝗虫上,并在上方均匀撒一大匙混合香料。用重盘子压在上面,把盘子往下压,静置10分钟。将卤水沥干,重新铺上蝗虫,浇淋卤水与综合香料并以重盘子压,重复这一过程5次,每次静置10分钟。每次沥出的腌酱颜色应该越来越浅,最后一次差不多清澈了。将卤水冲过的蝗虫放进陶锅,加盖密封,让容器气密。让蝗虫在室温中发酵至少几天或数周。
把蝗虫放进大碗中,加入椰枣,用手揉成柔软的混合物。将混合物拍成直径5厘米、厚度0.5厘米的圆饼,放进骆驼皮鞍袋中。
姜黄
姜黄(Curcuma longa)是姜与南姜的亲戚,会散发出带有土味的浓烈香气,还有颇为讨喜的苦味。嫩的姜黄根茎是淡淡的绿色,和铅笔一样细,干燥之后会呈现橘黄色,而表皮底下的颜色更深。姜黄源自南亚,今天多在印度种植。以前,靠着横跨陆地的骆驼商队,姜黄被送到印度次大陆以外,抵达小亚细亚的亚述与苏美。
到了8世纪,阿拉伯独桅帆船往西跨越印度洋与阿拉伯海,把姜黄送到也门与东非,包括由留尼汪、毛里求斯和罗德里格斯岛组成的马斯克林群岛(Mascarene Islands),还沿着柏柏尔人、贝都因人与犹太商人控制的商队路线,送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阿拉伯帆船也往东航行,在7世纪把姜黄送到中国,从此姜黄在中国逐渐被广泛栽培与使用。马可·波罗就看过不只中国栽种姜黄,连苏门答腊与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也有种植。
不过,姜黄名称的传播路线似乎不同,这可能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在较北边的商路有关。希伯来文中的姜黄称为“kurkum”,同源词包括意第绪语、希腊文、意大利文、保加利亚文、俄文、乌克兰文、芬兰文、挪威文、德文、爱沙尼亚文、捷克文、克罗埃西亚文、荷兰文、布列塔尼文、加泰罗尼亚文、西班牙文甚至韩文。英文的姜黄“turmeric”,概念则是源自法文,并源于拉丁文的“terra merita”,意思是“值得赞扬的泥土”,难怪有人说姜黄粉的外观看起来和贵重矿物不无类似。“turmeric”与“kurkum”的词源相近,都是指黄色的根,其他语言的姜黄也有类似的意思。
小豆蔻
小豆蔻(Elettaria cardamomum)价格昂贵,仅次于番红花与香草。它含有萜品烯(terpinene)、桉油醇(cineol)与柠烯(limonene)精油,因此香气浓郁。小豆蔻长在如灯笼般的白绿色豆荚中,里面有25个乌黑的种子,散发出兼具檫木属植物、尤加利、多香果、丁香、樟脑与胡椒的气味。小豆蔻的香气刺鼻,却不失细致温暖。
小豆蔻是姜的远亲,可能源自于印度南部西高止山脉(Western Ghats)的喀拉拉山丘(Kerala Hills),在5000年前的古梵语文本中到吠陀时代晚期都曾提过。小豆蔻在公元前7000年传到巴比伦,在50年之前已经抵达希腊。如今,小豆蔻从印度到危地马拉广为种植,在斯里兰卡还有果实较大的品种。
从语言上来看,小豆蔻的陆路贸易可追溯到小亚细亚,海上贸易则追溯到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中东与东非语言中,小豆蔻的名称相当类似:阿拉伯文称之为“habbu al-hayl”;希伯来文、波斯文与阿姆哈拉文称为“hel”;亚塞拜然语和提格利尼亚语称之为“hil”。这些同源词源自于梵语的“eli”“ela”或“ellka”,可能也影响到印度与克什米尔语的“elaichi”、孟加拉国语的“elach”,还有古吉拉特语的“elchi”或“ilaychi”。有趣的是,欧洲语言中(尤其是罗曼语系)的小豆蔻和东非、中东与印度次大陆中的截然不同。欧洲语系中的皆源自于古希腊文的“kardamomom”。香料学者葛诺·卡策尔(Gernot Katzer)表示,这个词的来源不明,就和目前尚无法辨认的香料“amomon”以及肉桂(kinnamomon)一样。其中一种可能的假设是,“amomon”指的是香豆蔻(Amomum subulatum),也就是在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与锡金生长的大型小豆蔻,但是欧洲罗马时代之后就不再食用。
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使用小豆蔻的历史相当古老,今天人们依然经常使用。其实今天许多贝都因游牧民族所使用的咖啡壶,在壶嘴处都有个小空间用来装小豆蔻荚。虽然我在中东的阿拉伯近亲并非贝都因人,但他们也一样喜爱小豆蔻。我在黎巴嫩贝卡谷地(Bekāa Valley)任何人的家中,小豆蔻好像会飘进每一个咖啡杯、米布丁(roz bi haleeb),甚至部分早餐吃的面点(man’oushè)中。在黎巴嫩,普通咖啡称为“mazbûta”,通常搭配点小豆蔻粉,以及一两滴的橙花水。
小豆蔻是许多重要的混合香料的主要原料,包括也门的左格香料,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巴哈拉特(Baharat),印度咖喱粉、印度奶茶与腰果酱,以及马来西亚的马萨拉。小豆蔻荚可和杜松子、肉桂搭配,加入特制的琴酒中。
【注释】
[1] 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 1304—1377),出生于摩洛哥,史上最伟大的旅行作家之一。
[2] 乔治·法德洛·胡朗尼(George Fadlo Hourani, 1913—1984),是黎巴嫩船商之子。
[3] 亚伯拉罕·乔舒亚·赫舍尔(Abraham Joshua Heschel, 1907—1972),出生于波兰,后移居美国的拉比。拉比(Rabbi),有时也写为辣彼,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Judaism)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