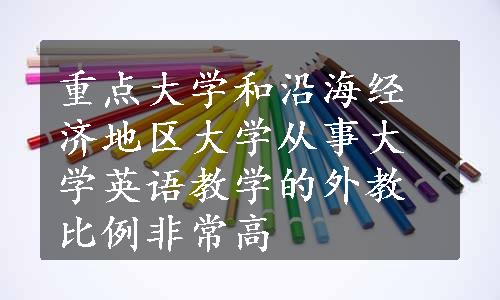
一、师资质量
根据我们在2002年对十所重点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和其他331所取样学校进行对比,发现前者的教授平均比例为7.9%,副教授平均比例为30.75%,而后者的教授平均比例为3.3%,副教授为22%。在学历方面,前者35岁以下的大学英语教师中的硕士研究生平均比例为58.1%,博士生比例为2.3%,而后者同一层次中的硕士研究生比例为21.7%,博士生比例为0.25%。
重点大学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学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的外教比例也非常高。浙江大学10名,清华、复旦等大学常年保持外教5到6名。在培训教师方面同样如此。复旦大学每年有7到8名教师出国进修一年,华南理工大学分期分批把所有大学英语教师送国外轮训。此外,这些大学的归国留学生,专业人才的引进规模都大得多。这些师资情况不仅有力保证了学生说、写交际能力的培养,也保证了高质量地用英语开设专业课。
如果从所调查的所有341所学校来看,师资质量也极不平衡,总体是比较低的(见下表)。
表5 大学教师中各职称人数及比例

表6 大学英语教师学历情况及占教师总数比例

表7 35岁以下大学英语教师的学历层次情况及占青年教师比例
 (www.zuozong.com)
(www.zuozong.com)
表8 外籍英语教师人数情况(2001学年)

教师中具有学士和学士以下学历的高达76.7%。可见就学历而论,我国大学英语教师的质量在全世界可能是属于低的。美国、中国香港、韩国和日本的大学外语教师的博士学历都高达到80%—90%。“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83%外语教师获得语言学或文学博士学位,17%获得硕士学位。即使个别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也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一旦通过,就可获得博士学位”(董耐婷,2005)。
出现师资质量较低、学历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文革”造成了几乎一代英语教师的断档。从1968年到1982年,我国几乎没有培养任何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更不要说硕士生。第二,语种选择的失误对教师质量的影响。50年代初,原先的英语教师纷纷改行,放弃专业,去教授俄语。70年代,大批俄语教师又经过短期学习后改教英语,这样的反复折腾对师资质量的提高带来严重的影响。
应当承认,最近十几年,我国外语教师的学历程度在不断提高。但是学历程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教学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外语教师总体素质还是较低的”(戴炜栋等,2001),个中原因是我国外语教师大多是为了解决职称去攻读学位的,而不是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去学习的。出于功利性动机,只要是博士,什么专业都可以,因此不少青年教师借助自身英语的优势去攻读法学、哲学、中文等博士学位。即使读英语的,也多倾向于英美文学专业或翻译专业或理论语言学专业等。国内读硕士和博士的人较少去读和外语教学水平提高直接有关的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教育心理学、教材开发、测试学、教学法研究等课程。如(根据北京大学2005年度“国家精品课程”申报表)北京大学英语系大学英语教研室申报教育部“大学英语”精品课程的教师团队共有23个教师,其中有教授8人,副教授9人,讲师6人。博士生导师3人,博士5人,在职博士生6人,其余皆硕士。可以说,这样职称和学历的大学英语师资队伍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但从他们所填写的研究方向即学科专业来看,真正搞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的只有两人(见下表):
表9 北京大学大学英语教师研究方向

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就是以二语习得理论为核心的教育语言学这门在西方较成熟的学科在中国还未被重视。一种观点似乎在国内占了上风:只有从事理论研究,如生成语法研究、功能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等,才是真正搞语言研究的,而应用语言学,以及二语习得研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只要统计一下我国外语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二语习得研究的论文数量,统计一下我国院校开设二语习得理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课程数量,就不难得出此结论。
根据俞理明等(2004)研究,在西方,甚至在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各种不同层次的以外语/二语教学为主干的应用语言学(含TESL/TESOL)课程发展很快,从一星期的证书班到长达五年之久的博士学位课程应有尽有。以研究生课程为例,1996年,在北美各大学里开设了39个硕士和博士课程,而到了2000年,这样的硕士课程有73个,博士课程为29个(www/aaal.org)。
看到现在这么多大学英语青年教师在读博令人高兴,但看到他们的研究方向,我们不能不呼吁:再也不要干这种费时低效的事了。要真正提高我国外语教学质量,培养语言教学人才,就必须大力建设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我们建议,对在职教师,要免除入学考试的门槛和必须发表论文的限制,让只要愿意深造的教师,都能攻读这些学位课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