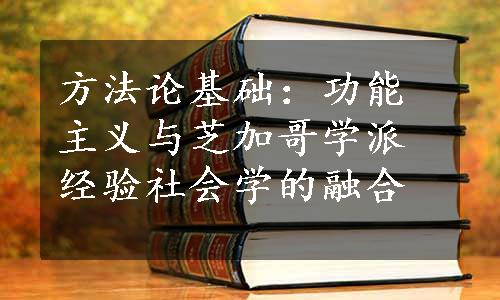
任何一个学者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后必定有着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作为学理支撑,雷德菲尔德的农村社会研究也不例外。简言之,将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经验社会学有效融合后的主题升华是雷德菲尔德农村社会研究的方法论背景,也是他此项研究的最大特色,这一点从前述几部著作的书名中也可窥见一斑。那么,雷德菲尔德为何会倾心于功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经验社会学,他是如何继承并在哪些方面有所超越后用于自己的农村社会研究?要厘清这些,就不得不先行说明雷德菲尔德的师承关系,以及功能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学术版图中所居的统治性地位。
前文已有述及,雷德菲尔德求学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该系乃美国第一个(在很长时间内也是最好的)社会学系,由斯莫尔(Albion Woodbury Small)于1893年创建,并在此后经帕克(R.E.Park)、伯吉斯(E.N.Burgess)等人的共同努力而形成蜚声学界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帕克和伯吉斯合创人类生态学这个以“人和社会机构的地理分布的形成过程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和规律”[5]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分支。芝加哥学派将人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定名为“社区”(community),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之间也就是群体内部形成所谓共生关系(symbiosis),而社区则是观察社会整体发展和演变趋势的缩微“单元”或曰“模型”。
在社会学发展史上,芝加哥学派经验社会学一改此前韦伯(Max Weber)、齐美尔(Georg Simmel)、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人过于纯粹的理论社会学取向,透过社区研究和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转向以正在发展和兴起中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直接面对工业化后美国城市中的各类社会问题。“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绘出一个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6],也正是在社区分析这方面,人类学与社会学有它们相通的一面,而雷德菲尔德之所以进入人类学研究天地,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受到来自帕克的指点和提携之故,两者存在明显的师承关系。对于芝加哥学派的这一整体学术风格,雷德菲尔德不仅受其熏陶,而且沿用了社区研究方法,并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这两点都成为他日后农村社会研究的显著特征。
另外,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主义也为雷德菲尔德自身的学理建构提供了源头活水。
19世纪的最后25年,社会人类学这个名称在英国开始被使用,第一个获得社会人类学教授头衔的乃《金枝》作者弗雷泽(J.G.Frazer)。[7]起初,社会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一同被当做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学科,但到了20世纪初的西欧,已逐步从广义的人类学中分离出来而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虽然学科主体性日益增强,但研究对象却一仍其旧,主要还是研究欧洲和美国以外的落后地区。“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在30年代前一直以当时欧洲人称为‘野蛮人’作为研究对象”[8],社会人类学事实上被等同于“野蛮学”。
与此不同的是,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雷蒙德·弗思三人通过自身研究,有力改变了这一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和白人优越论调性的学科取向,逐步将社会人类学从对野蛮人的研究过渡到对文明人的研究中来,强调研究者不应为猎奇而写作,而要亲身参与当地人的生活和劳作,并对其进行密切观察。问题的答案不能求诸社会之外,而只能从社会生活的内部寻找,具有直接观察、重视民间生活、民间知识和亲自参与等特点。(www.zuozong.com)
马林诺夫斯基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划分为“文化”与“人的基本需求”两大类,“他认为社会人类学者的使命在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人的文化性,制度性的活动与人的基本需求之间的关系”,而功能指的是“文化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或满足机体需要的行动”[9]。需要导致文化的产生,文化又反过来满足需要,文化之所以重要且是一个完整体系,在于它能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功能主义主要关注“个体行为,关注社会制度强加给个体的限制,关注个体需求与那些需求通过文化与社会框架实现满足之间的关系”[10]。功能学派认为一切制度、习俗和信仰之所以能够存在,皆因其对社会有独特的功能。与历史学派挖掘过往史实相比,功能论解释更加着重于怎样说明一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只不过是人类普遍规律的一个例子。在研究中,功能主义与芝加哥学派经验社会学类似,也采取社区研究法。[11]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功能主义被独尊为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唯一科学方法,且被它的提倡者视为一种“科学”而非“学派”[12]。
对于功能主义,雷德菲尔德可谓心有戚戚焉,这可以从他对社会人类学发展进程的评述中得到验证。在检讨与反思的基础上,雷德菲尔德根据已有经验,结合农村社会实况,针对功能主义在研究中的具体运用做了进一步的阐发。
在雷德菲尔德看来,包括泰勒(E.B.Taylor)、弗雷泽和麦克伦南(Mclennan)等人在内的早期人类学家在著述中都存在“泛泛而谈”的弊病,“找不到有关某一具体的人的群体的总体生存状况的论述材料”[13]。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海登(A.C.Haddon)、里伏斯(H.R.Rivers)、波亚士(Franz Boas)则主要是研究世界上仍鲜为人知的区域和人群,如海登和里伏斯对地处大洋洲美拉尼西亚的托里斯海峡所做的考察,波亚士对爱斯基摩人的系统调查。只有到了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于1922年分别出版《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人》[14]时,社会人类学研究的路径才被正式确定下来——也就是研究者本人只身远赴人迹罕至的地区展开社区调研工作,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生活,体验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从而在整体上把握这一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形式。
雷德菲尔德以“抽象的形象“来概括这一研究方法,毕竟学者不可能穷尽所有社区,对某一社区的实地研究虽无法涵盖全部,但这一学者研究中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却有助于认识整体。个别社区所呈现出的面貌与社会现实并不矛盾,社区研究能够成为很好的社会“镜像”,所谓“众出于一、异中见同”!这些经抽象后的形象之所以对研究非常有用,恰恰在于它们与具体生活状况保有一定距离,“尽管一个事务的‘抽象的形象’在许多特定的方面存在着与实际事物的明显差异,但它却在整体上比现实中存在的具体事务更具有真实性。”[15]为了做好社区研究,雷德菲尔德认为社会人类学学者“必须成为一个具有通晓整个社会科学这个大领域里的所有学科知识的百事通”,能够熟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立体观照整个社区。在此基础上,雷德菲尔德继续提出要跳脱单一小型社区,转向研究较大群居体,这两种研究之间也并非决然不相往来,而是存在紧密关联。如据现实参照,“小型社区—较大群居体”其实就正对应着“农村社会—城市”,这也说明雷德菲尔德开放式的研究态度和整体联系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