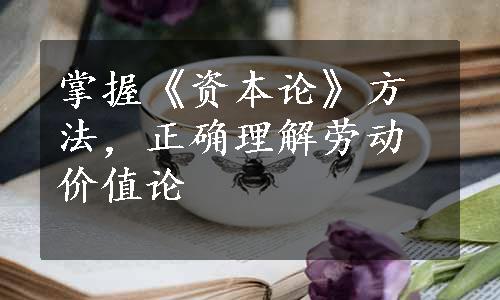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应该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是要像邓小平在讲到研究毛泽东思想时所多次强调的那样,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随意曲解;另一个方面则要结合新的实际,对劳动价值论加以发展。在这两个方面工作中,前一方面工作是前提,前提没有搞好,不仅会损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基础”[1],而且也使后一方面工作失去了依据和方向。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出版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著中,有一些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尚有很大的距离。下面对一些观点试作粗浅分析。有一本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在批评劳动价值论的偏颇时,认为马克思未能正确理解价值和价格这两个范畴在历史上和理论上的关系。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始终是一个本质的事实和唯一的存在,而价值不过是价格中的一种形式,即长期价格水准;只有从价格的存在和变动去探求和说明价值,而不是相反;价格决定比价值决定层次更高,更带普遍性,价值决定原理理应从属于价格的决定法则。笔者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对《资本论》方法的理解上存在三个偏差:
一是不了解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事物的本质是由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而现象则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尽管事物的本质隐藏于事物的内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是价格的本质,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他说:“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物的名称对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2]尽管在价格表面上找不到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但是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3]如果把价格作为本质的事实和唯一的存在,那么:第一,不懂得本质这一概念的含义,价格作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态,只能是现象,不可能是本质;第二,把价值合并到价格,这一唯一的存在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价值这一本质,这不仅是对劳动价值论进行釜底抽薪,也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常识;第三,经济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成为多余的了。
二是不了解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虽然先论述价值,以后才论述价格,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价值前,没有进行过价格研究。恰恰相反,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之前和过程中,收集了大量有关货币和商品价格的历史和现实的材料,做了深入的研究:“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从抽象的简单的价值规定,再逐步达到价格这一“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4]。前一行程属于研究过程,后一行程属于叙述过程,它们所采用的方法是有区别的。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上述观点作者指责马克思没有从价格的存在和变动去探求和说明价值,说明他对马克思在“价格的存在和变动”方面做过的大量研究视而不见,并且把《资本论》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为一谈了。
三是不了解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三节“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明确指出,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6]商品及其价值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很抽象的范畴,但“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7],即不仅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而且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商品生产,因此具有很大的普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的生产价格,是一个较价值具体得多的经济范畴,它的适用性和普遍性比起价值就窄多了,只能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因此,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8]如果不了解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会得出价格到处都存在,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很密切,因而比起价值更具有普遍性和决定性的肤浅结论。
在前面提到的那本著作中,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存在“局限性”,就是因为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实物交换的场合”。笔者认为,该作者之所以做此断言,是因为他不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分析商品时所应用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辩证方法所造成的。
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又加以批判改造,并应用于《资本论》的一种辩证方法。1859年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称该书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初篇)出版后,恩格斯写了一篇著名的书评。在书评中,恩格斯针对马克思“从商品开始”的分析,写道:“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就来分析这种关系。……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期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9]恩格斯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为《资本论》逻辑分析起点的商品是同商品生产历史的起点相一致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理论抽象。这样就同黑格尔的历史无非是绝对的规定和理念的实现的唯心主义观点彻底区别开来了。第二层意思是,作为《资本论》逻辑分析起点的商品,不仅同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相一致,而且还同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相一致。恩格斯所说的“从历史上……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以及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的过程,指的就是人类社会商品生产史;而“从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以及“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史。
正因为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同两种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相一致,所以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中,就同时存在有关两种商品生产的论述。关于人类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马克思在第一章谈到商品的最简单价值形式时指出:“很明显,这种形式实际上只是在最初交换阶段,也就是劳动产品通过偶然的、间或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的阶段才出现。”[10]在第二章“交换过程”中,又进一步指出,商品交换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仍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11]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马克思的论述就更多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2]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的商品——产品的这个特殊的社会形式出发。”[13]“货币和商品是我们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时必须作为出发点的前提。对资本的进一步考察将表明,事实上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表面上,商品才表现为财富的元素形式。”[14]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与两种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相一致,会不会自相矛盾呢?不会的。因为其中后一个一致是主要的、基本的。虽然在开篇中马克思暂时舍象资本的关系,从商品的纯粹形态上来考察,但这不意味着它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马克思说,“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为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15]。《资本论》开篇的商品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和“个别的侧面”,这是我们“应当时刻把握住”的。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发展也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人类社会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发展,正如现代社会个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缩影一样。因此,作为《资本论》逻辑起点的商品在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相一致的同时,自然也与人类社会商品生产历史的起点相一致了。认为劳动价值论适用范围仅限于实物交换场合的作者,只看到《资本论》开篇有一些关于人类社会商品生产历史起点的论述,未能把握马克思所应用的科学方法,就轻率地做出了不符合《资本论》原意的结论。这进一步说明,在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时,掌握《资本论》所应用的辩证方法,是多么重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16]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上面提到的那本书的作者,也认为马克思对其劳动价值论的最完整最系统的论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做出的,为此他将劳动价值论的内容概括为三点,即商品二重性学说、劳动二重性学说、价值形式学说。笔者认为,对劳动价值论的这种界定,显得太简单、太片面了些,这里也涉及对《资本论》在阐述劳动价值论时所应用方法的理解问题。依笔者拙见,马克思的“最完整最系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肯定、继承和批判、改造。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以此为武器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能“从这个基础出发……去揭示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17],最终导致理论体系的破产。马克思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非常重视采用批判的方法,摒弃前人研究成果中的非科学成分,吸取其中的合理内核,并结合新的实际,发展和超越前人的理论。这种批判的方法,在哲学上称之为“扬弃”。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18]。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批判”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马克思1857—1858年创作的经济学手稿(后人称为《资本论》第一稿),名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正式出版经济学巨著第一卷时虽然改用《资本论》这一书名,但副标题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说明,马克思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无从区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联系和区别,就不能真正了解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伟大意义。以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为例。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的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19]“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20]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所做的“批判地证明”,应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关于劳动价值论最简单、最抽象、最一般的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采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所论述的劳动价值论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21]正因为简单,所以它所研究的“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22]“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就是“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23]。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象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似乎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这种一般不是普通的一般,而是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本质的一般”,它是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即“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24]的一般。有的论者把《资本论》开篇的商品交换理解为原始社会末期的实物交换或者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商品交换,就是因为不了解它实际上已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的一般”。
三是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具体化。这里所说的具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是多样性的统一”。[25]也就是说,随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的一步步深入,劳动价值论也愈益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由简单的一般的规定转化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这里举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界曾多次讨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单个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提出的;所谓“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某种符合社会需要的商品总量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中提出的。有的论者不了解《资本论》所应用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把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硬地对立起来,从而得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缺乏一贯性和彻底性的错误结论。有的文章这样写道:马克思“在建立劳动价值论时,坚决地排斥‘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而当需要将‘需求’引入理论来解释‘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已在通过‘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又回到‘需求也决定价值’(而不是决定价格)”,由此造成了马克思理论体系内部“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26]。笔者认为,只要了解马克思所应用的方法,这里存在的所谓“困惑”就可以得到澄清,所谓“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也就不复存在。其实,所谓“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属于劳动价值论第二层次的内容,它确实是把供求关系暂时舍象了,但是这并不影响其结论的正确性,就像伽利略在研究自由落体定律时暂时不考虑空气的阻力并不影响其结论的正确性一样。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属于劳动价值论第三层次的内容,劳动价值论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步引入原先被舍象掉的“许多规定和关系”,包括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使得由劳动价值论决定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变化与人们每天耳闻目睹的经济现象大体相符合。上述“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后人概括出来的,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因此,依据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行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不一定局限于“两种含义”,还可以有更多种含义。例如,最近有一篇论文,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为四种:第一种为生产同种商品的同行所要求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为从社会效益上要求一种行业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须符合由社会总劳动分配给该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三种是从产业结构动态平衡角度要求各行业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是耗费在社会需求总量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四种是“世界市场”要求的世界(人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7]这一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它给我们的启发是:不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由抽象到具体逐步展开,劳动价值论的其他方面的抽象规定,如作为逻辑起点的商品、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商品拜物教等也都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其所包含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趋于具体。
上述劳动价值论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内容是相对独立、有所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一个有机整体,第一方面或第一层次的内容是劳动价值论的来源和前提,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的内容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三方面或第三层次的内容则是劳动价值论的展开和具体化。按照这种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就不能仅仅局限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或第一篇中,应该包括《资本论》全四卷和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只有掌握了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真正了解劳动价值论。
(原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9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24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www.zuozong.com)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7—19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12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页。
[16]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64页。
[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页。
[26]樊纲:《“苏联模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27]胡培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今解》,《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7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