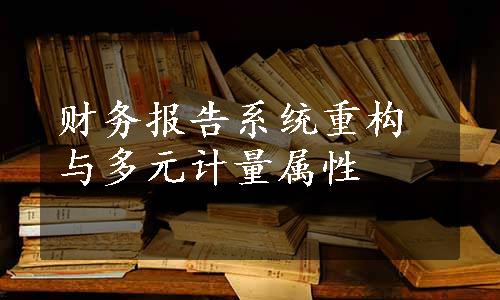
当我们强调财务报告真实、公允地反映一个报告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时,我们假定企业经济活动系统与会计系统相对独立,经济活动系统发生在前,会计系统在后;会计系统接收经济活动系统所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信息,按照会计规则进行记录、处理(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与报告;信息使用者基于这些信息做出相关决策;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如历史成本或公允价值),只是导致会计系统所报告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不同,经济活动系统行为相对独立于会计系统,不会受到会计系统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财务报告的性质就是一种事后提供信息的工具,它不会、也不应当影响到经济活动系统的行为。也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曾经提出全球统一会计的设想,并认为,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事项,不论在全球何时何地发生,都应当按相同或相似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报告,并予以基本一致的解释。
从实际经济运行角度来看,会计系统是整个企业系统的一部分,它与经济活动系统之间并不必然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当管理层的考核——这是信任活动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是以会计系统所报告的信息为依据,管理层自然会关注,甚至干预会计系统的运行,包括最终财务报告的生成。我们所熟知的盈余管理,就认为会计系统并不必然独立于经济活动系统;盈余管理的研究发现,管理层除了采用干预会计政策等方式来管理盈余信息外,他们还可以借助实体经济活动安排,来影响盈余。比如,当会计准则要求将所有研发费用资本化后,一些对利润比较敏感的公司,就会降低研发支出,以求得比较满意的报告利润;美国的一些研究发现,鉴于APB要求企业并购必须满足12项条件,才能够按照权益结合法进行会计处理与报告,为此,很多企业并购专门按照这12项条件来设计,即便收购方因此多支付百万乃至千万的成本(Lys and Vincent,1995)。正如Ball(1995)所言,会计是企业契约成本的一部分,改变了会计,就改变了企业的行为。
当我们将视线投向现实经济活动及其运行,我们就会发现:财务报表不仅仅是一种事后反映报告主体经济活动状况与成果的系统(或工具),财务报表本身还会受到公司管理层及其他相关各方的干预,使得财务报表信息不再仅仅是一种事后反映。Graham et al(2005)访谈了267位公司财务负责人和134位CEO,发现之一是:这些经理人员都认为,管理层会为了各自的奖励以及在经理人市场上的价值等,进行诸如盈余平滑或达到分析师的预期等盈余管理行为。这时,财务报表就不再仅仅是对报告主体经济活动的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它还承载着对管理层能力的评价、市场分析人员对公司发展的预期判断是否准确等等信息。很显然,这时的财务报告系统,也不仅仅是采用历史成本、提供单一报告所能够胜任的。
回到会计价值的讨论上。如果维系经济社会人类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会计的核心价值,放弃交易基础的、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采用价值基础的、广泛应用重估价(revaluation)方法的会计计量模式,未来会计的可验证性渐渐缺失。而到目前为止,可验证性仍然是会计信息质量中最不可或缺的基础,失去了可验证性,会计信息在维系利益各方之间相互信任的能力也将逐渐丧失。果如是,则未来会计存在的基础将会逐渐丧失。会计的核心价值不能、也不应该放弃!
但是,如果我们为了维护会计系统的核心价值——维系人类社会的信任,而拒绝对财务报告系统进行改造,让其同时也能够服务于社会财富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这无疑将限制了会计的发展,让其落后于时代,甚至会被社会所淘汰。
易言之,完全放弃财务报告的传统内容,或固守财务报告的传统,都不是会计系统的应有之道。从会计学科乃至会计职业的生存与发展路径来看,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重构财务报告系统,让其能够同时服务于多种目标的需求。(www.zuozong.com)
幸运的是,现有会计系统为了适应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框架:基本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其中,基本财务报表是整个财务报告系统的核心,它应当取自历史成本信息(或者说,交易基础的信息),将客观、可验证性作为首要的信息质量基础。这套信息相当于是传统的财务会计信息,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与报告主体相关的各利益方的利益需求。如果某个利益方对历史成本基础的报告信息有疑问,它可以借助可验证性这一标准,追溯到信息的源头:真实交易或事项。这套信息必须要经过独立审计,才能够向社会公开发布。
由于现代社会财富总体上处于流动状态,与报告主体相关的各个利益方,其利益并不仅仅与过去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有关,任何关于报告主体现在的状况、未来可能的变化信息,也会影响到报告主体相关方的利益。会计系统不能够、也不应当抱残守缺,忽视这部分需求。为此,可以考虑在基本财务报表之外,提供派生的财务报告,我们也称之为其他财务报告。管理会计在讨论不同的成本属性时,提出“不同目的,不同成本”。借用这一思想,其他财务报告也可以“按需订制”,根据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对基本财务报表信息进行再加工,它们可以背离历史成本,采用诸如市场价格,甚至预计价格等非历史成本计量属性。比如,资本市场关注短期投资与套利交易的投资者,与公司长期债权人(如西方市场上的动辄长达15年的公司债)相比,他们对财务报告信息的需求应当是不同的。其他财务报告可以针对这些各异的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设计出能够较好地满足他们需求的财务指标体系,而不再是目前这种通过表外、文字叙述的方式加以介绍。
传统财务报表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可验证性,外部审计师的介入并进行审计行为本身,就表明可验证性的意义与价值。其他财务报告是对基本财务报表的再加工,如采用包括一些数学模型在内的估计价格所确定的信息,可验证性程度不断降低。这时,再对派生财务报告信息进行审计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对这部分特定使用对象来说,提供经过审计的基本财务报表,同时,充分披露派生报表的生成过程(如对重估价项目所采用的重估价方法、价值估计或判断标准;对按照数学模型计算推定的资产、负债项目如期权项目,详尽披露计算过程所需要的各项参数的采集过程),让使用者可以据以自行衡量、判断其他财务报告信息的价值。
针对同一个项目,采用多元计量属性,报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数据,最终导致同一个企业出现两套以上的财务数据,这会对人们业已形成的、关于财务会计与财务报告的传统观念产生冲击。毫无疑问,多重财务报告体系产生的初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混乱。例如,2004年5月,媒体发现厦门航空在南方航空与建发股份的报表上利润、净资产相差甚远,并推定认为至少有一家错了[9]。这需要未来一段时间,会计职业界能够向社会详细介绍不同财务报表/告体系的特性,让社会各界能够逐渐理解并接受“不同目的、不同报告”的特征,逐渐理解并接受同一个企业、同一期间,按照不同标准可以生成金额不同的利润或资产指标。
回到本文开篇所引用的次贷危机中国际社会,特别是金融界对公允价值会计的批评。按照他们的意见,因为采用公允价值,让一些金融机构账面损失加大,导致不符合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此为理由,他们反对采用公允价值。这一辩解假定: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是完全基于财务报表的表内数据,他们绝不考虑表外补充信息对金融机构经济安全的可能影响。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表内确认与表外披露是否会影响到投资者的行为,仍然是一个行为层面值得研究的话题。同时,如果说监管部门是理性且理智的信息使用者——包括巴菲特在内的很多机构投资者也应当如此,他们完全有能力对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所有公司提供的基本财务报表信息进行再加工,生成满足他们需求的、派生的财务报告信息,以便更有效地监管或进行投资决策。因此,即便金融机构不在表内确认实际上已经发生的损失,监管机构也应当能够“看穿”这种会计处理上或分类上的差异。从这一意义上看,以基本财务报表为主、多套财务报告并存的模式,在实践中或许已经存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