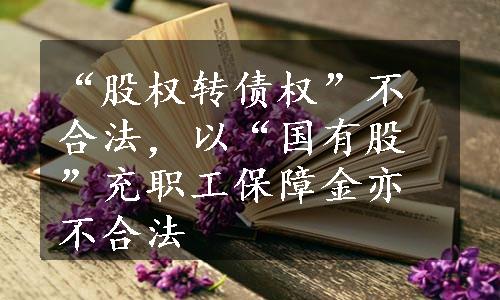
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在严肃的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上,按法制规范来进行。
涉及资产的所有权及各种权利关系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于那些号称“新制度学派”在中国分理所主持人的“著名经济学家”,应当非常清楚法制的重要。他们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批评,主要一条,就是“产权不明晰”,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一句“明晰产权”。他们在美国、英国的导师们,在教授他们“产权理论”、“科斯定理”的时候,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合法、守法。否则,制度学派何以立足?他们在美、英等国求学谋生时,大概也不敢违反人家的法律吧。
回到祖国,不仅原来的意识被清除了,就是所学来的东西,也只剩下形式——或者本来就学来一些形式,并变成简单口号了。求学时的谦卑,变成了高傲。张口闭口美、英如何,似乎那里是人间绝对真理,中国则一无是处。他们作为绝对真理派来的代表,就是要按绝对真理的标准将中国彻底变个样。至于能否做到,那不是我的事,我只管说,反正你们也不知道绝对真理为何物,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他们最热衷,也最拿手的,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了。以“产权理论”为根据,以“明晰产权”为标准,大发议论。而那些被国有企业的麻烦弄得不知所措的人,听到如此灵丹妙药,不免心动。反正我本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只要能让我摆脱这个麻烦,又有我和我的利益,就可以用这副药。也正是这供求二者的统一,使“明晰产权”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点”。
我是在1996年夏指导一个学生写参加“挑战杯”的论文时,才注意到被炒得焦糊的“产权”这一术语。不免用概念的标准加以衡量,发现其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准确,达不到概念的标准:“产”字之义颇多,生育、生产、创造、发明均可称为“产”,而他们用“产”所表示的是“财产”,或者说“产权”是“财产权”的简称,但这个简称实在让人莫名其妙,远不如“产妇”、“产业”、“产品”清楚。当然,英语念多了,能认得汉字就不错了,我们也不必深究人家说的字眼。“产权”如此,“剩余”也是一样,神仙知道它是什么含义?但因为是绝对真理的代表说出来的,我们也只有怨自己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但即使是将“产权”理解为“财产权”,也是不能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论证的,“财产”外延之大,包括了地球上几乎所有被人以其劳动改造或武力,甚至意念征服了的一切——近来已经有人在谈“太空产权”了。具体到企业,就是按私有制原则,也是“资本所有权”,或“资产权”,不能用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更不用说语词表示不清楚的“产权”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包括劳动力所有权。从民法原则讲,经济权利实际上只是一个,就是所有权,其他各种权利都是所有权权能的分化和派生。
在西方国家,大陆法学受古罗马法传统的影响,是比较明确地规定了私有制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各种权利关系的,这在《拿破仑法典》中有充分体现。当然,这部在资本主义制度初期制定的法律,到现在已显示许多缺陷,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没有把占有权定位为权利体系上的一个主体权利,仍在把占有视为所有权的一个权能。英、美法系在本质上与大陆法系是相同的,但在术语及表述上并不严格,上面提到的“产权”一词,就是如此。但这种不严格也有其方便,科斯等人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占有权的论证,以及“委托代理”关系的探讨,都只针对“产权”,但他们把“产权”分为多层面或者说切为若干块,每层每块都是“产权”,还有好事者用“博奕论”来界定它们的关系。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承认所有权的根本地位,并坚持法制原则。
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一系列权利,从民主法制原则讲,是不完善的,但并不等于没有所有权及其派生的权利关系。不论是从“全民所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其规定虽不明确,但所有权是存在的。实际上,国家在以所有权主体名义对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的控制,也在法律上发生效力。
国有企业改革,从权利关系或所有制而言,就是明确和理顺其所有权与它派生的各种权利的关系,以法律界定它,以法制保证它。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要从事的国有企业改革,与美国制度学派所促动的私有资本企业改革——其实质就是以公司制集合私有资本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并由它控制经营权——在一般意义上是相同的。
我相信这一点,不论是凡勃伦、康芒斯,还是科斯、诺斯,如果生在中国,并以他们的“制度经济学”——可以称为“法制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问题时,虽然能指出旧体制的诸多不完善——就像他们批评美国私有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一样,但总要坚持法制,并注重维护所有权的根本权利地位。
可是,那些号称“制度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们,却从根本上放弃了所有权,放弃了法制,不顾一切地宣扬“私有化”,并把“产权明晰”解释为对国有企业统一权利体系的分块割切。这里,他们所提出的所谓“法人产权”,就是典型。企业法人,即企业经营权的法权表现,是企业在对外交往中的法律代表。“法人产权”,实为法人所行使的经营权。可是,在“产权改革”派笔下,却成了“法人所有权”,即经营者拥有的一部分所有权。仅这一条,给国有企业的经营造成的影响之大,就是无法估量的。那些本来不善于经营管理的经营者——实为行政长官——从这种“产权明析”中看到了希望,即进一步“改革”,他们就可以成为企业的所有权主体,起码是控股人。于是,更加紧了“内部人控制”,并以日益下滑的效益来要挟政府:只有将“产权”更多地交给他们,这个企业才能存在下去——当然还会大发展!
顺着这个思路,又有人提出了“劳动雇佣资本”,以至“股权转债权”的建议。
“劳动雇佣资本”论中的“劳动”,并不是国有企业的职工,而是经营权的行使者。在西方国家的私有资本公司中,他们也是被雇佣的劳动者。现在中国的“改革家”把关系颠倒过来: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本。
刚听到这个说法,还觉得是哪个“极左派”人物提出的新口号,与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待了解了其要旨,才知道不过是要化国有为私有的一种技巧。
劳动怎样才能雇佣资本?其法理何在?(www.zuozong.com)
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关系和矛盾,它实际上是两种所有权主体之间合法的交易:资本所有权主体以其货币购买劳动力所有权主体的劳动力使用权。厂长、经理等经营权的行使者,也是以其特殊的劳动力使用权,来交换资本所有者的货币。
那么,“劳动雇佣资本”的关系如何理解?是经营权的行使者以其劳动力使用权交换资本的所有权吗?虽然此交换关系只是颠倒了主动与被动两方的地位,但经营权行使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怎么可能成为交换的主动方面?他又以什么付给被其“雇佣”的资本所有权以等价货币?给货币吗?如果经营者有等量货币,为什么还要拿它来买等量的同质的货币?
迄今为止,不论西方、东方、南方、北方,乃至中国的私有企业,都不可能是“劳动雇佣资本”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根本不存在其现实性的逻辑,又怎么可以用到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造中呢?同样的道理,国有企业现有的经营者凭什么、用什么来交换国有企业的资产呢?不能付出等量的货币,还是什么“市场经济”?又怎么谈得上是“雇佣”呢?
退一步说,即使让经营者不花一分钱就“雇佣”了国有资产,他就成了国有企业新的资本的有权主体,那么,“劳动雇佣资本”关系就结束了,他又成了新的资本所有者,还要再雇佣劳动——包括新的经营者。这样的“改革”,意义何在?
大概只有一点:只要毁了国有企业,就大功告成。至于以后,谁管他洪水滔天!。
可能“劳动雇佣资本”论者也觉察到不花一分钱,“空手套白狼”,是不能使“劳动雇佣资本”的,于是想到了“股权转债权”这一似乎不违背等价交换原则的招数。
“股权转债权”,换言之,就是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变为类似银行贷款的债权。国家从原来的所有权主体变成债权人,进一步说,是将国家变成银行。这样,企业的经营者就成了资本所有权主体,他与国家的关系,也就变成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或者说,国家通过把所有权变成债权,将已经投入企业的资金作为贷款使经营者成为资本所有者。据说,这样可以减少“监督成本”,降低“交易费用”,克服“内部人控制”,从而增加经济效益,等等等等等。
但发明者却忽略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点——法律及其规定的权利关系。不论从私有制的法律,还是从公有制——它不过是“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或真正的私有制的实现——的法律,都要讲究所有权,保证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是其职工和全民,即全体公民,即令国家暂时控制了这个所有权,它也是国有企业的根本权利,谁能决定它变成债权?国家成了银行,全体劳动者都成了储户,这种变化的法权依据何在?至于说国家作为债权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企业,几乎没有半点说服力:既然庞大的国家机关都控制不了经营者,作为企业的银行又凭什么控制他们?今天的中国,欠债不还已成了某些经营者(特别是私有企业主)的习惯,“黄世仁怕杨白劳”,成为当今一大时尚,在这种情况下,谁又能保证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控制呢?
最近,又有一种削弱国有企业的路数,随着国有企业下岗、退休职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突出,而提了出来,其要点是:将国有企业部分股票变成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但不是变卖成钱成立基金会,而是仍以股票形式存在,或者说,由负责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的机构掌握这部分股票。其名曰:“国有股减持”。
这看来是在维护下岗、退休职工的利益,但其要点在于“国有股减持”,即削弱国家(及其尚在代表的全体公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至于下岗、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基金,当然要保障,但它在国有企业权利体系上,并不属于所有权层面,而在所有权派生的收益权上,以现有体制论,职工的这个收益权由政府集中行使,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向企业征税,二是由财政支付职工社会保障金。
国有企业的退休、下岗职工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等,如按社会主义法制改革以后,应由行使劳动力占有权的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从其分割的公共价值中支付。改革前则应统归政府来支付,现行的政策是由单个企业自己解决,这本身就与所有权(不论是归全民还是归国家)的决定性地位不符。
而“国有股减持”,以其股票充做职工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本身没有任何法权根据,国有企业的股票,是属于全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体现,有什么理由将其只用于职工劳动力所有权所体现的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全体公民并没有义务支付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金;而有义务必须支付的政府财政又不支付。
真不知想此招数者居心何在——他们提出这个招数的时候,正是中国股票市场严重不景气的时候,谁能保证以股票“一次性”支付给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金,不会随着股票价格的下跌而大大贬值?到那时,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削弱,甚至不存在了,而职工又不能靠贬值了的股票保障其生存,大概“改革”就成功了。
我并不想对“改革”国有企业的各种奇思妙想费过多的心思,只是通过上述几招的分析,说明这一点: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上进行,任何不合法的思路,都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
“改革家”们,下笔时请深思:法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