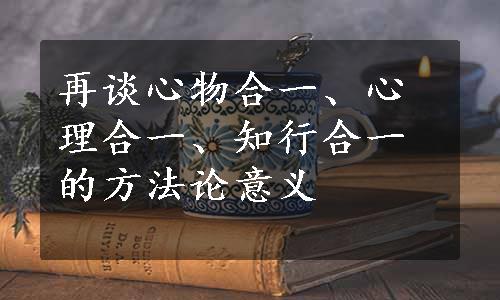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行动方式和思考方式。“天人合一的辩证法”乃是《道德经》首章所讨论的对象,就本文所涉及的论题,它委实关切的是“行动”(道)和“范畴”(名)的阴阳合一的辩证法问题。所谓“两者同出”,是言知行同体,浑然同一,皆出乎道;所谓“异名同谓之玄”,是言“阴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犹如马克思强调的劳动二重性乃是“政治经济学理解之枢纽”。然则,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经》和《资本论》的首章,在设计思想上确实具有很大程度的“逻辑同构性”。
以“无”为常,欲以观“运动之妙”。对象规定范围内包含的历史运动是“具体(运动)→抽象(构造)”,构成《道德经》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很显然,“具体存在——抽象存在”在运动结果不可能生成物质上的“心的结构”,而只能是产生出“心”能够把握的认识客体——主体社会。所以,研究对象只能是对象与思维统一的“行动”。全部的过程可以写成这样的历史行动路线:客体(对象)积极融入主体,构造自身为“实践对象”;这就是“主体的创世”。[49]可在思维看来,这是“客体”被主体所摄入,从而达到的对象根本上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实现的能动结合。继之,以“有”为常,欲以观“构造之徼”。仿造上述说法,研究对象乃是思维(主体)和对象本身的能动结合(思维被对象能动地摄入体内)。亦就是说,借助思维主体,对象变“研究对象”,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创生”。客体变出主体(依靠“客观批判”的行动),主体变出思维,对象变出研究对象,从而思维世界的规定(和客观世界契合的思想系统)才真正成行。作为行成系统,它试图主宰世界的运行,进而生成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生相克”的实践张力,但也同时衍生了客观历史世界的生生不息和无穷的知识图像。这个对象始终是这个实践的对象,所以出发点毋庸置疑是实践本身。应根据这个原则,重新综述王阳明学说中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它不是一个逻辑知识的描述,却是对“思维的统一结构”的一个描绘。把“主体社会”作为一个科学研究上的对象(即“思维之象”)来确定和把握,这是王阳明超出朱熹的地方。故此,在对象的演化路线上,王阳明肯定的是“自然之物”转向“社会之物”。“‘物’也不再是简单外在于知觉心的具体事物,而是相对于道德本心,是与人的道德实践相即不离的意向性存在,皆称其为‘物’。由此心物关系从人们日常习惯理解的认知关系转变为‘心’对‘物’之存在意义不断开显的意义结构。”[50]“阳明提出或建立‘心外无物’的原理,概括地说,通过三个环节作为中介,一是以物指事;二是从心上说事,即从主体方面定义事;三是通过意与物的关系建构起心外无物的心物论。”[51]所谓“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的心学所着力打造的就是“意之所在便是物”(物即是事)的哲学出发点,使之化为心的材料,但王阳明不否认外在具体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心外无物”并非一个认识论命题,而是具有内涵丰富深刻的实践论命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阳明侧重从心上说物,声称‘心外无物’。于是,心也就不是什么现成的东西:‘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能不离所,所不离能,即能即所,能所互生,心物也就在这一循环结构中相互争斗相互转让而复生了。”[52]
从“物的科学”对“事的科学”转化为起步,王阳明主张的认识论是迥异于自然科学的。这样,在王阳明看来,“心物合一”乃是社会科学的直接出发点,心物合一就是生产关系的“中国表达”(思维形式I)。“心”是统一的中国主体社会的思维范畴。“这里的‘物’主要指‘事’,即构成人类社会实践的政治活动、道德活动、教育活动等等。”[53]“大体说来,王阳明论心物关系有三个层次:一是心物循环论,将一切有关心物关系的‘自然观点’悬置;二是行为工夫论,以事为物,消心物于不‘积’之实行;三是生存本体论,于‘感应之几’处为前二说建立最后之根基。无疑,在这三层次中,生存本体是根,无它即无前二者。但行为工夫却是王阳明的‘立言宗旨’,即讲学目的之所在,因而也就成为重中之重了。”[54]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由物演(行动)通达心演(图式),但同时保证了“心外无物”,所以心物必须合一,这从行动本位上规范了存在范畴——它们是历史的“运动的合一”。
桥梁就是“感通”。既无离心之物,也无离物之心,训物为“事”,那“意之所在”背后立着的便是心的实践范畴了。在研究对象层次,“心”从“心物合一”关系中独立出来,成为天人合一的单独化的主体抽象表达形式,因为心不独是理的规定性(理是心的实体),按生成规定看,心是道和德的统一,是象的具象形式。物是行动的形象,心是思维(象的思维结构)的具象,至此,心理合一乃成为官僚社会历史形态的“思维表征”(思维形式II)。中国是“认识之成”的大国,而始能实现历史大治。[55]王阳明心学的理论奥妙就在于对行动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辩证统一,它是对研究对象范畴的逻辑规范。真正的象是在社会再生产中提取出来的;它在思维上是客观的、总体的。[56]这样才有意义和行动的生发,故而“在王阳明哲学中,心具有本体的地位,是价值的最终源头和存有论的最终依据”。所谓“心宰义”,即是说“阳明以心即理为宗旨时,他把朱子外在的天理标准转化为人人同具的良知”[57]。相应,王阳明心学理论——本质上是儒学社会理论——在使命上即是重建“阴阳”,实现了阴阳结构内“无”和“有”以及“抽象”和“具体”范畴(分别代表行动主义和思维科学)的“历史对话”。(www.zuozong.com)
王阳明从“万物一体”中取象,复归于“格者”(这导致王阳明以“正”训格),而又通过“心即理”进行思维的中介,直至通达“致良知”行动。这样,就完成了以再造秩序为己任的“批判的知识理论”。“就王阳明对《大学》‘八目’的知行分殊来看,王阳明将知行关系收摄为‘致良知’,以向内体认良知天理的‘致吾心之良知’为致知,以向外推扩良知天理的‘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为格物,以由内而外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为力行,力行践履的(主体)修养工夫贯穿格物致知的始终。”这是从完善主体的角度进行的知识生产创设。因此,“王阳明在格物致知中提倡的方法是由体悟良知本体的心体澄明,达到人情练达的世事洞明”[58]。其守卫“认识”的地方在于强调“知即行”(知行合一可看作与上述对应的“思维形式III”),成功地把无到有的生成运动反转为有生无的认识行动,从而也就完成了对知识范畴进行的行动规范。
根据以上综述,王阳明的学说事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第一,从与现代知识论接通的层面看,思维形式III是其体系的战略制高点,并且也是王阳明本人所热衷的“立言主旨”;第二,从与思维科学的可契合之处看,王阳明的体系精粹是思维形式II,因为它是和“天人合一”直接贯通的,也符合马克思抽象力的理论诉求;第三,从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对接之点看,就毫无疑问地要首推“心物合一”的假说了,因为思维形式I背后隐藏了中国的唯物主义的实质。本文更多是将思维形式II和思维形式III结合起来加以考量的,因为这尤其突显了王阳明和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上的历史继承关系——从中国角度,又在《道德经》和《资本论》之间搭建了可以信赖的逻辑联系。它表明思维科学一直是存在的,并在人类文明的总体建构秩序中以一个确定的方向在向前发展着,《资本论》委实是它的一次总体建构的成功!《道德经》是伟大的“第一次成功尝试”,王阳明心学继之作为“第二次成功尝试”;两次成功的尝试可以说为《资本论》提供最为扎实的历史文献根据,打下了思想根基。结合以上提及的三位伟大作家的著述,政治经济学批判范畴得以具象化,“它的完整含义包括:历史知识和历史支架;逻辑架构及其衍生的‘思维支架’作用;语言工具和认识支架”[59]。可以图像为如下逻辑之机理构造:
图2 思维科学——思维形式的运动和构造:对象·研究对象·知识逻辑[60]
所谓“思维科学”,在于肯定思维形式的客观总体性,揭示的就是思维的一般法则和一般规律。图中,居中的图形的“无”由左方的行程所规定,“有”由右方的行程所表现。在对象层面,思维范畴“抽象和具体”与存在(规定)统辖的“无”和“有”范畴对应;实际上在思维运动上,是以“无”规定“具体运动”,相应以“有”规定“抽象构造”。在王阳明体系中得到确认的则是“心物合一”,它们行动一体,故而“心外无物”,从中得到抽象思索的思维形式结晶——“心即物”。在研究对象层面,思维范畴“抽象和具体”与阴阳(规定)统辖的“抽象”和“具体”范畴直接对应,实现了人类思维上的对“天人合一”的知识内敛。在知识逻辑层面,思维范畴“抽象和具体”与批判(规定)统辖的“行”和“知”对应,从而“批判的知识理论”将抽象范畴和具体范畴变为可操作的“逻辑的知识”,即和形式逻辑构造对应的知识形式范畴(概念)。概言之,上图展示思维科学的内部秩序性,盖由“阴阳”统率,产生“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运动复归——运动不断重新出发、构造不断复归。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