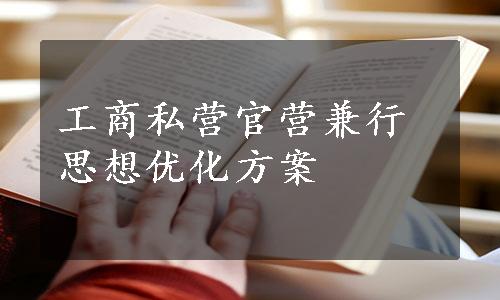
(一)欧阳修的禁榷与通商兼行思想
欧阳修作为宋代著名的士大夫,对工商业并不歧视,把它同农业相提并论,认为是治国安邦所不可缺少的。他说:“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钛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里。”[29]欧阳修对工商业究竟是采取官营(禁榷),还是采取私营(通商)的方式,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禁榷和通商两种方式,不可一概而论,应该看哪一种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证市场繁荣,货财流通,就采取哪一种方式,或者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使用。
对于兵器制造,欧阳修就主张国家集中经营管理。他认为兵器由各州、军分散制造,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与监督,加上各州、军工匠技艺不一,制造的兵器质量很差,“有打造成后,不曾经使,已修三五次者。修换既频,转不堪用,虚费人功物料,久远误事不细”[30]。因此,他请求朝廷于磁、相及邢州设置都造院,将各州、军所用兵器统一集中打造,“选得专一监官,拣择精好工匠,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赏罚,可以责成,兼亦易为点检者”[31]。这样由专官统一管理、监督,由技术娴熟的工匠按统一的标准制造,其质量就有保证。
对于民间小本工商活动,欧阳修则主张完全由老百姓自由经营,反对官府与民争利。他认为这些小本工商业如由官府自为,所得不多,而劳费甚大,又影响百姓的生计,公私双方都不利。如麟州原由百姓酿酒自卖,后来转运司禁民酿卖,由“官自开沽”。欧阳修经过了解,得知官榷半年,费本钱3500贯,而所得净利只1800贯;可是民间却因之“市肆顿无营运,居者各欲逃移”[32]。因此,他要求废罢官府榷酤,“令百姓依旧开沽,所贵存养一州人户,渐成生业”[33]。
对于商业活动,尤其是那些有一定规模的商业贸易,欧阳修则反对完全由国家垄断经营,主张采取国家与商人分利的方式经营,以提高效益,增加国家收入。
欧阳修指出,商人兼并势力“上侵公利,下刻细民,为国之患”[34],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但面对宋代当时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的现实,国家要想把商人完全从流通中排挤出去,由官府垄断和控制商业活动,已是不可能,而且对国家也不利。因此,欧阳修主张国家对商业贸易不应专利,而应与商人共利。实行与商共利政策,一来对国家有利。因为“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35]。二来可以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因为“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使商贾有利而通行,则上下济矣”[36]。欧阳修把国家与商人共利的方式比之为大商人与小商小贩的关系,“夫大商之能蕃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哉!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妒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取利少,货行流速,则积少而为多也。今为大国者,有无穷不竭之货,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宁使无用而积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贩夫;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若乃县官自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为,臣谓行之难久者也。诚能不较锱铢而思远大,则积朽之物散而钱币通,可不劳而用足矣”[37]。这里,欧阳修所谓国家与商贾共利,其实就像大商人让利于小商小贩。因为大商人往往经营大宗批发业务,然后通过把自己的利润让一小部分给小商小贩,使他们零售那些批发的商品给消费者。国家与大商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国家拥有大量的物资货源,也必须以让利的方式诱导商人进行分售。这样,国家虽然获利的比率减少了,但由于物货流通加速了,所以获利总额却比自售自销多得多。
总之,欧阳修能根据工商业不同行业不同情况而采取官榷、通商或二者结合的办法,体现了他对复杂的经济活动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务实灵活的精神。
(二)王安石的“榷法不宜太多”思想
王安石对工商究竟是官营还是私营,并不采取一刀切的态度,他不完全否定国家的经济干涉,但基本上还是倾向于采取放任政策,由民间经营。这就是“虽未能尽罢榷货”[38],但“榷法不宜太多”[39]。国家应放宽对禁榷的限制,让百姓自由经营,只征收工商业税。这样,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能促进工商业的发展。(www.zuozong.com)
在矿冶业方面,王安石不主张采取西汉桑弘羊的专卖政策。如当宋神宗提出榷铁时,他说:“若鼓铸铁器,即必与汉同弊”[40],主张由民间自由鼓铸。在王安石执政期间,不仅对铁没有采取专卖措施,相反还放宽了铜禁,准许民间自由铸造铜器并给予免税。在采矿方面,他废除国家强制“冶户”开采的办法,代之以招募百姓自由开采,国家则征收20%的实物税。“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41]显然,这种税制会提高冶户的生产积极性,促进采矿业的发展。
在茶的经营上,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私营。他认为“国家罢榷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贩,于方今实为便”[42]。茶在北宋时已成为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用品,“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而官府“所出皆粗恶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贩者”。因私贩者日多,国家虽严刑峻法,仍无法禁止。如将榷茶改为民营,不仅人民可食用好茶,免受刑罚之累,国家也可通过征收茶税弥补财政损失,“关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
王安石不仅反对榷茶,而且反对大商人的包卖制度。在《茶商十二说》[43]中,他列举了包卖制的12条弊端,大力推崇小商品经营,其思想主要可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其一,巨商人数少易于勾结在一起形成垄断经营,既可采用公开或隐蔽的手段迫使政府减税,又可压低收购价格使小生产者“园民”蒙受损害。其二,包卖制将大幅度提高经营成本。因为采取包卖制须严禁走私,这将增加大量缉私人员的开支;官府须在各州郡设置水陆运输设备及护运兵卒,难免仍有风波、盗窃等损失;包卖制必须大量储备茶叶,容易造成变质耗损。其三,小商品经营使经营者能直接关心商品质量,质佳则容易销售。这就是“货利己则精心,精心则货善,货善则易售”。相反巨商包卖则层层盗窃淆杂,“皆以非己而致货不善也”。由于质量低劣,只好借助官府强制配售,使消费者受害,并且容易引起茶叶走私,使犯法者大量增加。其四,商人必须有数千缗资本才敢承包,因此承包人数少而茶销量有限,容易形成积压;若是小商人经营,因其人数多而茶叶销量大,不会造成“难竭而成积滞”。总之,王安石认为采取大商人包卖制度危害甚大,故“不可不去也”。
(三)叶适反对抑末的思想
重本抑末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主流观点,在这一思想流传了一千年之后,南宋叶适公开否定“抑末”。他说:“《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帝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44]在此,叶适从三个方面对抑末论进行批判:其一,先秦儒家经典《尚书》《春秋》都肯定商业的作用,并以国家的力量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抑末厚本是后来才出现的。[45]这也就是说抑末厚本并非古代圣贤留传下来的正论,后人不必对此盲目崇拜,视为不刊之论。其二,作为末的工商业者,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列。只有“四民交致其用”,即士农工商各尽其用,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才能实现“治化兴”。抑末对“治化”是有害无益的。其三,为了厚本而故意抑末,虽然是一种片面的偏激观点和措施,但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后世的抑末,实际上是封建国家借抑末来夺取商人而由官府经商以自利,这根本不是抑末。
叶适基于当时抑末是夺商以自利的认识,不赞成桑弘羊所实行的由官府直接垄断经营工商业,控制全国经济的做法。他认为,桑弘羊“直聚敛而已耳”[46],“桑弘羊一志以民为壑”[47]。但他对国家干预生产、流通并非一概反对,关键在于干预的目的与方式。如果这种干预“为民通致食货,全与无取”[48],他是赞成的。他在评论汉宣帝时说:“是时已罢盐铁榷酤,利门不开,故择吏安民,政平讼理,即受其赐,虽不足以兴礼乐,行道化,至于富而教之,则庶几矣。”[49]其实,汉宣帝时榷酤已罢,但盐铁仍是官营。从此可见叶适反对官府直接垄断经营工商业“与民争利”的思想。
另一方面,叶适也不同意司马迁对工商采取放任主义的主张。他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50]他认为,人们为了求利而争夺是不好的,单靠因势利导、教育规范来治理那些违法乱纪者,是治理不来的。叶适主张必须通过制度来规范人们的求利行为:“古之圣人,以民不能自衣食而教以衣食之方。及其敝也,上下无制,而因其所以衣食者,斗其力,专其利,争夺而不愧,赡足而不止”[51]。只有改变“上下无制”的状况,才能解决“衣食之具”的“此有而彼亡”,“彼多而此寡”的问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