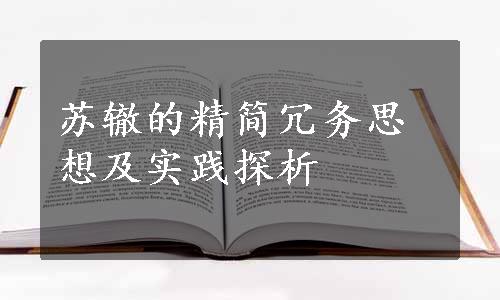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财政入不敷出严重,赤字达4204769,这一数字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自宋太祖建国以来至宋英宗时期最高的。可见,从宋真宗至英宗朝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神宗嗣位,尤先理财”[97]。苏辙即上《上皇帝书》[98],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面对当时国家财政的危机,苏辙的指导思想是重“节流”,即“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因此,他的着眼点是去除“害财者”,而不是寻求“丰财者”。苏辙把当时的害财者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这个概括比较全面合理地揭示了当时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三项巨大开支。苏辙不把以往宋祁的“僧尼道士”之冗、张方平的“释道”之蠹包含在三冗之内,其原因可能是释道主要是增加社会负担,而不是国家财政负担。
北宋自开国以来,官僚队伍膨胀迅速。在真宗景德年间,内外官有一万余人,仁宋皇祐年间,则增至二万多人。官员尸位素餐,空耗俸禄,国家为维持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需要巨额财政开支。为解决“冗吏”问题,苏辙提出三条措施:“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科举取士之多,是造成宋代冗官的一个重要原因。据学者统计,仅北宋贡举取士就达6万多人。[99]由于宋代取士之滥,加之科考及第者有种种优厚待遇,故天下之人“群起而趋之”。因此,苏辙提出延长贡举时间,并且不增加录取名额,废除推恩制度,以此来减缓官员队伍的增长速度。“其二,使官至于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于朝,袭簪绶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门荫入仕,是宋代封建统治阶级子弟亲属当官的一种特权,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凡中高级官吏及后妃公主等均可奏请亲属补官。据学者估计,宋代平均每年由门荫补官者不下500人。[100]这是造成冗官的另一原因。对此,苏辙意识到要废除这种特权制度是不可能的,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给其子孙一定的食禄而不再担任官职。“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在宋代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权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层次重叠,叠床架屋,使官僚机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苏辙就此提出中央机构精简事务,下放权力,裁汰冗员。他举三司为例,由于三司作为封建理财机构,其事务最为繁杂,主要是因为“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委,则吏不得不多”,即权力过分集中所致。因此“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其实,这种事无巨细中央统管的做法,不仅使中央机构日益膨胀,而且因忙于琐碎事务,反而失去对全局的控制。对此,苏辙主张应下放三司权力,使“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这样,转运使、州县各尽其职,逐层监督,互相制约,“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节省财政开支。最后,苏辙认为:“苟三司犹可损也,而百司可见矣。”由此可见,事繁权重的三司都能精简事务,裁汰冗员,更何况中央其他机构也应如此。这将使朝廷大大减少财政开支。对于中央机构的官吏,苏辙还主张推迟晋升,使官僚队伍增长速度尽可能缓慢。
如前所述,英宗治平年间,蔡襄就已提出了裁减军队人员的主张,但是,由于英宗在位仅4年,冗兵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军队将士在百万以上,巨额军费开支仍然是国家财政最主要的负担。苏辙对于冗兵问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对策:其一,“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仅30万),可以足用于今世”。苏辙十分重视在战争中间谍的作用,“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于此”。他认为,宋太祖时用兵之所以能“以少为多”,是因为重赏这些间谍,使他们“贪其金钱,捐驱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具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而现在用兵之所以“以多为少”,是因为轻待间谍,“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由此故也”。因此,苏辙主张利用关市征税之钱重赏间谍,以明敌情,减少边兵,“三十万之奉,比于百万则约”,从而节约巨额开支。其二,“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苏辙认为:“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不言而喻,增加土兵,裁减禁军,既提高战斗力,又节省九分之八的军费。
苏辙认为:“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其主要者,有宗室、漕运和赏赐之费。北宋自宋太祖建国至宋神宗时期,已“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于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于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由此可见,宋皇室经过一百年的繁衍,人数众多,其供养的费用已超过所有官吏的俸禄。有鉴于此,苏辙以儒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作为理论依据,建议“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总之,宗室子孙超过七世,就不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与一般平民相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宗室享有特权的人数,从而节省了财政开支。(www.zuozong.com)
宋代“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强,天下承受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于古”。北宋定都汴梁(今开封),京师民众、官僚和驻军所食粮食主要从东南地区漕运而来,“凡今东南之米,每岁溯汴而上,以石计者,至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于舟揖,州郡之卒敝于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率非完物矣”。总之,当时漕法劳命伤财,而且效果也不好,“非法之良者也”。因此,苏辙提出了改革措施:“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所欺盗败失者,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于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于贱。”这里,苏辙建议将每年漕粮总额一分为四,一半仍用旧法,1/4招募江南六道富人漕运,1/4由政府在京师置场收买,凡京师驻军不愿领米的,计值给钱,让他们上市场购买。苏辙希望“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
苏辙在“冗费”上与众不同、见解深刻的是把朝廷不急其所急、不用其所用,即不该开支的经费也称之为“冗费”,主张应裁减这些“无益之费”。他批评朝廷“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并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于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定,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俟岁月而葬”。他希望朝廷“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收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
总之,苏辙的解决“三冗”问题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上皇帝书》一文中,其中延长贡举时间、改革荫补机构、裁减禁军等措施都比较稳健缓和,力求在不引起动荡的情况下渐进式地使弊端自行消亡。如他改革州郡选士制度,要使“十年之后,无实之士将不黜而自减”。又如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是维护宋王朝统治的最重要武装力量,对其裁减必须慎之又慎。苏辙主张“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苏辙的另一些改革又显得新奇大胆,如通过重金招募间谍以明敌情,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布置兵力,从而达到裁减军队减少军费的目的;他把不急所急、不用所用的开支视作冗费,亦表现了他独特的眼光。他把皇帝宗室之费视作第一大冗费建议予以裁减,则又表现出了为了国家利益而无私无畏的气概。苏辙在解决三冗中有了比较明确的经济核算思想,他的益土兵损禁军就是从“材力”与“廪给”两方面加以估算,从而得出这一措施既能提高军队战斗力,又能大大节省军费开支的结论。又如他通过“权其轻重”,使皇帝清楚地认识到重金招募间谍所用的经费大大低于因明敌情所裁减掉军队而节省的军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