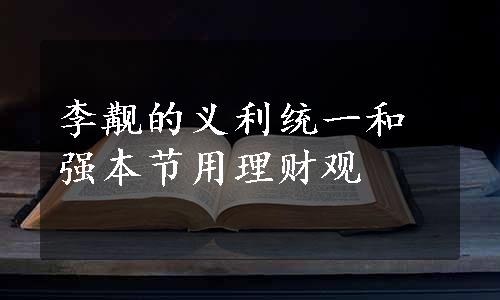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传统的义利观主要是提倡重义轻利或贵义贱利、先义后利。反传统的义利观则强调追求正当利的合理性,主张义利统一。北宋李觏肯定人的利欲的正当性,明确提出:“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20]他理直气壮地认为利欲是人天生的本性,为什么不可以说呢?他批判了孟子的“何必曰利”的思想,指出“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岂小哉?”[21]但李觏也并不是支持一切利和欲,主张以“礼”来制约,离开或违背“礼”的要求的利欲就是“贪”和“淫”。
他在《富国策第一》[22]中,不赞同儒家传统的贵义贱利论,“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明确提出国家应当讲求财利,实现富国,强调“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把财用看作一国政治、军事、外交、道德、文化的基础。他说:“盖城郭宫室,非财不完;羞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戍,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首先需要富国,“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而且,李觏的富国强调的是广义的富国,不只是狭义地为了增加财政收支,而是指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他特别指出:“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末,厚取于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可见,他主张实现广义的富国,而反对只从“厚取于民”来实现国家财用的充裕。(www.zuozong.com)
在广义富国思想的指导下,李觏主张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对当时财政上的聚敛提出评论:“夫财物不自天降,亦非神化。虽太公复出于齐,桑羊更生于汉,不损于下而能益上者,未之信也。况今言利之臣乎?农不添田,蚕不加桑,而聚敛之数,岁月增倍。辍衣止食,十室九空,本之既苦,则去而逐末矣。又从而笼其末,不为盗贼将何适也?”[23]他把赋税太重看作驱使人民逐末和铤而走险的一个原因。李觏从社会物质生产的有限性出发,强调国家财政要量入为出。他说:“天不常生,其生有时;地不遍产,其产有宜;人不皆作,其作有能”,因此,“国不尽得,其得有数”,如“不量入以为出,节用而爱人”,那就是“乱世之政”[24]。他主张财政收支要有一定的制度,防止任意向人民敛取和肆意支用,要求在财政收入方面作到“一谷之税,一钱之敛,给公上者,各有定制”,在财政支出方面也要做到“凡一赋之出,则给一事之费,费之多少,一照法式”[25]。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他还劝谏天子生活虽不能“下同匹夫”,但也要节用。当时正对西夏作战,恰是国用不足之际,天子“则宜深自菲薄”,“损上益下”[2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