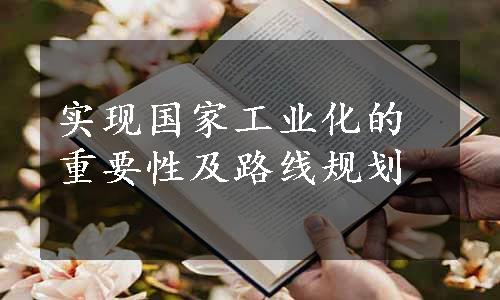
工业化与小康社会是什么关系?小康社会在它的最初阶段多表现为粮、棉、肉、油等农林牧副渔五业充足,但不管是“小康之家”还是“小康社会”,有饭吃仅仅是生存的最低需求,除此之外,还需要有衣穿,有房住,有钱花,有学上等,而这些都需要工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实现国家工业化明确地写在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动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这是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对此毛泽东同志称这是“统筹兼顾”的方针精神。第三十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辅助其发展。这是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这又是鼓励私营经济与国营经济合作的混合经济政策。
中国共产党原来的设想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但是,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时关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29]的讲话,则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他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就是过渡时期的开始,“从现在起就开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0]此后这个表述作了微调,主要是在完成的时间上。同年9月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引用了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提法,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31]为什么作这个微调?因为,毛泽东在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时提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的指标,指出:“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现在我国工业很落后,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达到70%。”[32]就是说,当时我国工业化率仅达到28%,要在现有的28%达到70%,困难的确很多,所以把“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改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更科学一些。但毛泽东提出“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的完成时限也是有根据的。首先是参考了苏联完成工业化所用的时间;然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共15年,如果再加上3年过渡期就是18年。
1.第一个五年计划
因为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来完成国家工业化,所以,中国的工业化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开始。1952年下半年,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很快就要进入全面建设时期的情况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提出了轮廓草案。包括《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和《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3个文件。草案提出“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工农业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长48.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05.71%,农业总产值增长44.75%;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6%左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地面积1957年将占总面积的30%~40%。这些指标的安排显然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
为了增强“一五”计划编制的准确性、科学性,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重点是争取苏联的援助。代表团由周恩来任团长,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包括各部门的专家共30多人。1952年8月15日,中国政府代表团从北京出发,17日到达莫斯科。9月下旬周恩来、陈云先后回国,由中财委副主任李富春留在莫斯科,主持继续与苏方商谈。斯大林与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两次会谈,在8月2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对代表团提出的“工业资源的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军事,肯定地回答愿尽力之所及予以帮助”。在看完代表团提交的轮廓草案文件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表示,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五年计划中,每年要超过1%,其数量总是比过去大的。次之,在五年计划中,你们未将民用工业与军事工业和装备计算在一起,这是不应该的。只有将他们放在一起,才便于掌握情况和调度……据我们自己经验,五年计划至少有一年准备,审查方案还要两三个月。即令如此,也还可能有错误……谈到最后,斯大林具体指出: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每年生产计划应定为20%,要动员工人来完成和超过这一计划。[33] 1953年2月1日晚,苏联国家计委主席萨布洛夫约见李富春。他说: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太大。并指出:搞建设一定要把地质资料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有把握的就暂缓。这样,中国的建设速度将会很快。李富春认真研究了苏方的意见,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以便抓住重点,建立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工业化的人才,积累建设经验,搞清资源,如此,则日后的速度可快。”[34]据此,又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原则性意见:一是要实事求是,没有资料、缺乏力量的决不勉强上,该推迟的项目一定后上;二是从发展战略要求及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联系上考虑,必须建设的重点项目,要充分说明理由,力争苏方帮助设计。李富春要求各小组根据这些原则对原方案进行修改补充后,同苏方进行第二轮商谈。2月9日,李富春再一次综合各小组商谈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14日,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给李富春复信,明确表示:一、我们认为苏联国家计委对我们计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苏联国家计委介绍的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对我国制定五年计划有巨大的帮助。二、长期计划中的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拟定为13%~15%,年度计划中根据实际可能情况适当提高,以保证长期计划的提前完成。这样办是有好处的。三、苏方对各工业计划所提出的具体意见,我们基本同意。
从1952年9月至1953年4月,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领导下,同苏方进行了反复研究磋商,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上已取得一致意见,1953年5月15日晚10时,中苏双方举行签字仪式。李富春、米高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文本上签字。其主要成果是苏联援助中国新建与改建91个项目,主要包括钢铁、冶金、机械、化工、发电、医药等方面的大型企业。另外,毛泽东在第一次访苏时,与斯大林敲定了作为第一批项目的50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时签订第三批15个项目协议。此后,中苏双方又陆续签订18个项目,经过反复调整,最后确定154项。因为156项工程公布在先,故仍通称为“156项工程”。“156项工程”的建设在经验、技术、人才、制度等几个方面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指导性经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这次商谈的另一重大成果,是为了使中国能够尽快掌握新建与改建企业的技术,苏联政府决定每年接受1000名中国实习生,派出五年综合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来中国指导工作。
1953年6月李富春回国后,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苏方的意见,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所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意见,很快向中央上报了《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提纲草案)》。1954年3月,中共中央又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领的八人工作小组。在李富春等领导下,国家计委组织人员经过认真仔细的测算和反复讨论修改,终于如期完成了计划草案初稿。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这个草案。7月5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同意李富春所作的报告,审议并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具体安排是:5年内全国经济建设的支出总数766.4亿元,其中属于基本建设的投资427.4亿元,占55.8%。5年内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4.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2%。在工农业发展的基础上,1957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498亿元,比1952年增长80%左右。5年内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将有较大发展。在人民生活方面,5年内,工人、职员的平均工资月增长33%,其中工业部门增长27.1%,农林水利部门增长33.5%,基本建设单位增长19%,国家机关增长65.7%,文教卫生系统增长38.2%,农村购买力1957年将比1952年提高1倍。
“一五”计划的核心是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最早建成投产的项目是重庆电厂和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前者用了2年时间,1952年开工,1954年建成;后者用了1年时间,1953年开工,1954年建成投产。实际建设的150个项目,绝大部分是1952年至1957年间开工,在1955年至1962年间陆续建成投产的。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年7月15日破坏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将一座宏伟壮丽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中国第一家现代汽车制造厂由此诞生。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我国第一个拖拉机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也是经过4年的建设,于1959年11月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拖拉机的历史。在化学工业建设方面,1954年我国最大的医药联合企业华北制药厂开始施工,1958年建成投产。该企业建成后,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国内对青霉素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青霉素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吉林染料厂、吉林氮肥厂、吉林电石厂,组成全国最大的化学工业基地——吉林化工区。该项目1955年4月开始施工。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了3万多名职工,组成了一只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为了把长达100米、重达100吨的硝酸排气筒安装就位,工人们打破常规,在地面上逐节焊接,单凭四个据点的卷扬机和推土机,就一次整体吊装成功并安全就位。仅用了3年半时间,就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染料厂和化肥厂,安装了亚洲最大的电石炉和一系列后加工设备。全部工程一次试车成功,并于1957年10月25日正式投入生产,当年就为国家提供了7900吨染料和中间体、4.3万吨化肥和2.83万吨电石,生产品种达到37个。“156项”中唯一的轻工业项目——佳木斯造纸厂,于1954年8月开工建设,1957年即建成投产,比预定计划提前8个月完成建设任务。佳木斯造纸厂投产后生产的产品,填补了我国造纸工业的空白,大大减少了我国工业技术用纸和造纸用无端铜网进口的数量,供应了2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家工商企业。从1960年开始,机制纸、造纸用铜网、造纸副产品粗木素塔尔油开始出口,为国家提供了新的外汇来源。总之,以“156项”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仅就“156项”中的民用工业106项工程来说,仅花了156.0865亿元人民币,就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基础。
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5年的努力奋斗,到1957年底,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到1957年底,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手工业者占全国手工业者总数的90%左右;私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不到1‰,私营个体商业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只占3%。在基本建设方面:5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其中国家对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15.3%。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原计划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产的有428个,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09个。这921个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电子器材的制造等。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面貌,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和技术改造奠定了基础。在工业方面:195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一五”计划15.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平均每年增长25.4%,轻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2.9%。同时,重工业也超额完成“一五”计划,1957年产值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8%。在五年计划规定的46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中,有27种提前一年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钢产量1957年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近两倍,为原定计划的137%。煤炭产量1957年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近一倍,为原定计划的110%。在农业方面:1957年农副业总产值达到“一五”计划规定指标的101%。其中粮食产量为计划的102%,棉花产量为计划的100.3%。农业生产条件方面:5年内扩大耕地5867万亩,为计划的101%,新增灌溉面积1.1亿亩,为计划的152.8%,在林业建设方面:5年来造林面积达21469.5万亩,为计划的228.1%。在交通运输邮电方面: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千米,比1952年增加22%。1957年底,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5万千米,比1952年增加1倍,穿越世界屋脊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通车。1957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内河航运里程增长51.6%,空运线路增长101.5%,现代化运输工具的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增长144%和142%,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增长159.1%和100.6%,邮路总长度增长72.3%,邮电业务量增长72%。在科技教育方面:高等学校由1953年的181所增加1957年的229所,增长26.5%;1957年在校学生44.1万人,比1952年增长1.3倍。中等专业学校1957年在校学生77.8万人,比1952年增长22.3%;普通中学1957年在校学生628.1万人,比1952年增长1.5倍;小学1957年在校学生6428万人,比1952年增长25.7%。1957年全国科研机构共有580多个,研究人员2.8万人,比1952年增长2倍多。在人民生活方面:1957年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34.2%,其中城镇居民为205元,比1952年提高38.5%;农民为79元,比1952年提高27.4%到1957年底,我国职工人数为2451万人,比1952年增长55.1%,城市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957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达到637元,比1952年增长42.8%。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的生活也有较大改善。农民1957年的收入比1952年增加20%左右。1957年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比1952年增长2倍多。[35]
2.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58年至1962年,简称“二五”计划,它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编制完成的。鉴于按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国家工业化的总体设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具有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承上启下的作用,党中央认为,编制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实事求是地估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的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党中央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36]同时,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在提交中共八大审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周恩来指出:“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扩大冶金工业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推进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37]
尽管中共八大审议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但周恩来对这个计划心中还是不安。中共八大闭幕不到2个月,周恩来就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把他担心的几个问题提了出来:
“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错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错误。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联系到我国是不是也可能产生这些问题呢?周恩来说: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第二点,就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周恩来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话,“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38]周恩来进一步分析了人口多的优势和可能带来的困难,他说,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建设中如何处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要正确地解决这十大关系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安排得更恰当。但是我们要认识,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
第三个问题,就是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发展速度问题。周恩来指出,“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很高的产量呢?当然,产量是要高一点,但是不一定很高,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39]
后来的事实都被周恩来言中了。由于急于求成,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后来又下很大功夫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和恢复,实际上不仅没有加快发展速度,反而影响了发展速度。尽管如此,我们在科学技术、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等方面,还是实现或部分地实现了“二五”计划目标。
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早有清醒认识。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会见科技界代表,说:你们都是科技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很重要,我们建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呢?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面前,“我们之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挥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40]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争取留学生回国的工作。据教育部1950年8月统计,1946年至1948年,中国在外的留学生共5541人,其中在美国的有3500人,在日本的有1200人,在英国的有443人。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1950年至1953年,以李四光、华罗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约2000名留学生回到祖国。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在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41]
在清醒看到世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革命性变化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报告提出了“我们走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任务及中国科技发展的道路:第一,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至两年的学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第六,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这次会议后,我国就启动了“二五”计划规定的发展后来被称为“两弹一星”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试验工作。
1955年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发展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从哲学的角度谈了原子可分的问题,鼓励核科学家们进一步地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42] 1958年6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还有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什么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的。[43]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就曾对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说:“你回去告诉毛泽东,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自己有原子弹。”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邓稼先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7年邓稼先从北京大学考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1950年10月回国后邓稼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跟随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等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从事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和放射化学等领域的研究。他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我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成为中国核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中央作出集中力量研制核武器的重大决策后,对核理论有很高学术造诣的邓稼先进入党中央的视线。1958年10月,33岁的邓稼先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普照的高粱地后,隐姓埋名,任新筹建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主任,负责核武器的理论设计。1959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决策,明确了研制原子弹的时间表: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中国还用苏联撕毁协议的时间“596”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以此鞭策大家为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而“争气”。
邓稼先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按照这三个方面把理论部的同志分别编到三个组中去。后来的事实证明,以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选得很正确,它是以后研制工作顺利进展的极为重要的保证,可以说是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邓稼先全面掌握着三个组,自己又亲自领导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组。1961年底,经过3年的攻关,邓稼先带领科硏人员基本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和理论计算,朝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迈出了一大步。1962年9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诞生了。基于这个方案,由罗瑞卿审定,二机部向中央打了一个“两年规划”的报告,此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这就是著名的“两年规划”。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二机部争取在两年后制成原子弹的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随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为主任,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干部组成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从此,全国的行动节奏加快,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项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63年2月,邓稼先跟随科研大部队转战青海金银滩,参与并指导核试验前的轰炸模拟试验。七个月吃住在试验基地,一天工作达十多个小时,饿了就啃一口馒头,实在累了,就和衣在基地临时搭建的四面透风的棚子里眯一会儿,他们硬是用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取得了模拟试验的成功,造出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宣告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计划完成。1964年10月,邓稼先在设计方案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原子弹爆炸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后,许多人兴奋又紧张地问邓稼先:“能行吗?”邓稼先回答:“该考虑的都考虑到了。”
1964年10月16日,代号“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中国西北大漠的铁塔上待命。在西北大漠的试验过程中,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在前方的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下午3时整,翻滚着的巨大蘑菇云在罗布泊的上空腾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当张爱萍激动地用有些颤抖的声音向周总理报告:“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问:“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当得到肯定回答后,周恩来如释重负,随即拿起话筒,向毛泽东报告。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恩来高兴地宣布了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个消息让与会人员万分激动,欢呼跳跃,响起了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这一颗原子弹不仅震撼大漠长空,更震惊了全世界。
在此之前,1960年1月22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为此,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成立“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全面主持研制氢弹的工作。
研制氢弹,选好学术带头人极其重要。钱三强经过再三斟酌,先后任命黄祖洽和于敏担任轻核理论组的正副组长。当年参加了氢弹理论研究并有重要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同志说:“调于敏来参加工作,这是三强在领导氢弹理论研究方面所做的重大决策。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十分正确。如果那时不是及早请于敏来参加这一工作,氢弹理论的完成,恐怕至少要推迟两年时间。对科学人员,知人善任’,这是三强担任科学研究工作所特有的才能。”以后的历史轨迹是:于敏在氢弹理论研究中解决了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是氢弹理论设计的主要完成人,并且在氢弹的武器化和新一代核武器研制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杨振宁一再称赞“于敏是中国非常杰出的科学家”。
氢弹理论研究工作,无论是对氢弹中各种物理过程,还是进一步对氢弹作用原理和氢弹结构的探索和研究,都离不开核数据作必要的基础。考虑到这种情况,钱三强决定在成立轻核反应理论组的同时成立轻核反应实验组,用轻核反应数据的精确测量来配合、支持轻核理论组的工作。这一决定无疑是有远见卓识的。轻核反应实验组的组长,最初由蔡敦九担任,后改由丁大钊担任。
在轻核理论组、实验组的研究方向、工作步骤等重大问题上,钱三强总是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先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讲自己的意见。丁大钊写的《关于轻核反应组的回忆》:“在2—9组(轻核反应组的保密代号)成立后的近一年时间内,钱三强先生多次来组讨论及指导工作,对该工作的开展起了定向作用。钱先生谈到:这个体系中有一大群中子、带电粒子及光子的核作用,不仅产生能量,并使反应过程能自持。希望你们首先能弄清这个反应过程、有关核素及重要的参数。希望你们从学习与调研入手,在半年到一年内能理出头绪。要加强与理论组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指导。这是个复杂的体系,不是少数人能测好所有的数据的。希望你们在调研基础上提出实验课题,然后你们抓住一些问题开展。听说人家不完全用同位素614C,而714N在反应中也起作用。这需要弄清。他多次鼓励我们:人家能搞出来,我们也一定能搞得出来。按照钱先生的要求,我们第一步,第二步……”
在钱三强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下,于敏、黄祖洽、何祚庥等40余名理论物理和应用数学方面的研究人员,在轻核这个肉眼看不见但又浩瀚神秘的王国里奔突闯荡了4个春秋,对氢弹中的各种物理过程、作用原理和可能结构进行了研究,认识了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为1965年1月掌握氢弹设计原理奠定了基础。
在钱三强的领导下,氢弹理论预研组全体科研人员团结协作,艰苦奋斗,在4年左右时间里,对氢弹各种物理过程、作用原理和可能的结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认识了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研究和计算了中子和辐射输运参数,形成了初步的氢弹设计方案,为氢弹突破奠定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基础。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集中力量快速突破氢弹技术,黄祖洽和于敏等31位科研人员调到九院理论部。经过机构调整和人力集中后,氢弹研制工作进展飞快。在于敏的亲自组织和部署下,1965年10月我国氢弹理论得以突破。1966年12月28日,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两个月,我国氢弹原理爆炸试验成功。
此后,我国又于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任务,经过第三个、第四个五年计划终于完成,是新中国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创举;“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支较高水平的科技队伍,促进了国家科技进步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使我国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增强了国防实力,提高了国际地位,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的和平生活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书写了中华民族振兴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对中华民族在当代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3.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6—1970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简称“三五”计划。本来第三个五年计划应该从1963年开始的,由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开始国民经济全面调整,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调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样,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到1966年开局。
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建议“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加强基础工业,增加产品品种和产量,继续提高产品质量;相应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当时人们形象地把这个计划称为“吃穿用计划”。
这时候,中央开始考虑三线建设问题。其背景是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试爆成功,为了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的计划已进入最高决策层,并征求了苏联的意见。1964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绝密报告,当月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就此进行了讨论。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写出一份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一)工业过于集中。仅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包括:飞机制造工业的72.7%,舰艇制造工业的77.8%,无线电工业的59%,兵器制造工业的44%)。(二)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20个50万至1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袭、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同时,这些交通要点,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我国现有容量达1亿到350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232个,其中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有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此外,尚有不少中、小型水库位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和交通干线的要害位置。”[44]这份包含标点符号在内总共600字左右的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那次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是在列车上进行的。当李富春汇报到基础工业、交通同各方面还不适应时,毛泽东插话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当汇报到国防建设时)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45]
5月27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三五”计划。毛泽东在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三线建设问题。他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汇报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北京出了问题,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46] 5月28日,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筹划“三五”计划的讨论扩大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的范围进行。因为毛泽东已经提出了战略思想,这次会议主要围绕如何进行三线建设的布局进行讨论。周恩来发言指出:我们现在要建立三线观点,同时又必须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一、二线这样集中,很不利。现在要把攀枝花作为一个中心,其他很多相应的东西都要搞起来。不单是一个攀枝花的问题,要通过攀枝花把云贵川联系起来。不单是一条铁路,一个煤矿,一个铁矿;有色金属、电力、水利、机械工业和轻工业,都要作相应的安排。机械工业,还是要用一分为二的办法来搞。现在我们很多好的机械工业还是在沿海,比如上海的,大连的,济南的,武汉的,这些机械厂,可以把它们的技术再提高,把设备更新,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就可以分到第二线和第三线……我觉得,做计划工作的同志,不要因为现在有三线的工作要做,一、二线的事情就可以放松些。实际上并不如此,一、二线的工作还是很重的。比如上海,我看任务更大。如果把一个上海变成三个、四个、五个,最后变成十七八个,用二分法把它分出去,上海的城市既不至于扩大,又能够帮助别的地方发展起来,这要做大量的工作。[47]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形成的共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终于确立。这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第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
由于迅速启动三线建设,因此对原来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作出重大调整。首先确定的是《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其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这个计划草案于1964年10月30日经中央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接着于1965年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提纲(草稿)》。《汇报提纲》提出总的方针和任务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善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的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汇报提纲》特别指出:这是关系着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全局、关系国家安危、关系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战略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的错误。在基本建设方面,提出要综合考虑战争、灾荒、人民这三个因素,基本建设规模不能搞得过大,必须留有余地;规模小一些,少搞些项目,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具体安排是:建设攀枝花、酒泉两大钢铁基地,投资18.1亿元;在西南、西北,建成为国防工业服务的迁建和续建的重庆、昆明两个钢铁厂,四川江油、重庆、贵阳、西宁4个特殊钢厂,宁夏石嘴山、四川江油两个金属制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遵义薄板厂和6个配套项目,投资共15亿元;续建武钢、包钢、太钢,5年投资18.5亿元;建设一、二线的河北水厂,江苏梅山、海南岛、马鞍山凹山等铁矿和辅助原料矿、铁合金厂,湘潭的钢丝绳厂等。在农业、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提出到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700亿至2750亿元,5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左右,其中,农业总产值为700亿至750亿元,平均年递增5%~6%;工业总产值为2000亿元,平均年递增8%。在文化、教育、卫生方面,提出要普及小学教育,继续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重点要巩固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到1970年达到每个大队有一个文化室(或俱乐部),70%左右的大队能够收听到有线或无线广播;卫生事业的重点要转向农村,到1970年争取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不脱产卫生员,每个大队有一名半农半医的医生和一名接生员。在人民生活方面,提出: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到1970年达到737元,比1965年增长12%;农民的收入也要有较大的提高,使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比1965年增长15%左右。
为加快三线建设步伐,早在1964年开始编制“三五”计划时,中央同时启动了重大项目从一线向二线、三线搬迁计划。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听取薄一波关于计划工作的汇报时,就中央的战略方针下工业的重新布局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现在沿海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嘛!二线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山西、陕西、江西、吉林、内蒙,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嘛!……沿海各省都要搬家,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而且整个的学校、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家。迟搬不如早搬。”[48] 9月18日,薄一波就1964年、1965年工业企业的搬迁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现在必须立即动手,对工业布局重新加以部署。一方面,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一线搬一些工厂到三线去,有的全部搬,有的一分为二,搬一部分去。已经安排在一线的新建项目,一般应当停止建设,有的可以缩小规模。进口的新技术项目要坚决搬到三线去。另一方面,还要注意使一线的生产不受大的影响(不受一点影响也是不可能的),并且要充分发挥一线企业的潜力。”[49]薄一波的搬迁计划包括:一、首先必须坚决迁建与国防有关的重要企业(车间、设备),包括生产或试制常规武器和国防尖端产品所需的原料、材料、配套产品的企业以及生产民用关键产品的企业。二、必须分期分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即先品种,后数量(先解决有无,后解决多少);先协作,后配套(近期先依靠一、二线协作,将来逐步在三线配套);先搬设备,争取快出产品,先不带家属(一心一意建设,平时当作战时)。三、迁建的工厂,要结合进行生产组织上的改革,多搞小的专业化的厂,不搞全能厂。
中央确定第一批从一线搬往三线214个项目,到1965年上半年已搬迁51个,预计到1965年底可搬完127个,迁出的职工约4.8万人,设备约6700台。西南三线建设进展很快,据国家计委西南调查组调查发现,自1965年以来,西南铁路建设首先攻破了隧道掘进的难关,做到了施工效率成倍的提高。“矿山的施工效率普遍提高1倍以上。矿山平巷掘进,过去较快的每月成峒也只有50~70米,现在铁矿、煤矿、铜矿的先进单位,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过200米以上。竖井掘进,历来是矿山建设上的一个难关,过去比较先进的每月只能完成二三十米,现在已经突破了70米以上。矿山的建设工期,普遍比过去缩短一半左右。铁矿,建设一个年产500万吨的大型矿山,由过去的5年左右缩短为3年;建设一个年产100万吨的中型矿山,由过去的4年左右缩短为2年左右。铜矿,建设一个年产精矿含铜量1万吨的矿山,由过去的5年缩短为2.5年。煤矿,建设一个年产45万吨的矿井,由过去的2年半缩短为1年;建设一个年产60万吨的矿井,由过去的3年缩短为20个月;建设一个年产99万吨的矿井,由过去的4年缩短为30个月。由于效率提高,工期缩短,西南地区的几个重点铁矿山,都可以在1968年以前建成。攀枝花的兰家火山和尖包包2个铁矿,年产650万吨的规模,原计划1968年底建成;现在看来,整个工程到1968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泸沽铁矿,原计划1967年底建成第一期年产40万吨的规模,现在看来,1967年上半年可以建成40万吨;1968年可以建成100万吨的规模。水城观音山铁矿,原计划1968年底建成第一期60万吨的规模,现在看,1967年底可以建成60万吨;1968年可以建成115万吨。昆钢的八街、王家滩铁矿,1967年就可以建成67万吨,上厂铁矿1968年建成50万吨,共建成117万吨。綦江铁矿,1966年底可以全部建成100万吨。这样,1968年的铁矿生产能力就可以由现在的85万吨增加到1082万吨,大体上适应年产300万吨铁的需要。1970年攀枝花的朱家包包建成后,铁矿石的生产能力可以达到1782万吨,大体上适应年产450万吨铁的需要。”[50]
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三五”计划中的三线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中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状况;初步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结合的战略大后方现代工业交通体系。在国防科技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基地。
这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虽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没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但却为后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物质基础,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在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之后,接续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29年间,我国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和平友好成果,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从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来看,按当年价格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79亿元人民币,1976年增加到296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167亿增长到1976年的9.3717亿。同期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说,增产的粮食不仅多养活了近4亿人,而且使9亿多人的人均占有粮食量比5亿多人时增加了近200斤。全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农村居民从1952年的65元增加到1976年的131元,城镇居民同期从154元增加到365元。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从教育事业发展看,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在校生从2439万人发展到1.5亿人,中学在校生从103.9万人发展到5836.5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从11.7万人发展到56.5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从医疗事业发展看,1949年全国拥有医院2600家,到1976年发展到7850家。这个时期,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从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看,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从体育运动看,中国运动员共获得22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1项世界纪录。
《联合国世界经济年鉴》指出,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GDP总量排名第8位,在1949年时中国仅排名第104位。到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0位,人均190美元,与新中国成立时人均27美元相比,增长了许多倍。这时全国人口9.63亿,尚有2.5亿农民处于未解决温饱的贫困状态,一方面,说明我们在小康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减贫几亿人;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在小康的道路上还任重道远,必须使2.5亿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民尽快脱贫致富。
【注释】
[1]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页。
[2]同上书,第727页。
[3]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4页。(www.zuozong.com)
[4]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41页。
[5]《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452页。
[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9-570页。
[7]《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9页。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9]刘少奇:《国家的工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50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页。
[10]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62页。
[11]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12]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78页。
[13]同上书,第879页。
[1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1962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0页。
[15]《关于包工包产的指示》,《中共安徽省委文件选编(1955—1957)》,1994年内部发行,第412-413页。
[16]《论60年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重大历史问题评价》第三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7页。
[17]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79页。
[18]《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9-1230页。
[19]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选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页。
[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1页。
[21]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选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9页。
[22]《论60年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重大历史问题评价》(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0页。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4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8页。
[25]《论60年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重大历史问题评价》(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1页。
[26]同上。
[27]《论60年代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重大历史问题评价》(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3页。
[28]《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开国创业(1949—1956)》(卷一),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6月15日。
[31]周恩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9月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01-302页。
[32]《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9-750页。
[33]《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426页。
[34]《李富春致周恩来、陈云电》(1953年2月3日),《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开国创业(1949—1956)》(卷一),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405页。
[36]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225页。
[37]周恩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页。
[38]周恩来:《经济建设中的几个方针性问题》(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39]周恩来:《经济建设中的几个方针性问题》(1956年11月10日),《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页。
[40]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41]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182页。
[4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338页。
[4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44]《60年代三线建设决策文献选编》,《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
[45]毛泽东:《毛泽东:不搞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打起仗来怎么办》(1964年5月10、11日),《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46]毛泽东:《要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建设搞起来》(1964年5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47]《周恩来:要建立三线观点,又必须懂得一二线怎么布局》(1964年5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48]《毛泽东:一线要搬家,二线三线要加强》(1964年8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49]《薄一波关于今明两年工交企业搬家问题的报告》(1964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
[50]《国家计委西南调查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1966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220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