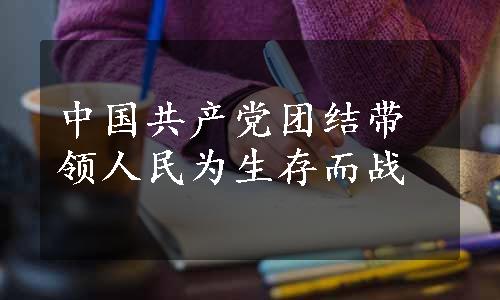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军阀和腐败无能的北洋政府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尽的灾难,人们最初把希望寄托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尽管它在辛亥革命后走了弯路,把胜利果实拱手让予窃国大盗袁世凯,导致此后十多年军阀混战,使中国人民已经十分苦难的生活雪上加霜。但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掀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终使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漫漫的长夜中似乎看到了一丝光亮。但是,军阀尚未铲除,蒋介石又成为新军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7年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下达反革命政变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20]当日下午,大批军队布防上海街市。晚上,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赴宴,汪被骗至杜宅后惨遭杀害。12日凌晨,隐藏在租界内的青红帮打手,打着工人的旗号,携带枪械,倾巢出动,在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等地袭击中共的工人纠察队。刚刚倒戈参加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开来,声言调解“工人内讧”,并先行收缴了青红帮武装分子的枪械。一部分工人纠察员信以为真,停止抵抗,却被强行缴械,另一部分工人纠察队员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死于国民党军队之手。截至4月15日,上海已有300名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此间,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国民党军警相继展开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搜捕和屠杀。包括著名共产党人李启汉、萧楚女、熊雄等在内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遭到杀害。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当晚,他召集国民党要人在寓所秘密开会,布置分共和大屠杀的计划。15日下午,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第二十次扩大会议,对“分共”作出一系列决定。这次会议之后,在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的反革命行动。汪精卫甚至咬牙切齿地说,对共产党“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现在还要说是容共的,就算不得是人”[21]。从此,武汉革命中心成为汪精卫反革命集团惨杀革命群众的屠场。
到1927年11月,共产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骤减到1万多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也由280多万人减到几万人。中国共产党能否度过自成立以来的这一重大危机,严重的摆到全党面前。它不仅要为劳苦大众和革命群众的生存而战,也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1927年7月12日夜,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训令,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政治局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刚刚诞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夜举行会议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从此日到7月26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续举行会议,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重大决策:一、依靠我党掌握的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发动军事暴动。二、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三、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这三项决策的作出,标志着中共中央应对蒋、汪反革命政变开始摒弃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并迈出了正确的步伐。
(1)举行南昌起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后,即把组织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列入重要议程。为此,着手做出两个计划:一是制定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二是决定以中央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军事暴动计划提前实现了。
最初,中央并没有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而是根据鲍罗廷的提议,想利用张发奎同唐生智的矛盾,联合张发奎,把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部队从南昌、九江地区带回广东,以图再举。为实现这一意图,7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李立三和邓中夏前往九江活动。
但李立三、邓中夏到达九江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唐生智、朱培德调动第三、第六、第九军对南昌地区取包围态势,张发奎也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的表示。7月20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与叶挺、聂荣臻在九江召开第一次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一致认为张发奎的联共态度已发生变化,正在日益右倾,叶挺、贺龙在南昌、九江间的部队已处于反动军队的包围之下,依靠张发奎回粤已很少有成功的可能,甚至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改变原来依靠张发奎的策略,转而实行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独立的军事行动,不失为明智之举。根据这一判断,这次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最初主张。
21日,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面见鲍罗廷和瞿秋白,进一步商议举行南昌起义问题,鲍罗廷、瞿秋白均赞成这一建议,并决定由瞿秋白向中共中央报告。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同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由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组织领导这次起义。
7月27日,肩负组织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及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陈赓等来到南昌。周恩来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一、将起义日期由7月28日推迟到30日;二、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三、成立由国民党左派参加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以商讨起义中出现的有关事宜。这时,叶挺、贺龙的部队已到达南昌。
8月1日凌晨2时,一声枪响划破了长夜的静寂,由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贺龙指挥第二十一军第一、第二团向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驻守那里的是号称滇军“精锐”的警卫团。起义军战士经过激战,消灭了该部敌军,占领了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和省政府。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堵住敌第六军第五十七团的退路。敌人关上大门,依靠坚固的掩蔽物进行抵抗,起义军将敌包围在教堂内,一面用火力猛攻,一面喊话劝降。敌人支持不住,终于吹起“敬礼号”,缴械投降。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负责歼灭敌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由于敌人的两个团长被朱德用计扣押,失去指挥官的第二十四团几乎没作抵抗就被歼灭;敌第二十三团遭到起义军攻击后,夺路突围,亦被我军歼灭。经过4个小时激烈战斗,共歼敌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南昌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它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独立的人民武装。
(2)举行秋收起义。中共中央筹划和组织实施南昌起义,是与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一起考虑的,并希望夺取广东和湖南两省政权。在八七会议上,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提了出来。为加强对起义工作的领导,中央委派毛泽东指导湖南省的工作,重点研究湖南政治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秋收起义。后来,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带着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使命回到湖南。此时,由于唐生智部队南下,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实现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的目标已经没有可能。同时,原定参加南昌起义的武昌警卫团和平、浏工农义勇队没有赶上起义,退驻在赣西北修水、铜鼓地区;罗荣桓从鄂南带来的一部分农军在修水,王兴亚从赣西带来的一部分农军在安源。因此,毛泽东力主缩小起义范围,只在湘中四周各县举行暴动,而放弃其他几个原定的中心地区的起义。这样,湖南省委将秋收起义计划修改为:以毛泽东为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到湘赣边将武昌警卫团、平浏工农义勇队和罗荣桓、王兴亚带来的部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会攻长沙;由易礼容为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发动长沙周围7县镇农民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8月下旬,上述部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实现了合编: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编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第一、第三团;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醴陵等地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以这3个团部队约5000人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原警卫团团长卢德铭任总指挥,副团长余洒渡为师长。
9月初,毛泽东来到安源,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兵分三路,从赣西修水、铜鼓和安源三地分别起义,进击湘东,会攻长沙。中路第三团为主力军,准备会合驻修水的第一团合击浏阳;以第二团进攻萍乡、醴陵,对长沙取包围之势。行动时间确定为: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www.zuozong.com)
但暴动计划执行却不顺利。当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起义前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使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进攻浏阳东门市也出师不利;毛泽东随军行动的第二团最初发展顺利,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在国民党正规军优势兵力反攻中,几乎全部溃散。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况,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并放弃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此后,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来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后来又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3)建立工农武装割据。1927年2月20日至23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曾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这就是日后他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源头。
1928年5月,毛泽东已经产生了武装割据的想法。在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布的《军事工作大纲》明确提出:“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22] 10月5日,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他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23]
什么是“工农武装割据”呢?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就是“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24]。即是说,仅仅打下一块地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块根据地里,必须建立人民政权,实现农民拥有土地等最大权益。而建立能够“长期地存在”的红色政权,没有革命武装作坚强后盾更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25]
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重大意义,1929年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赣边界巡视的杨克敏向省委提交《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说:“鉴于过去军队没有一个根据地,流寇似的东闯西窜,得不到一个休养的机会,军队十分感觉疲劳,而甚难解决的,就是伤兵的安置问题,要找一个军事根据地,必须用力量去建立一割据区域。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26]杨克敏的报告披露了当年毛泽东设计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考虑之一,为“工农红军的安全计”;其实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为“工农群众的生存计”,建立红军割据之后,在割据内的工农群众安全是有保障的。由此,毛泽东看到了从工农武装割据到统一全国的中国革命希望。后来,他借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建立武装割据的光明前景。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27] 1928年10月5日,在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中,毛泽东从理论上分析和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农村割据之所以能够长期地存在,第一……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28]
1929年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九月来信”明确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的重要论断。1930年5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理论、政策和实际工作问题。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策略问题上,周恩来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决不是放弃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方针,而是更适应实际的策略,可求得更大的发展。在中国什么地方更适合作苏维埃根据地呢?是赣西南、闽粤边界等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群众。在巩固这些根据地之后,再向工业城市中心发展。斯大林接受了中国同志的观点,在听取汇报后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情形与西欧不同,如西欧德国在柏林暴动即可得到全国胜利,但在中国是一相反的形势,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他要求中共中央特别注意红军问题,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29]
来自各方面对武装割据认识的深化,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不断前进的信心。沿着“武装割据”这条思路,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形成了新的认识。这期间,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初步地描绘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就是:通过党去领导军队,又用军队去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农民建立政权,再把农民武装起来,用一部分武装了的农民去保护和解放另一部分农民。革命就这样滚雪球般地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形成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一句话,形成一种国家模式。这种模式从南方的根据地带到北方的解放区,最后,水到渠成般地发展成全国政权。1930年1月,毛泽东致信林彪(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这样一条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进行了理论阐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创立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正式确立。
(4)进行长征。1933年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改变战法,采取的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的战术。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力量对比为1∶6,尽管形势严峻,但比第三次反“围剿”时的1∶10、第四次反“围剿”时的1∶10几要好许多。如果形势估计和采取战法正确的话,打破“围剿”仍然是有希望的。
但以博古为总负责的临时中央采取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6月13日,临时中央提出将中央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这种面对6倍于我的敌人,不收缩力量而“两面开花”的战法,显然不是高明之举。结果开局即在黎川陷入被动。
黎川失守后,博古、李德则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这种与敌人硬拼的消耗战,正中敌人下怀。从1934年1月至3月,在不断的阵地防御战、阵地反击战中,红军不仅没能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还遭受重大伤亡。伤亡最为惨重的是1934年4月10日至28日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自身却付出伤亡5000多人的惨重代价。
到1934年9月,瑞金中央根据地已由1931年底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时发展到包括瑞金、会昌、安远、寻乌、信丰、于都、广昌、石城、黎川、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减少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8个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这就是被称为“战略转移”的长征。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途中,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条件。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都为长征胜利不可磨灭的贡献。”[30]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恪守为人民打江山的人民情怀,为了给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长征时指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正是因为依靠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支持,也正是因为造福了人民。”[31]这段话是从“半条被子的故事”中引伸出来的。1934年11月6日,参加长征的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司(即现文明瑶族乡),红军卫生部干部团驻到沙洲村。据当事人徐解秀老人回忆,当年红军来到沙洲村,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许多人都上山躲起来了。她由于生孩子坐月子,又是小脚,就留下来带着婴儿在家。有3位女红军来到她家,跟她拉家常,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叫老乡们不要害怕。晚上,3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家中。她们看到徐解秀的床上只有一块烂棉絮和一件破簔衣,就打开她们的被包,拿出被子,和徐解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睡。三天后,她们临走时,便要将被子留给徐解秀。徐解秀不忍心,也不敢要,推来推去,争执不下。这时,一位女红军找来一把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3位女红军对徐解秀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生活。这时,红军大部队已经开始出发,徐解秀就和丈夫朱兰芳一起送三位女红军追赶大部队。快到山边时,天快黑了,徐解秀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不快,就让丈夫送她们翻山。谁知她们这一走,就没了音讯。因此,每年这几天,徐解秀总要在当年她们分别的地方等好久。因为她坚信红军会回来的。1984年11月7日,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采访了徐解秀老人。徐解秀说:“虽然那辰光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32]
为中国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底线。生存权,是人生的基本权利,只有生存有保障,才能再谈如何生活得好。保证中国人民的生存权,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肩负的历史使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政治前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