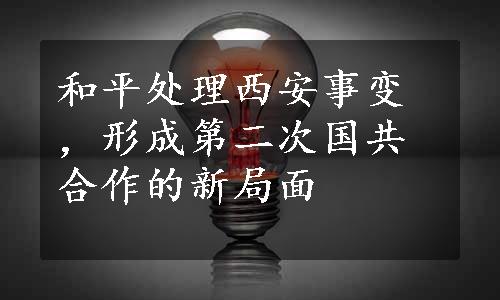
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国民党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为敌的道路。此后近十年,坐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第一把椅”的蒋介石,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断对以“朱、毛红军”为主力的中共军队围追堵截,曾多次使红军面临灭顶之灾。
这期间,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22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以巡视铁路为名,在奉天(今沈阳市)北面约7.5千米处,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00米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守各队,此事件由称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的开端。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退居为第二位。标志中国共产党反蒋政策开始重大转变的,是1935年8月1日草拟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一著名宣言,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参加筹备共产国际七大工作期间,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多次讨论的意见,执笔起草的。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审阅同意,10月1日,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共代表团主办的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发表了“八一宣言”。宣言的主要内容:第一,强调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明确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公开号召全国“工农军政商学各界男女同胞”,“为民族生存而战”!“为祖国独立而战”!第二,要求国民党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它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第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在国防政府领导下,一切抗日军队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31]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少帅、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张学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在第一时间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通报情况,希望中共派人协助处理事变,并将“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为了和平处理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处理事变。12月23日,由张学良、杨虎城为一方,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为一方,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为第三方,开始正式谈判。
经过几天来的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周恩来在《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把经各方认定的和平放蒋协议概括为10项成果:“(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32]
这10项成果被概括为“六项承诺”:(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33]
为了确保上述协议的落实,24日晚10点,周恩来在张学良、宋子文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对于刚刚达成的六项协议,蒋介石表示完全接受。除此之外,蒋介石又作了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34]
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从而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为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创造了重要历史条件。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全面抗战这一重要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誉为“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如何落实协定,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上作了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意见,还提出了4条对中共的要求,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4条与中共承诺的4项保证基本吻合。
当时国民党确实停止“剿共”,准备抗日了。会议期间,国民党当局还悄悄通知报界,不再用“赤匪”的字样。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宣言没有再提“剿共”问题,“抗战”一词首度见之于国民党宣言。实际上表明它接受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的基本精神,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转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于演习时失踪(实际上那名士兵是去上厕所了并在随后不久归队),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向卢沟桥一带开火,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37师219团予以还击。这便掀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开始的标志,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域战事的起始。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昔日的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蒋介石表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寸尺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介石宣布:“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与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35]
为了使中共领导的红军部队尽快开赴前线,投入抗日战斗,国民党加快了谈判速度。至8月3日,蒋介石已同意中共提出的有关条件。6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公开讲:中央已承认中共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并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现在举国团结对外的形势已经形成,亟应奋起抗战,一致御侮。8月19日,蒋介石正式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红军改编的主张。9月22日,国共两党对外公开宣布了所达成的合作协议。当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表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起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36]
经过半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在客观形势发展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宣布命令,红军主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设立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全军共4.6万人。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全军共1万余人。(www.zuozong.com)
1937年8月7日,南京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并确立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方针。8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要求:“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任务。”[37]抗战之初的前10个月,蒋介石按照自己理解的持久战思想进行战争指导,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会战等多次重大会战。只有台儿庄会战取胜。
毛泽东也主张打持久战,但他所主张的持久战与蒋介石实行的持久消耗战是不同的。1936年7月16日,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在回答“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在回答“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时,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38]
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科学预见到战争的形态、中国应该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战争的最终结局。抗日战争的进程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主张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提出了我军必须坚持的战略战术原则。他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他认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原则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
毛泽东还向会议提交了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在这份提纲中,提出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四、改革政治机构。选举国防政府,驱逐亲日分子,实行地方自治。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路线,反对德日意侵略路线。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善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日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
从1938年1月起,毛泽东开始用很大精力研究军事理论问题,主要是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到这年5月,《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光辉军事著作得以问世,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了关于抗日战争的基本问题。对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问题,毛泽东对中日双方国力、军力、战争性质、国际国内的态度等进行了综合分析。深刻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个特点决定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可避免性,也是决定中国抗战不能速胜的基本依据;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中国所进行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这就决定日本侵略战争必然失败,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一定取得最后的胜利;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就意味着日本经不住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则能够进行持久抗战。因此,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我们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
对于怎样进行持久战,毛泽东科学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如何与敌交锋提出了具体战略方针。按照毛泽东的见解,第一阶段为战略防御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在这一阶段,敌人欲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势必将投入大量兵力,气势汹汹扑来。面对强敌,“我所采取的战争方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39]第二个阶段为战略相持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在第一阶段,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兵力日显不足,无法迅速灭亡中国,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毛泽东说:“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40]第三个阶段为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41]走完战略反攻的全程,才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针对一些人对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及消耗战的认识误区,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在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要完成抗日战争的历史使命,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消耗战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42]
在战略防御的一年多时间中,中国共产党经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革命武装却取得了多次胜利。平型关大捷,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以及对曲阳、唐县的克复等,都记录着毛泽东高超的战争指导艺术。
为了打破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争取华北乃至全国战局的好转,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在华北敌后发动了规模浩大、震动国内外的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战役打响。在历时3个半月中,参战部队和民兵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伪军5000多人,俘虏日军280多人、伪军1.8万多人,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这次战役先后进行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八路军在正太、同蒲、平汉、津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使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第二阶段,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榆辽战役和破袭同蒲路,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第三阶段,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了侵华日军强有力的打击,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对坚持抗战、遏制当时国民党内的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所谓“游而不击”的诬蔑,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声威。
在整个相持阶段,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敌后战场上仍然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而正面战场牵制的侵华日军在40%以内。
经过5年多艰苦卓绝的战略相持,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这时,国际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战略反攻已进行数月。在中国战场,国民党军队继续奉行保存实力的政策,这使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反攻任务又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从1944年初开始,毛泽东指挥敌后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中,毛泽东分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五年来的抗战形势,认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战略阶段到来。他明确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43]敌后战场经过一年的局部战略反攻,奠定了对日全面反攻的胜利基础。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漫漫长夜,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