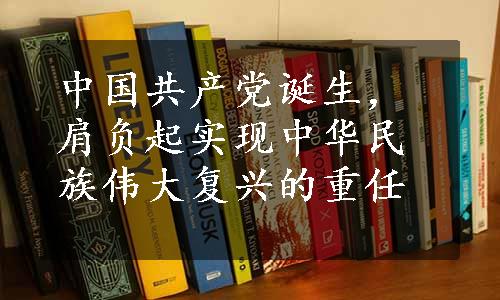
苏联的共产党,是先有小组,然后再发起建党。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36]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是学习俄国的经验,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即党的早期组织开始。
作为建党的第一步,1920年5月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会”。负责人是陈独秀。小组的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冰、邵力子、杨明斋等。稍后加入的是施存统。据邵力子回忆:“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远、戴季陶、邵力子等。……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成员起了一些变化。”[37]
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这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所要坚持的革命理想和被维经斯基纳入联合对象的一些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不愿放弃自己原来的理想的矛盾便不可调和地反映出来。围绕是坚持建党的标准还是降低共产党员的条件,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最后达成了一致。经过充分讨论形成的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8月,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在党的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
8月底,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由沪返京。离沪前,陈独秀与其谈话,指示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38]很快,北方地区的建党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也取得进展。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后又发展一批新成员。年底,在“共产党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分别是: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之后,马上来到广州,推动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到1921年三四月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广东共产党组织就此成立,取名“广东共产党”,先由陈独秀任书记,后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确定以《广东群报》为党的机关报,并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了刘尔崧、阮啸山、杨匏安等人入团、入党。
与此同时,陈独秀以极大的精力指导各地建立党组织。他函约五四时期济南地区著名进步人士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39]。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夏,李汉俊从上海写信给董必武和张国恩,告诉他们上海建党的情况,希望他们也建立共产党组织。于是,董必武立即联系陈潭秋、赵子健等酝酿建党工作。对李汉俊指导武汉建党的过程,几十年后董必武仍然记忆犹新,他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组建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40]正在董必武等筹备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从上海派来了筹建武汉共产党组织的使者——刘伯垂。刘伯垂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他按照陈独秀的指示,分别找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人联系。这些人对建立中国共产党取得共识。于是,8月的一天,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由刘伯垂主持召开了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大会。当时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参加成立会议的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刘伯垂在会上介绍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有关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上海党组织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由刘伯垂提议,会议推选包惠僧任书记。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毛泽东的筹划下建立的。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寻找志同道合的“真同志”入手,先后成立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并与新民学会的中坚分子讨论建党的问题。1920年秋,新民学会已经拥有100多名会员,是一个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进步团体。其中一些先进分子已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在上海、北京的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入党的赵世炎、陈公培不久先后赴法国留学,张申府也到法国里昂大学任教。张申府到法国后即在旅法学生中发展党员,周恩来和刘清扬就是这时在法国加入了党组织。到1921年初,陈独秀了解上述情况后,分别致函赵世炎、陈公培,要求他们与张申府接上联系,于是上述5人即组成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
这样,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增加。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41]在国外,也成立了2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立中国共产党,首先回答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
关于党的名称。最早由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李达记得,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有七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我对于‘生产合作'一项表示异议,陈独秀说‘等起草党纲时再改’”。党纲有了,那么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呢?当时的方案有两个:一是叫中国社会党,二是叫中国共产党。围绕叫什么名字争论很激烈。于是,写信跟李大钊、张申府商量。据张申府回忆:“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这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42]这样,党的名称定了下来,就是“中国共产党”。
关于党的性质。陈独秀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在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43]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进一步强调建立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出:“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者的政党。”[44]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指出:“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镜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45]后来,在讨论建党问题时,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46]
关于党的纲领。1920年11月,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公有,社会公用。”[47]
关于党的组织原则。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期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48]
经过全党的集体努力和悉心探索,中共早期组织已经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建党思想,为在中国建设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担负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作为上海发起组书记的陈独秀肩负着更大的责任。1920年12月16日,陈独秀接受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邀请,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离开了上海。李汉俊接替陈独秀担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负责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主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了后,认为这是陈独秀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于是,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草案,提出党的组织要实行地方分权。这显然不符合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按照这种主张建立起来的党也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改造社会的任务。李汉俊起草的党章草案寄到广州后,陈独秀看了也不满意。两人就这样决裂了。李汉俊一气之下,辞去代理书记一职,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从此到1921年7月,李达主持完成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举行。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张国焘主持了大会,毛泽东、周佛海为大会秘书。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他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随后,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7月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25日、26日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他们以酝酿建党过程中形成的党纲草案和上海、广州小组起草的党章为基础,参考共产国际一大纲领与俄共(布)纲领,起草了将党纲、党章合在一起的党纲,以及当前工作决议。7月27日、28日、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主要讨论4个方面的问题。陈潭秋后来回忆说,大会集中讨论的问题是:一、目前政治状况;二、党的基本任务;三、党章;四、组织问题。
7月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四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侦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会场,结果一无所获。由于代表们的活动已受到监视,会议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会议代表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完成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内容。
这是党的一大最重要的一天,它把此前为建党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变成党的意志。在这天的大会上的一项最重要的议程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这个共有15条的纲领中,第一条即确定了党的名称,规定:“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条规定了党的基本纲领:“(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第三条规定:“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49]这些规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虽然没有使用“共产主义”的概念,但指向目标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如“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讲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指出:“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主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经期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50]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是小康社会的最高境界,我们所说的小康社会只是走向共产主义路上的一个小浪花。从这个意义上讲,建成小康社会,不是邓小平正式使用“小康社会”概念的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而是肇始于党的一大。
【注释】
[1]郭建勋文:《屈原的乡国之情与人格魅力》,见《光明日报》2014年5月26日。
[2]同上。
[3]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
[4]《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80年大事简介》,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
[5]同上书,第49页。
[6]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概论精选》(增订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03页。
[7]陈旭麓主编:《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80年大事简介》,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8]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8页。
[9]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页。
[10]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4页。
[11]金一南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2]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6页。
[13]尚明轩著:《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14]《临时政府公报》,第一号,南京大总统府印筹局1912年编印。(www.zuozong.com)
[1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16]《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77页。
[17]《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18]《新中华民族主义》(1917年2月19日),《李大钊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19]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192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476页。
[20]《〈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21]《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22]《给父母亲的信》(1923年1月10日),《俞秀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23]《湖北全体学生上督军省长公函》(1919年5月12日),《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24]《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921年1月1日、2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5]《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1922年1月15日),《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26]《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27]《荏苒三十年》,《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28]《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29]《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1922年1月1日),中共湖北省潜江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李汉俊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281页。
[30]《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
[31]陈独秀:《〈共产党〉月刊短言》(192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476页。
[32]《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1921年3月21日),《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368页。
[33]《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1922年9月27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34]《蔡林彬给毛泽东·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35]《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 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508页。
[36]《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37]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62页。
[38]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39]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
[40]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1937年),《“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
[4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42]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43]陈独秀:《答黄凌霜》,《新青年》第9卷第6号。
[44]《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
[45]毛泽东:《毛泽东给罗章龙的信》(1920年11月25日),《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34页。
[46]同上书,第544页。
[47]《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6页。
[48]蔡和森:《蔡长彬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9月16日),《“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49]《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5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