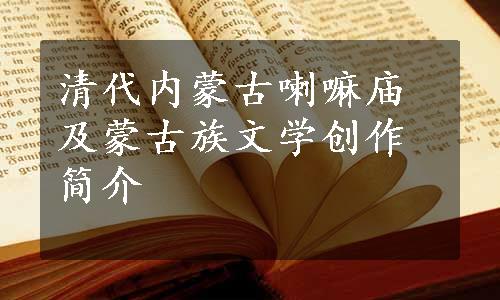
清代内蒙古地区的宗教,占统治地位的是格鲁派藏传佛教(又称黄教)。清中叶之后,西方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在内蒙古地区的势力急剧膨胀,并直接与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及内蒙古民众的反帝斗争交织在一起,影响深远。黄教又称喇嘛教、藏传佛教。该教是佛教的一个支派,其教义主要是宣扬灵魂不灭之说,劝人独善其身,虔修来世。凡能积累功德者,死后灵魂即可升天,人千极乐世界,即或再次投转人世,也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黄教是清代内蒙古地区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黄教在明晚期传入内蒙古地区,并迅速得以传播,到17世纪初时,业已成为蒙古全民族信仰的宗教。俗之道也。清朝政府为扶持发展喇嘛教,不惜消耗大抵财力物力,在蒙古地方大力鼓励和提倡兴建喇嘛庙。内蒙古地方现存喇嘛庙绝大多数为清代建筑,且以康雍乾三朝为最。1691年,康熙帝为纪念多伦会盟,在多伦诺尔修建汇宗寺,时漠南、漠北蒙古各部均派喇嘛住持参加,使该寺成为当时著名的宗教中心。雍正时又在多伦修建善因寺。清朝皇帝还以御赐寺名及匾额的形式进行鼓励,蒙古各旗凡兴建50间以上的庙宇,请奏御赐寺名时,按制可由理藩院奏请赐给名号。清代蒙古地区较为著名的黄教寺院几乎都有御赐的名称。喇嘛寺院遍及整个草原。多伦诺尔地区先后修建的有汇宗寺、善因寺、会心寺、曼陀罗庙等大寺庙,还有15座附属寺庙。设有章嘉呼图克图掌管的“多伦诺尔喇嘛印务处”,还有驻京和内蒙古各地大呼图克图的驻庙(称“仓”)。呼和浩特地区修建和重建了无量寺(大召)、延寿寺(锡坪图召)、崇福寺(小召)、崇寿寺(朋苏克召)、隆寿寺(额木齐召)喇嘛教的教义经典业已成为民众处理一切事务的基本准则。“人生六七岁即令习喇嘛字,诵喇嘛经”。蒙古人患病不去请医生诊治,首先求助喇嘛念经祈祷;泉水干凅、家畜染疫死亡狼群为害等许多事情,蒙古人都认为是恶魔作祟,赶快延请喇嘛念经驱鬼。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选择营地都要请喇嘛占卜,以定吉日,并在场哮经。但在清末,由千寺庙经济,特别是佛仓经济的恶性膨胀,上层喇嘛挥霍无度,生活腐化堕落,加速了藏传佛教的衰败。20世纪初,蒙古王公中间的部分有识之士已开始逐渐觉悟,意识到藏传佛教对社会的严重危害,进而提出改革和取缔宗教的进步主张。科尔沁郡王棍楚克苏隆在其“条陈自强办法”中,首先提出“取缔宗教”。由此可见,藏传佛教的精神统治地位已发生动摇,蒙汉民众随着宗教的衰落也正日益觉醒。
清代以来,蒙古族学者重视蒙文古籍和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涌现出一些卓有成绩的学者。他们用蒙、汉、藏文撰写的著作,记载并反映了历代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兴衰和沿革,成为后人研究蒙古史的宝贵遗产。清初,伊克昭盟乌审旗出生的蒙古族历史学家萨囊彻辰,编著有《蒙古源流》(蒙文名《额尔德尼·脱卜赤》)。该书于1662年(康熙元年)写成,是根据元代记载蒙古诸汗源流的《大黄册》、《红册》等蒙藏文多种史料写成。清代,蒙古族文学作品体裁呈多样化发展,无论是书面文学中的小说、诗词,还是许多无名作者的口头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蒙古族民众的聪敏才智。在文学创作领域中,涌现了松巴堪布伊什班觉、罗卜藏楚勒图木、罗布桑丹必扎拉申、阿克旺丹丕勒、阿克旺丹达尔、阿克旺道布敦、阿克旺罗卜藏达格巴坚赞、罗布桑普仁莱、丹津拉布扎、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阿克旺海珠卜等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们用蒙、藏两种文字创作了大量作品,为蒙古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蒙古族和临近民族在沟通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文化交流活动逐渐活跃。一些先进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冲破清朝的愚禁政策和宗教文化的禁铜,进行汉文创作。有些文人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汉文小说诗歌。其中,尹湛纳希最有代表性。在《红楼梦》和《镜花缘》等影响下,以毕生精力创作了具有鲜明特点的《一层楼》、《泣红亭》等多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和大量诗歌、杂文。他的作品在承继蒙古族文学传统同时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兼容并包、融会贯通。他还搜集了大量蒙汉满藏等多种文字的有关蒙古史料,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大元盛世青史演义》。
蒙古族女诗人那逊保兰,是喀尔喀蒙古阿拉善王之女,自幼接受汉族古典文学和诗歌的熏陶,在12岁时即可利用汉文吟诗赋词,有《芸香馆遗诗》三卷存世。和瑛是乾隆三十六年的进士,曾任总督、将军等职,著有《铁围笔录》、《易简斋诗钞》等。八旗蒙古正黄旗人法式善是略晚千前者的乾隆朝进士,著有《存素堂集》、《诗龛咏物诗》、《清秘述闻》、《陶庐杂录》等。博明为博尔济吉忒氏,精通满、蒙、藏文,著有《西斋诗》、《西斋偶得》、《凤城琐录》等。正黄旗人思麟为道光朝进士,著有《塞游草诗》、《听雪窗诗草》、《笔花轩诗稿》。
许多蒙古族文人还把大量汉族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蒙文,为蒙古族文学领域的繁荣输入了新的血液。其中有的汉文作品是由满文转译成蒙文的。这些名著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今古奇观》、《金瓶梅》、《封神演义》等百余种。卓索图盟人哈斯宝译有《新译红楼梦》一书。这些文学作品在衣业蒙旗几乎是妇孺皆知,远比清朝政府大力提倡下翻译刊行的《圣谕广训》和喇嘛教义传播广泛。此外,还有不少汉文哲学、史学著作也被译成蒙文,介绍到蒙古各地。
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华民族风起云涌的反侵略抗争,激发了那些出身于统治阶层的爱国作家,青年诗人古拉兰萨创作了诸如《望肃清英吉利匪盗胜利归来》和《太平了》等许多诗篇。此外,他还写作了一些揭露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荒淫无耻的诗歌,鸦片战争发生后,中华民族风起云涌的反侵略抗争,激发了那些出身于统治阶层的爱国作家,青年诗人古拉兰萨创作了诸如《望肃清英吉利匪盗胜利归来》和《太平了》等许多诗篇。此外,他还写作了一些揭露蒙古王公和上层喇嘛荒淫无耻的诗歌,如《丑恶的本相》等。
蒙古民族能歌善舞,其音乐和舞蹈都具有曲调高亢、音域宽广、旋律奔驰明快等特点。在清朝,“什榜”是蒙古族著名音乐。它以笳、管、筝、琵琶、弦、火不思等民族管弦乐器演奏,同时有声乐伴奏,伴唱者“鼓喉而歌,和罗应节”气据《清裨类钞》“礼制类”记载,“什榜,番乐也,思桴苇篇,有上古遗音。”这种乐曲,多用千宴会时的伴奏。清政府将此乐曲列为国乐之一,在宫廷节日和朝廷赐宴蒙古王公贵族时演奏。据《清会典》“乐部“记载,“太宗文皇帝平定察哈尔,获其乐,列于`燕乐',是曰蒙古乐曲。”在蒙古族和达斡尔族中盛行集体舞蹈“安代”,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舞蹈,与其原始宗教萨满教密切关联,它把音乐、舞蹈和歌谣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在表演上具有歌舞结合的特点。清中叶,“安代“舞开始在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地区盛行,但已更多地渗入了宗教迷信色彩。随着汉族移民的大批进入内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下层民众的语言文化艺术交流,也逐渐展开。蒙古族民间的说唱艺术“好来宝”,经常演唱《三国演义》等汉族故事内容。深受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喜爱的“二人台”,更是蒙汉民间艺人共同创(www.zuozong.com)
清政府出于强化内蒙古地区统治的需要,比较重视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在中央机构的理藩院、国子监,在内蒙古地区的各盟旗官署衙门,都提倡使用蒙古语言文字,兴办了一些蒙古官学和寺院附属的翻译机构,肆业生员必须掌握蒙文阅读和书写的基本知识,一般还兼学藏文、汉文。清政府规定在内蒙古古地区普及蒙古文字,还提出了实行蒙古语言的规范化、统一化的书面语言要求,对于一些重要的官书、典籍和律例等,都要求翻译成蒙文刊印发行。在此政策影响下,清代蒙古族中出现了一些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有的精通满、蒙、汉、藏多种语言文字,有的还通晓托忒文、维吾尔文字。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学者们编撰和出版了不少蒙古语言学著作,尤其以各种蒙古文字、语法、语汇、辞典为多。中国各民族间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他们相互学习进而熟悉了对方的语言文字,编纂出许多蒙古文和满、汉、藏、维吾尔等多种文字对照的辞书和书籍。蒙古民族能歌善舞,其音乐和舞蹈都具有曲调高亢、音域宽广、旋律奔驰明快等特点。在清朝,“什榜”是蒙古族著名音乐。它以笳、管、筝、琵琶、弦、火不思等民族管弦乐器演奏,同时有声乐伴奏,伴唱者“鼓喉而歌,和罗应节”。在蒙古族和达斡尔族中盛行集体舞蹈“安代”,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舞蹈,与其原始宗教萨满教密切关联,它把音乐、舞蹈和歌谣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在表演上具有歌舞结合的特点。清中叶,“安代”舞开始在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等地区盛行,但已更多地渗入了宗教迷信色彩。清代蒙古地区的许多庙宇都是蒙古族能工巧匠们自行设计修建的,集蒙古族的造型、雕塑、绘画艺术之大成。其建筑风格、佛像塑造及绘画雕刻装饰,都充分展示了蒙古族建筑设计师和艺术家的才华。当时有很多技艺超群的画匠喇嘛和雕塑家活动千内蒙古地区的各个寺庙,留下了无数作品。归化城的工匠希库尔达尔罕和贝勒达尔罕设计修建了本城乌苏图西召、包头昆都仑河右岸的昆都仑召(又名法褶寺)。鄂尔多斯大召的建筑风格和团案都出自博硕克图济农之手。在汉族织绣、刺绣和西藏佛像刺绣等艺术影响下,蒙古民族的民间刺绣和贴花艺术也不断丰富发展。他们常用这些艺术品装饰帽靴、腰边、荷包等服饰和被褥单、枕套、门帘等,显示了游牧民族的张扬豪放的风格。
清朝内蒙古地区曾有多种教育体制和形式。既有官办的八旗教育和汉地厅学,也有西方教会势力兴办的学校,较之更为普遍的是私塾教育和寺庙教育。伴随着晚清兴学社会思潮的掀起,一些地方开办了仿西式的学堂教育。许多西方传教士为配合传教,在内蒙古地区设立了一些学校。如在归绥城内,光绪二十七年,一牧师千通顺街建教堂、施医药房,复设男女国民小学各一处、男高小学一处。与其他教育形式相比,私塾显得更为普遍,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才逐渐消止。内蒙古地区的寺庙教育一直相对独立地存在且很普遍。很多没有条件入官学或就读私塾的平民阿勒巴图子弟,从喇嘛那里学习蒙、藏文字。较大的寺院,是内蒙古地区宗教文化教育的中心。多伦诺尔汇宗寺、东土默特瑞应寺、科左中旗玛拉沁庙等有名的寺院里,均设有经院学部(喇藏),招收部分喇嘛攻读时轮、医学、密学等高等课程,培养了很多高层次人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廷筹办京师大学堂,谕令将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之学校。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再令将各省驻防的八旗官学和书院,一律改为小学堂。内蒙古各盟旗在这样背景下,出现了兴学热潮。
清代内蒙古地区许多著名的喇嘛教寺院中都设有医学研究机构,如瑞应寺、多伦诺尔庙、锡林郭勒盟贝子庙(崇善寺)、科尔沁地区玛拉沁庙、延福寺等庙宇里设有各类学部,其中医学部最为有名,培养出很多著名的喇嘛医生。绰尔济墨尔根、伊什班觉、伊希丹津旺吉拉、察哈尔罗卜藏楚勒图木、罗布桑全普乐、占布拉、占布拉多尔济以及阿克旺罗布桑丹必扎拉申等人是典型代表。据资料记载,在清代先后出现了上百位名医。清初,藏族著名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所著《四部医典》传入内蒙古地区。很多蒙医吸收该书基本原理,结合当地医疗实践经验,编撰了不少蒙医著作。19世纪奈曼旗的占布拉多尔济所著《蒙药正典》,是一部系统阐述蒙古医药的专著。蒙医所用传统疗法,效果颇佳,在当时颇受重视。清政府还特设有蒙古医生服务的机构,选调医术高超、擅长治疗创伤、正骨、接骨和按摩的蒙医,专治外伤,并令其招收学徒,传承其专门医术。许多蒙古医生不仅将精湛的接骨秘方技术传授给满蒙八旗将士,还使当时在京师学习的俄国学员受益。清代内蒙古地区大型寺院里还设有时轮学部,研究和传授天文、历法等高等知识。瑞应寺的时轮学部培养了不少精通天文、历法的人才。一些蒙古天文学者综合当时天文基础知识,吸收西方天文知识,以蒙文编著有《天文学》,这是一以探讨盖天说和浑天说相互结合的天体理论著述。康熙、雍正年间,著名的蒙古八旗正白旗籍天文学家、数学家明安图(1685—1770年)在钦天监学习,并任职时宪科监正。他不但精通天文学、数学,且精通汉文,每年将汉文本《时宪书》译成蒙文,呈请清廷颁行,供内蒙古地区使用。在算学方面,明安图也著名千时。他研究割圆术和圆周率新的计算方法,“积思三十余年”,著成《割囡密率捷法》四卷,用新的解析方法计算圆周率,创造了计算割圆术的13个新公式。
清代,内蒙古地区蒙文印刷事业已有一定发展。京师寺庙和内蒙古地区多设有木刻印刷所。其中京师地区比较有名的是净住寺、离祝寺、隆福寺、白塔寺等,在内蒙古地方,则有察哈尔察罕乌喇庙、多伦诺尔庙、瑞应寺、五台山、大库伦、阿拉善延福寺等处的木刻印刷所。清末,在西方近代文化和清王朝新政政策影响下,部分蒙古有识之士开始尝试兴办各种新式社会文化事业,以求提高民智、改革图强。石印技术的传入及日后蒙文铅字的创制和应用,使蒙古族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可以着手石印或油印蒙文教材及其他出版物。蒙古民族新式出版事业由此开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