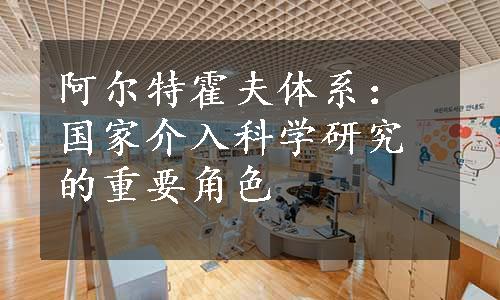
在国家介入科学研究方面,阿尔特霍夫起到了重要作用。意志坚定、手段灵活的俾斯麦是德国统一与崛起的关键人物,而执着的阿尔特霍夫对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教育及科研的重大突破同样不可或缺。1882—1907年正是德国国力的跃升期,阿尔特霍夫为普鲁士大学和科学事务负责人,他权威、个性化的领导风格很容易让人想起俾斯麦。阿尔特霍夫削弱普鲁士大学的自主权,把大学纳入政府的管辖之下,使之为工业和社会服务;他改造普鲁士的科学研究体系,建立众多的国家研究所,使之成为大学之外重要的科研力量;他为普鲁士和德国构筑了一套现代化的教学与科研体系——阿尔特霍夫体系。(Vereeck,2001)32
阿尔特霍夫主要的工作地点先后为斯特拉斯堡和柏林。阿尔特霍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工作了十年之久,主要负责大学行政管理工作。他以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为榜样,将斯特拉斯堡大学建成为一个标准的联邦大学,并且通过聘任优秀的德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将斯特拉斯堡大学打造成德国科学的国际中心。这一计划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因为斯特拉斯堡大学位于法国割让的领土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德国当局意在使该大学成为化解民族对立的工具。阿尔特霍夫推广了研讨班,充实了学校理事会(Senate),把自然科学从哲学学院中分离出来,把政治—法学学院分成政治学院和法学院两个独立的学院。他还成功地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打造了年轻优秀的教师队伍,他任命的教师(准确地说应该是“教授”,因为只有教授才需要国家的正式任命,并且是政府的公务员)平均年龄不到39岁。与此相比,当时德国大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53岁,而柏林的教授的平均年龄是62岁。因为拥有一批充满创造力的年轻教师,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院、政治和法律学院很快就成为最好的学院。阿尔特霍夫强硬的工作风格经常受到一些教师的诟病,新上任的州长对他也不太友好,把他推荐到文化部工作。没承想,柏林为阿尔特霍夫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为了使普鲁士的科学和大学占据领先地位,他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取得了巨大成就。(Brocke,1980)30
1.千方百计吸引优秀人才
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是科学体系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是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大学声誉的最简便的做法。鉴于普鲁士和柏林的特殊政治地位和经济上的优势,阿尔特霍夫能够把相当数量的学者吸引到柏林来,这其中既有早已获得教授职位且远近闻名的学者,也有青年学者。在对学者的选择上,阿尔特霍夫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会因为民族和宗教信仰而区别对待。在对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学者和未受洗的犹太学者的任命上,他比前任走得更远,一些持社会主义信仰的国民经济学家也获得了教职。
普鲁士大学任命教师的一般程序是,学院和校方提出一个候选人名单,一般包括三个人,教育部从中选择一人。在这种传统下,大学和学院掌握了主动权。出于自身小圈子利益,大学教师任命之中的“裙带关系现象”时有发生,知名教授往往推荐自己的朋友或学生出任空缺的职位,但是这些候选者并不一定是最佳的。阿尔特霍夫任职后对学校的推荐进行严格审查,有时甚至提出自己中意的人选。他的朋友也通过他的影响直接涉入了教授任命,在相关学科领域中有着很大的影响。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和哈纳克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在古代史和神学领域的任命中各自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阿尔特霍夫不断加大政府对大学的掌控力度,使之更为明确地为国家的全局利益服务。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对大学自主权的粗暴干涉而遭到非议。被任命的青年学者则把阿尔特霍夫视为“拯救者”,典型的例子是对贝林(Emil von Behring,1854—1917)、科赫(Heinrich Robert Koch,1843—1910)和埃尔利希(Paul Ehrlich,1854—1915)的任命。
贝林最早在部队医院服役,后来来到普鲁士传染病研究所做科赫的助手,并成为主治医师。在此期间他发明了血清疗法,在医学治疗和科学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要获得学术职位并不容易,他在马堡的任命遭到了大学的抵制,马堡方面曾拒绝了他三次。这一任命是在阿尔特霍夫的强力支持下才最终实现的。科赫自己也是在阿尔特霍夫的支持下来柏林任职的,并成为专门为他专门建立的研究所的所长。埃尔利希最开始在贝格曼(Ernst von Bergmann,1836—1907)手下工作,科研缺乏独立性,经常被使来唤去。阿尔特霍夫为他专门建立了一个研究所,埃尔利希获得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并发明了治疗梅毒的砷凡纳明。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1893年,阿尔特霍夫任命天主教徒希策(Franz Hitze,1851—1921)为明斯特新建立的基督教社会学教授,但他连博士学位都没有,这显然突破了常规。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在马堡的任命也是在学院的反对中实现的。(Brocke,1991)1901年贝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接着科赫在1905年、埃尔利希在1908年获奖,这或许是阿尔特霍夫“慧眼识才”的证明。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绝大部分人都受到过阿尔特霍夫的提携,他因而又被称为德国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
2.积极推动科学与工业“联姻”
阿尔特霍夫执掌文化部的时代正是大工业时代的早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工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工业以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同时工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德国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发展都与德国相关科学领域的进步有着直接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得包括皇帝在内的德国统治阶层对发展科学技术高度重视。他对工业界与科学界的“联姻”持鼓励和支持的态度,积极扮演富有阶层和工业家支持科学活动的推动者、引导者和联络人的角色。具有奠基性意义的是阿尔特霍夫仿效外国的科研项目资助模式,培育了德国私人资本和基金会组织。阿尔特霍夫发起建立的腓特烈皇后宫(Kaiserin-Friedrich-Haus)主要用于培训医生,为此成立的基金会拥有150万马克的基金会本金。他成立的《国际科学、艺术和技术周刊》(Internationale Wochenschrift für Wissenschaft, Kunst und Technik)受到鲍定谔和科佩尔基金会(Koppelstiftung)的资助。阿尔特霍夫还是克莱因成立的哥廷根应用数学和物理促进协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这一协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工业家。(Füssl,2004)53(www.zuozong.com)
3.创办了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
新的科研机构的建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在大学内部设立新的科研机构,这主要是指大量研讨班的设立;另一方面是独立于大学之外的国家研究所的设立。建立新的研究机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新学科的研究人员提供研究条件。新学科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在大学的体制内为这些研究人员提供职位的可能性并不大。这些研究机构从一般性的教学任务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研究工作,那么建立国家研究所就成为一个必要的选择。在阿尔特霍夫任职期间,超过240个研讨班、临床课(Kliniken)和医学实验室及自然科学研究所建立起来或者扩建。1900年,阿尔特霍夫被选为医学界代表大会的主席,这使他对医学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提议下,在科隆、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建立了临床医学科学院,这对医生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Lischke,1990)21-24他是夏里特(Charité)扩建工程专员,这对柏林和普鲁士的医学研究和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阿尔特霍夫科学政策的核心是达勒姆计划,即在柏林市郊的达勒姆建立一个现代科学中心,形成所谓“德国的牛津”。这一计划最终促成威廉皇帝学会的建立。
4.政府介入大学和科学事务
阿尔特霍夫大刀阔斧地改革也造成了他与大学、大学教授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学教授对他的批评持续不断。批评集中在他对大学“学术自主”的破坏和他的工作作风。教授在阿尔特霍夫眼中与中小学教师和档案管理员毫无差别,都是公务员,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接受调配。为了和阿尔特霍夫见面,教授有时要等几个小时,这对于习惯让别人等自己的教授来讲是难以接受的。(Brocke,1980)13在《一个经典物理学家的梦魇》一书中对此有较为生动的叙述。(麦克马克,2004)
人们对阿尔特霍夫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对传统的破坏,把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松散变得紧密,即大学的“官僚化”。这实际上是20世纪大学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只不过在普鲁士较早发生。当大学和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时候,政府肯定要加强对它的管理与引导。另外,政府的拨款对于大学来讲越来越重要,大学与政府互有所求,这意味着大学原来所拥有的自主性要受到损害。这一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英美大学当中也发生了,当然不一定是在教授的任命问题上。同时,人们也不应把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大学视为大学的理想状态。大学内的裙带关系、保守性和管理的松散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比如有些大学的博士答辩不需要提交论文,只需通过口头答辩就能获得学位。阿尔特霍夫的努力就是消除这些问题的一种尝试,也许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尝试。
就他对普鲁士和德国的大学及科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来讲,他可以与洪堡相提并论。洪堡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他所提出的教育理念和他对建立柏林大学所起的作用。阿尔特霍夫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理念,但他打造的普鲁士大学和科学体系更为高效和现代化。
阿尔特霍夫对大学的改造也被称为“大学的官僚化”,即大学频频受到政府干预,几乎变成了政府机构。洪堡提出的“学术自由”原则保障了大学内部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扰,大学学术发展的原则是“为了科学自身的目的而研究”。政府为大学提供相对来说还算充足的预算经费,保证了大学的正常运作。但是这种保障的一个后果便是大学与社会的发展脱节。大学面对工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需要没有主动做出调整,仍然处于远离尘世的象牙塔之中。
在19世纪80年代普鲁士的综合性大学中,传统的优势学科,如哲学、法学、语言学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些领域的教授们控制着学校,他们仍然抱着过去的纯科学观念,拒绝与现实接轨,新的自然科学和相应教授职位的设立在大学中受到抵制,克莱因在哥廷根大学开展技术教育和研究的努力屡受挫折就验证了这一点。很多大学的物理、化学等学科都是以研究所的形式被囊括在哲学学院中,而不能成立独立的学院,这限制了教授职位的数量和学科的发展。普鲁士大学的这些问题,仅靠大学自身是很难解决的。那么政府作为外部力量介入就是必需的,而阿尔特霍夫则是这种力量的代表。正是阿尔特霍夫等人的努力,普鲁士的大学体系才从以人文学科为重转向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的现代大学体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