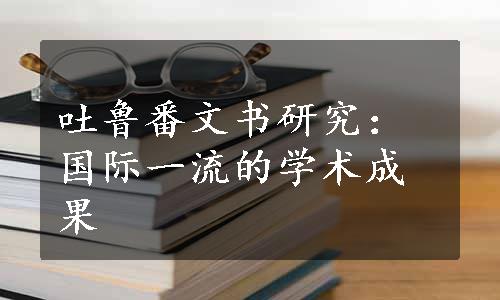
吐鲁番学的研究上,日本人就不敢讲“吐鲁番在中国,吐鲁番学在日本”。吐鲁番文书是从1975年开始大规模发掘的,也就是藤枝晃讲话那年开始发掘。吐鲁番盆地两个很大的墓群(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发现很多文书,包括剪成碎片,做成衣服、鞋底等保留下来,一共三万多片。以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的主任唐长孺先生为首,参与整理这批文书,这项工作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全部结束,现在已经出版了十册《吐鲁番出土文书》,这十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的。后来我们陆续出了一批非常有分量的研究著作。我本人在我的老师韩国磐教授领导下,也参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出了一部《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论集》。我们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就是不到二十年间,在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上,像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学者们,总体水平是国际一流的。因为他们花了精力、花了时间,所以这一段历史不应该是我们的伤心史,但是伤心史是在前段,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次我在中正大学参加“海峡两岸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做得很好,包括一些很年轻的学者,比如政治大学罗彤华,她写沙州帐本,从帐本看当时归义军寺院和各方面的关系,我认为这篇文章做得非常好。不管大陆学者、台湾学者,有一批年轻学者都非常好。我们走过这个历程将近一个世纪,自1900年发现敦煌材料后,以后有吐鲁番材料,一百年的历史证明,陈先生提出来的“一代之学术,必有一代的新材料与新同题”的教导是十分正确的,要牢记敦煌学开始的半个世纪伤心的历史。
陈垣《敦煌劫余录》以后,陆续又出版了关于敦煌资料撰编的书,这些书很多,比如史岩编《敦煌石室画像题识》,“题识”就是佛经故事、经变故事的画像下的题款,由于画像有人出钱,所以底下有一个题款,题识某某人某某职务。这本书我认为做得非常好,常书鸿有一篇序。常书鸿在四十年代就到沙漠里去作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做到八十年代才到北京去住,不久就去世了。除了本书以外,罗振玉编纂《敦煌石室遗书》一百二十种,也是非常大的工程,对整理、保存文献做了贡献。比较迟一点就是王重民先生,编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这是流失海外的敦煌文书,第一次以比较全的面貌,回归到国内学者的案前,后来有刘复《敦煌掇琐》等。八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大陆方面非常重视敦煌文书的整理,现在已经正式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全套出版。这样一来我们海内海外的文献,搜罗、编印工作应该说是空前未有的;各大出版社还出版很多专门研究性的著作。现介绍其中重要者如下:(www.zuozong.com)
陈垣《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序)、史岩纂《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常书鸿序)、金同祖辑《流沙遗珍》、罗振玉纂《敦煌石室遗书》一百二十种、王重民撰《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刘复辑《敦煌掇琐》、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附录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代表性研究著作(以社会经济史著作为例):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附录文),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韩国磐《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程喜霖《汉唐烽燧制度》,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研究》,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朱雷《吐鲁番文害研究论集》,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上下卷(共四册),北大、武大、厦大出版社印行的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多种,散见《敦煌学辑刊》、《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和各大学学报之论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