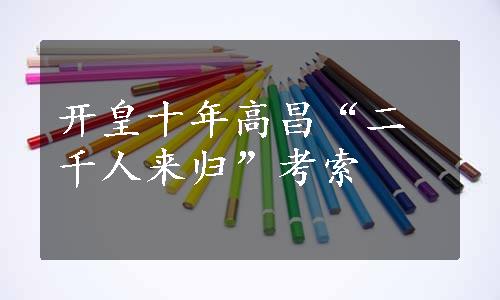
《北史》卷97“高昌”云:“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隋书》卷83“高昌”记载同。如果以上记载属实,那么这是有隋一代见诸文字的和高昌的第一次接触。但是,这一记载疑问不少。《北史》同卷同条还说:“隋开皇、仁寿之间,尚未云经略。”即,开皇、仁寿时隋还没有经略西域之事。这样,2000人归中国之说,便难于落实。查《北史》、《隋书》之纪传和《册府元龟》外臣部,除上述记载外,均无高昌2000人来归之说。所以,黄文弼先生在《高昌国麴氏纪年》中明确否定了此说的真实性,他写道:
按,隋开皇十年(590)正麴乾固延昌三十年,时高昌已附属突厥,当无突厥来侵之事。高昌传下文紧接“坚死自伯雅立”之语,由今地下发现,坚死后,又立四世,方及伯雅。故知“坚死子伯雅立”之说不可据;因而开皇十年突厥来侵之说,亦不可遽信。故余疑突厥侵高昌,破其四城,必在建昌以前,或与突厥侵北边同属一事,而中国史书错记年代耳。[3]
就黄先生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来说,这一分析应当说是谨慎而值得注意的。其次,既然不存在开皇十年突厥侵高昌四城事件,当然也自然无所谓开皇十年高昌2000人归隋一事。但是,我查阅了已出版的吐鲁番文书和有关史书记载,认为黄先生的分析,还有商榷之余地。《北史》、《隋书》关于高昌和周隋关系的记载本身就有一些矛盾,不那么准确。如《北史·西域传》记载说“东西魏时,中国方扰,及于齐、周,不闻有事西域,故二代并不立记录。”事实并不如此。《北史》本纪就记载北周保定元年(561)高昌遣使来朝贡。可见《北史》记载有关事本身前后不一致。尽管如此,也不能怀疑所有记载的参考价值,重要的是要找出适当的佐证。
就开皇十年突厥破高昌四城,“二千人来归中国”的记载来说,首先应考索的是突厥有否或有没有可能侵入高昌问题。黄先生认为高昌在建昌以前即附属突厥,则不会发生开皇十年突厥来侵高昌之事。这是可以讨论的。突厥是一个奴隶制的游牧民族,掠夺是无法停止的,所谓“候月将满,辄为寇抄”。[4]它并不因臣属于隋而不再侵扰隋辖境,也不因为高昌依附于它而不再侵扰高昌了。在延昌十五年(575)前一段时间,突厥与高昌的关系可以肯定比较融洽。《麴斌造寺碑》的记载证明这一点:
……其后,属突厥雄强,威振抈(朔)方,治兵练卆(卒),侵我北鄙。□□□□军之委,承厝(庙)胜之策。鹰扬阃外,虎步敌境。兵锋暂交,应机退教……安虑危,见机而作。乃与之交好,永固邦疆……之以机辨,陈之以祸福。席(厥)主钦其英规,土众畏其雄略,遂同盟结姻,□□□□而归。自是边□□□,□□无虞,干戈载戢,弓矢斯韬,皆君之力也。[5]
麴斌施产建寺为建昌元年(555)乙亥,但其子亮立此碑在延昌十五年(575),从建寺到竖碑历时20年,其原委黄文弼先生已有分析,[6]既然立碑时还颂扬麴斌与突厥和解的功劳,而且碑阴蹶名首为麴宝茂,头衔是“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同)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帑堇□多浮跌无亥帑利发高昌王”,帑利发或称俟利发为突厥大臣之一,说明延昌时,对于突厥赐予的封号,还很重视。由此可见,麴乾固延昌十五年之前,高昌依附于突厥,高昌与突厥一直维持着融洽关系。[7]但是,以后一些资料证明这种关系可能发生问题,我认为继麴宝茂而王的麴乾固统治后期,有一段时间兵部买马频繁、各城丁输加紧,给人以战火迫近的印象,从时间上说,恰好发生在延昌二十七年(587),即随开皇七年。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3册(以下凡引本书时只记册数,略去书名)阿48号之五至十二兵部条例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计八件。这八件文书除第十二缺署名部分,其余七件署名和年代基本清楚。根据高昌王朝公文格式,文书后的署名以时间一行为界,前半部由中央主管部门首长签署,后半部为地方主管部门首长签署,这七件所署官职,前半部为门下校郎口琼(或麴患)、通事令史麴患(或和乐、杨友)、侍郎史养生(或麴庆儒);后半部统一为中军将军高昌令尹麴伯雅、右卫将军绾曹郎中麴绍徽、平远将军领兵部事麴欢以及严佛图、翟奇乃、郑僧道三人。时间最早为延昌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最迟为八月十五日,不明时间文书估计最迟在九月间,也就是这次兵部奏文买马公事在九月大雪季节到来之前办妥,似乎是为了防止秋收及秋后敌人的袭击,这是军事行动发生前一种迹象,更令人瞩目的是麴伯雅以下重臣将领的联署,说明此次兵部买马非同寻常。
就所买马匹数量来说,也是比较大的。第一次(四月二十九日)计有赤马、騧马3匹,第二次赤马1匹,第三次(六月二十九日)计有赤马、紫马、騧骝马、赤余(左旁马)马48匹,第四次(七月)紫马等8匹,第五次(七月十五日)计有青马等18匹(?),第六次(八月十五日)计有紫马、铁青马、弱马、骝马、余(左旁马)马、黄马40余匹,第七次2匹,第八次不详。高昌运输多赖驼、牛、驴,马匹显系主要是作战的需要。也就是说,此年买马的军事目的相当明显。
其次是,同时间各城兵役丁输加紧。阿48号之十三至十八等六件文书均系各城丁输文书。阿48号之十三《高昌传判麴究居等除丁输役课文书》涉及一般丁输除免,除免原因是应输民丁服兵役了。如文书的11行云:“赵应儿兵役,二人为校尉相明作供人一年除。”赵应儿前还有一人,名字应列于10行,属交河城人,可惜10行末此人名字已缺或漏写。赵应儿等二人应征服兵役了,所以为校尉作供人役除免。由此可以推断田地麴究居、交河马养儿、辛堆奴等人免除丁输一年,原因均为征服兵役,本件文书还首次出现商人役。商人役内容不详,但属非常措施则可能,不能不与特殊情况有关。文书中还有羁人役,其征发背景应与商人役相同。(www.zuozong.com)
阿48号之十四、十五两件是高昌、高宁、洿林等丁输木薪额文书,役其人数、范围、薪车数也是惊人的,这种情况可能与诸城重大的防守需要有关。现将两件文书丁输木薪额合计列表如下:
以上仅12城的丁输木薪额的不完全统计。高昌在北周时有城16座,隋时增至18座。还有6城未列出。这些不完全统计,大体上说明为各城运送薪柴的情况。
阿48号之十六、十七、十八三件文书是高昌诸城丁输额文书,第十八件包括将阿勇等所领人名籍。这三件文书丁输额是指征发到各城服役(筑城等工役)民夫数额。数额是比较大的,如第十七件明确记载“诸城得人六百八十六人”。三件文书具体年代不详,《吐鲁番出土文书》编者将它们系于延昌二十七年(587)兵部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之后,推断属于延昌时期。
总结上列三部分文书内容,我们得到印象,开皇七年(587)前,高昌曾发生局势紧张现象,而当时能够威胁高昌安全的,不是突厥阿波可汗(大逻便),就是莫何可汗(处罗侯)。阿波原建牙在高昌之北,约在阿尔泰山及准噶尔盆地。[8]《资治通鉴》卷176记载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与沙钵略有隙,阿波浸强,东距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号西突厥。
阿波约于隋开皇三年(583)左右西奔,而后浸强。依附阿波各国不包括高昌,是高昌未附西突厥,坚持独立的一个根据。这时的高昌必然会受到西突厥威胁。开皇七年阿波被处罗侯(或作处罗俟,沙钵略弟,开皇七年立,称莫何可汗)所擒,经隋王朝干预未被杀。处罗侯继阿波之后再西征,并在西征中为流矢所伤而卒,[9]继位者为都蓝可汗。处罗侯西征,《资治通鉴》系于开皇八年(588),但这可能是得到消息的时间,实际西征应在开皇七年,即延昌二十七年。上述高昌兵部买马、加紧各城丁输兵役工役恰在阿波和处罗侯争战及处罗侯西征之时,所以把这两件事和高昌形势联系起来考虑,就比黄文弼先生的推论似觉可靠。所以,我的看法是:目前尚无断然否认《北史》、《隋书》两书“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的记载的必要。我还怀疑这里“开皇十年”的十,恐系七之误,若如是,更有说服力了,但仅为猜测。而且,既然突厥有可能侵入高昌,高昌动议迁人归隋也不是不可能。
说到高昌内迁,早有先例可寻。据《北史》卷97的记载,麴嘉曾于北魏熙平元年(516)遣其侄、左卫将军、田地太守麴孝亮“朝京师,仍求内徙,乞军迎援。于是遣龙骧将军孟威发凉州兵三千迎之,至伊吾,失期而返”。北魏孝明帝熙平初年高昌遣使入朝,曾诏称高昌“甿庶”及“汉、魏遗黎”,在其地“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也”。神龟元年(518)冬,麴孝亮再次表求内迁,朝迁不允。麴嘉在位时为何一再表求内迁,恐非虚词假意。《隋书》卷83记载说:“嘉字灵风,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为高车所杀,嘉又臣于高车。”麴嘉在这种寄人篱下的困境中思迁内地,完全符合情理。相比之下,麴乾固统治的中后期,即延昌三十年前后,所处境况有些相同。先是阿波可汗的西突厥势力对高昌的包围,后是处罗侯于开皇七年西征的强大威胁。凡此种种都有可能导致麴乾固在开皇十年或许是七年派人传达请求内徙消息。
我推测,因为当时隋王朝没有解决突厥问题,西路阻隔,麴乾固请求内徙消息虽经转折传入长安,但因处罗侯死于流矢,西征中断,高昌所受的军事威胁解除,内迁动议也就停止。就是说,内徙动议是可能的,消息也传到京师,但内迁可能未果。《隋书》作者魏征和《北史》作者李延寿均经历隋、唐初时期,对隋朝许多情况是知道的,不太可能同犯一个错误,把建昌以前的事拉到开皇十年(或许是七年)来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